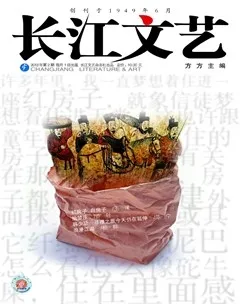生死不明:被诅咒的诗歌
关于新诗的生与死问题,是我在深圳的“诗歌人间”研讨会上思考的话题。今天早晨,我坐在北四环我住宅楼的厨房里,发了会儿呆,我面前苍茫的北方大地没有给我一丝灵动,大概有七八支烟囱在远处或近处也像我一样吃力地发着呆。我写下了“生死不明”几个字,觉得有点悬,几次想划掉。在此过程中,我还念叨过“生死不离”几个字,觉得有点媚、有点俗、有点土,更不是我想说的东西。当我写下“被诅咒的诗歌”几个字时,我的感觉来了。
我在深圳参加活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好玩儿的感受。2012的岁末年终了,人们如此热衷消灭与死亡的话题,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人们太向往这个游戏了。世界真的会终结吗?那我们终结在深圳这个乳臭未干的城市,死亡或许也生机勃勃。我在研讨会上是第一个发言的,自然就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是我现在写文章,回想起他们阐述的那些真理,有许多的确不能苟同。然而,我对写诗的人总体没有成见,他们已经面临灭亡了,如果他们表达出强烈的求生求活求伟求大的愿望,又有什么不可呢?
显然,我对新诗命运的判断是悲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快乐地写作。我的写作直指肉体、内心、分泌和性。对我而言,生命本身已是人质,我通过文字与语言来拯救,哪怕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拯救,其过程也充满欢欣。死亡在我们之外、在诗歌之外跳舞,我们记录它、描摹它。但在有些诗人那里,死亡却直接是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悲愤、修辞、装腔作势,利用抒情和叙事,诗歌的工具化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总是感慨很多诗人仿佛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这一点很麻烦,他们在他们的时间里说话,你解决不了那些困扰新诗的问题。
好,问题来了,大众却越来越背离我们、背离诗歌,他们不想解决我们的问题,压根儿不想。他们有吃、有喝、有玩、有干,他们花时间把财富聚集在自己手里,他们用多样化来养育自己的精神,他们离开诗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没死,还活着。人们为拥有最便宜的价值观而沾沾自喜。而诗歌人格说到底是理想化的,它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精神入侵者的角色,它试图洗涤那些虚妄、自私、短见和贪婪,它与世俗层面形成了对峙。这一场诅咒就此开始,仿佛祖国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博机上的博弈,双方都试图把对方降低为廉价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诗人是硬币,赌场的老板偏偏不是咱们选出来的。我们有点难受,中国诗人的整体生存面临评估,中国诗人的经济结构面临评估,中国诗人的社会身份面临评估,最后还涉及尊严。在这个世界迎娶新娘的时候,没有一种诅咒比对诗歌的诅咒更恶毒的了。
发言在深圳,诵读也在深圳。我记得那天在夜晚的寒意中陪伴诗人的不多几人中,我不记得是于坚还是谁说了那场寒冷简直是个阴谋。几天后,我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的“诗家歌”活动上也有片刻的停留,目睹了人们如何呼唤诗人下去。没有意外,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仍然是粗略的、无知的,诗歌照旧止步于写作者的领地;没有意外,诗在功成名就的古典主义师傅们眼里,充其量只是女实习生随手饲喂的牲口。由此,诗的实际命运必将和女实习生一样,人们并不因为她是处女,而为她加薪。
这世界已经演变成一张大床,人们不再承继私密的生活。有着金子般理想、不自认堕落的一群人他们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尽力控制住这世界继续下滑的速度。这个貌似悲观的人群,偏偏是莫名领了使命的写诗人。
悲观是一种美德,它转化为写作的态度,就是沉郁。中国新诗经历了三个30年,前30年、后30年都是沉郁的,中间的30年最为亢奋。不幸的是,最亢奋的30年诗歌对大众影响反而最大,最有害。人们把诗理解为朗诵,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异。世界一贫如洗,而朗诵附体的人们昂扬得个个有如人参。他们朗诵唐诗、毛诗,朗诵郭小川,朗诵前朦胧诗,造型别无二致。即便是在今天有人放言诗歌复兴的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些比比皆是的悬挂着红色横幅的朗诵会现场,纵使你是一大个儿,我也不得不把你往低了看。
有一些所谓的贵族,他们各立山头,巧取豪夺了当代诗歌实验的荣誉和果实,在我看来不少作品却不忍卒读。我在深圳的会议上提出过反对假写和写假诗的问题,反对自私的写作,提倡超越了公共经验之上的表达。回顾我本人的写作史,我从来没有爬过车皮,没有赶过任何一轮诗潮,没有参加过什么论战,但我决不反对“双百”方针。1989年公刘抨击大众写诗时,我记得我在《百家》杂志上写过《上厕所的人》以示回应。我深信,厕所于诗歌是有益的,然而那些假装的桂冠诗人们还是把诗歌带离了现场,带回了学院。诗歌,为什么不是劳动人民的写作,劳动者为何等而下之?他们不拒绝对财富的攫取,不批评物欲横流,没时间诅咒人生,活得能够像个■已是最高境界。一个置身普通人生的人,难道就不能写出牛逼的诗吗?就不能写出让你们看不懂的诗吗?
我喜欢那些放低了身段写作的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高高在上。他们住在798、住在崔各庄草场地。他们所在的村庄越来越小,那里既不是高尚的农村,也不是蹩脚的城市,村里懒洋洋地溜达着许多狗,即便是名犬,也还是一条狗。的确,我不认为你今天的写作,必须与唐诗宋词扯上关系;的确,我不认为你今天的写作,是与小说、散文等量齐观的劳动。诗,唯有逼近当下,才能留得更久。诗,不必去■学的浑水了,才能清者更清。我在80年代曾写过一首短诗《语法》:“从汽车的尾部,挨次拆下汽车的零件,拆到第几步,汽车不能开走。”诗人,就该做个少些零件的人,就该做个与神相交的人,做个至简的人、孤绝的人。韩东说我孤绝,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朋友比我更孤绝。
有许多诗已经过去了,我看到过一些选本。批评家如果不沉浸于缅怀中,他怎么才能够成就为学问家呢?许多诗人也已从善如流,成熟、睿智,成了公知母知,唯独不能成为作为诗人的他自己。
30年既然又掀一页,大师轮流做,吸血换他人,亲爱的朋友们,你必须忍痛割爱你钟爱的宝座了,相信会有神勇的少年派上得船来!但也好,好在诺贝尔奖已进步得仿佛金鸡百花,相信它一定会奖掖中国当代诗歌20年前的辉煌。
诗,会死。我赞成它应当成为少部分人的艺术,尽管它生殖于劳作中、生殖于黑色与血泊中。刚才我翻到一条微博,特别符合我目前发呆的心情,“因为寒风,因为河流冰冻,北方是强大的。因为枯枝,因为树干笔直,北方是强大的。因为污雪,因为阳光直射,北方是强大的。冬天,北方是一根裸露在原野上的骨头。”(@布格拉风 )北方,它断然不是南方;首都,它断然不是深圳。尽管活着的人们总是把所谓的5000年文明押宝在30年这座乳臭未干的城市上。
新诗,也是一根骨头。我赞成为它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