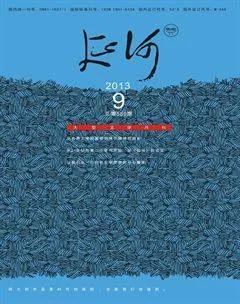我的身体,我的时代
从我的一首短诗《乞婆》说起
——兼谈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
趴在地上
蜷成一团
屁股撅着
脑袋藏到了
脖子下面
只有一摊头发
暴露了
她是个母的
真是好玩
这个狗一样的东西
居然也是人
这是我2000年写作的一首短诗,时至今日,这首诗依然不时被读者和诗人、批评家们作为“反面教材”提起。这是一首令我陷入巨大“道德困境”的诗歌,比我最有名的那首《一把好乳》遭受到的道德指控更严重。随便在百度上搜索关于这首诗的信息,就能查到很多“仁人志士”们对这首诗的口诛笔伐,比如“严重伤害了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心灵,以污秽的思想制造污秽的文字,其社会影响极坏!”,再比如“在这种文痞式的文字暴力背后,跳动着被他们糟践的生活在这个不公平社会里最底层的人们的心灵以及人类那仅存的,惟一一丝可怜的良心!用文字摧毁掉一个最无力最柔弱的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诬蔑一个底层的人就等于诬蔑世界上所有同样处于那种困境中的人们。”
十几年来,我从未对这类的道德指控做过任何解释,对这首诗“到道德为止”的解读,已成诗歌界内外的定论。
我曾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这样的诗歌应该会有更多的理解能力,应该会产生更多不同层面的解读——而不是耽于最肤浅的“淫者见淫”的义愤,但非常遗憾的是,哪怕是最欣赏我的写作的人,也从未提供过任何正面的解读,认为我写出了“人性之恶”,认为“恶”也是文学中的重要情感基础的,已经是最大程度上的对这首诗的善意理解了。
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诗人活在他的时代,长在他的时代,是从社会、时代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肉体和心灵,但当诗人长成为诗人,长成为独立的意志时,他拥有了自身的“个体写作”的决绝,因此也与社会性的公共表述发生了断裂。即使在面对同样的社会事实,在诗人把目光投射到非常具体的社会现象时,其内心的声音也永远是孤立的,是在集体话语和集体意志之外的,难以被“集体意识中的人群”所理解。
今天,我将第一次,对这首《乞婆》做出解释——打脸式的解释。我并不想打对这首诗做出反向道德解读的普通读者的脸,但我非常想打打那些对这样的诗歌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污蔑式解读的,所谓专业读者的脸。
如果我说,这首诗的写作出发点是基于最大的“善”,甚至是基于最深刻的“爱”,会不会令人跌破眼镜?我所呈现的,是我所目睹的事实,“这个狗一样的东西,居然也是人”,这是当我目睹作为“人”的尊严可以匍匐进“狗”一般的身躯时所发出的悲鸣。人为何成为人?当人失去成为“人”的全部时,人会成为什么?我所写的,是我目睹的乞婆,我所悲愤和质询的,是当人失去属于“人”的全部时的那种沉沦。这种沉沦,难道只会发生在肉体如此卑贱的乞婆身上?难道不会发生在所有腆胸凸肚的大人先生们身上?
而在对这样的诗歌发出各种道德解读的大人先生们那里,面对一个匍匐在地的乞婆,他们认为,一个诗人,只有发出同情之声,悲天悯人之声,关怀底层之声才是唯一正确的,这是取消了自由意志的集体道德对于诗歌独立性的反动,对于诗人独立意志的反动。而这种反动,甚至浅薄得无法解读出《乞婆》这首诗中比同情更深刻的悲恸,比悲恸更深刻的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诘问。这种悲恸和诘问,不是来自同情,而是来自同样作为人类的“同比心”。焉知我们自身,不会在某个时刻,丧失了作为“人”的一切,如这尘埃中的乞婆,匍匐如狗?“人”之脆弱,“人之类于禽兽者几希”的质询,是永恒悬挂在人格之上的铡刀。
诗人的个体写作在面对由集体形成的社会时,必然有其格格不入的部分,完全与社会解读融为一体的,一定不是真正的诗歌。像大众一样,依据某种道德和修养的模板,去批发同情、批量生产愤怒、复制各种良知——这会获得大众短暂的叫,但绝非真正的诗歌精神。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来自追求自由和独立意志的内心,它永远是个人的,有着不一样的心跳。
我在忙碌不堪的生活中写诗
我在忙碌不堪的生活中写诗,在很多人以为的庸俗世故的生活中当一个诗人。我曾经试图将作为诗人的我,与为了养家糊口而从事商业工作的我彻底分开。一度,我以为他们能够分开。每次,当我将内心从工作频道转移到诗歌频道时,仿佛都需要使劲一掰,嘎嘣一声,心惊肉跳。
在不断的写作,不断的与庸常功利,甚至必须抹杀思想锋芒的社会工作对抗的过程中,我的焦虑日渐增多。这种对抗性的焦虑,来自对自己内心的不信任。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质问和寻找,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到底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我?我会不会因为做不成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我而彻底完蛋?我被我的分裂搞疯了。至少是,曾经疯过。
但我活过来了。写作的过程亦是对内心的修炼。诗歌的目的并非为了抵达真理,但它需要抵达的是真理之后,甚至是真理背后——那些有无限广阔的,令诗歌的微妙之羽飞翔的空间。这是诗歌与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导向一种积极的虚无。而这,正是生活本身所同样正在试图抵达的。
生活与诗是一体的。生活中的一切与诗歌皆为一体。生活中之我与诗,自然也是一体。当区别心消失,诗歌的微笑,向我释放温柔而强大的力量。仿佛(其实就是真的)经历了一次艰难的修炼,我发现我真的开始热爱生活中的一切时,诗歌开始围绕我舞蹈,诗歌是空气,其中的生活饱满而充满质感。是诗歌令生活充满质感,而当我感受到生活的质感,诗歌才长出了更热烈丰厚的嘴唇。
写作无所不在,因为诗歌之箭随时会命中生活竖起的一个个移动靶心。作为诗人,我要做的只是,击碎靶心,让离弦之箭,穿越靶心之后,继续在微妙之境飞翔。
诗歌不是证道,也不是证道的过程。但其中包含着证道所带来的过程快乐与顿悟的快乐。另一方面,它又做鬼脸般揭发出证道的伪善与无聊。诗歌不排斥任何其他事物和精神,他有着虚怀若谷的热情。
于我,诗歌写作的过程竟构成了某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2000年到2012年,诗歌对我进行了长达12年的教育。直到今天,我才敢侥幸的说,这种教育正在我身上初见成效。我目睹着自己经过了非常艰难的跋涉,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2008到2009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想明白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写作了后来带给我巨大荣誉的长诗《蝴蝶》,当《蝴蝶》写完,我仿佛真的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清算,甚至觉得,自《蝴蝶》写完的那一天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诗歌无时无刻不在对我的生活发生作用。诗歌写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生活本身亦是一种自我教育。当两种教育开始在我身上展现出默契的融合,我突然觉得,也许,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写作即将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无论如何,我都明白一点,我要写的诗歌是离生活最近的诗歌,我的诗歌与具体的生活的距离,就是我与真正的诗歌精神的距离。
我的身体,我的时代
——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获奖感言
如同世纪初喧嚣一时的“下半身写作”带给了我长达十几年的“身体写作”的标签一样,近年来,随着《文楼村记事》、《河流》、《玛丽的爱情》等诗歌重新被文学界反复提起,这次甚至又因为《文楼村记诗》的同名诗集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个“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崭新标签逐渐往我身上贴来,大有取代“身体写作”标签之势。
我不喜欢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诗人沈浩波,但也并不打算拒绝,甚至还有些欢迎这些叮叮当当的标签。对于某些患了辨识无能症的专业诗歌读者,有了标签,他们才知道,该把我放在诗歌论文的哪一个角落。我甚至有时会恶作剧般的想,“民间立场”、“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批判现实主义”……我在漫长写作的一生中,最后到底会挂上多少勋章般的标签呢?我会在衰老时,会把它们串成风铃,悬挂在心灵的枯海上听响儿取乐吗?
标签固然会遮蔽一个完整的诗人,但也能凸显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于我而言,身体、时代、人性,确实构成了这么多年写作的关键词。这一定不是刻意选择的结果,每个诗人,都有一种内心的本能,让他的触须天生会向某些方向伸展。我有三首最著名的诗歌:《一把好乳》、《文楼村记事》、《蝴蝶》。其中《一把好乳》无疑代表了我诗歌中身体性的一极,它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流传最广泛的一首诗,这当然是建立在巨大争议的基础上。它至今仍然是我自己所有的诗歌中,私心最爱的。懒得去理会那些无聊得近乎肮脏的道德解读,这就是一首饱含着强烈生命意志的诗。身体的琴弦,铿锵的节奏,这是生命之歌,由身体而生命的礼赞!无论《一把好乳》受到怎样的争议,我将用我一生的写作来为其正名——这就是一首杰作!而《文楼村记事》则当然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了,也可能是新世纪以来在诗歌介入现实方面做得最好的一首,当代诗歌介入现实和时代,确实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如何既表达出现实与时代的切肤之痛,又不伤害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我以为,恰恰是我的诗歌中那种对身体感的强调,让我在不经意中完成了《文楼村纪事》的技术处理。什么叫“切肤之痛”,就是要贴肉,贴着肉写,写出贴着肉的疼痛感。“身体写作”与介入现实与时代,这中间有着天然的统一。如果说《一把好乳》和《文楼村记事》恰好分别成就了我的两个标签的话,那么《蝴蝶》则是一首无法被标签化的长诗。它既是口语的,又是意象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抒情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身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自我的,又是人性的——它是我此前所积累的所有写作经验、情感经验和思考经验的一次集中爆发,我觉得它干得不错,配得上是一首真正的长诗。但无论怎样综合,怎样跳跃腾挪,它都依然也只能直指我个人写作的核心方向——身体感、时代性和对人性的探掘。
我一直觉得,2011年颁发的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应该给我,应该颁发给2010年刚刚出版了长诗《蝴蝶》的作者。但世事总是这样,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臻于完美的事实发生,它总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没有因为2008—2009年写作的《蝴蝶》得奖,却因为2004年写作的《文楼村记事》得奖了,这对我来说,不完美,但却更美好。这样的认可能够重新擦亮《文楼村记事》,我不小心在2012年以《文楼村记事》为书名出版了一本诗集,而这本诗集却因为这首同名诗歌获得了评委的认可,这种认可又再次让这首诗收到更多的关注。贴着“新批判现实主义”标签的这首《文楼村记事》,比我自己更像一个幸运儿。
诗歌中的身体性,强调的是个人生命意志的在场,强调的是具体的贴肉的体验,亦是强调一种有身体的诗歌,自身具备血肉,有生殖力的原创;而诗歌中的时代与现实,则是个人与世界碰撞时,世界对于个人内心的反哺。诗歌永远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经验,但个人在时代中,个人在现实中,诗人对于时代现实的介入过程,亦是其个人内心的丰满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我身上的这两个标签,加起来也许正是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无法割裂。
时代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人,一刀一刀雕刻我们的精神,勾画我们的身体。但诗人一旦形成了个人的生命意志,就绝不能任由时代之刀将自己如同木偶般随意刻画,他终究要完成自我的生长,在强烈的不肯屈服的意志下向着内心自由的方向生长。这种生长固然艰难,没有人真能战胜时代,但反抗即是尊严,这种尊严构成生命的意义。
好在,诗人是最原始的创造者,他创造诗歌如同创造世界,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彼此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同时完成了对自我的创造。这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于写作的理解和理想。时至今日,我满意于我确实走在这样一条反抗与创造的道路上,诗歌使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拥有更自由不屈的内心,如果没有诗歌,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甚至,是否能够活成一个“人”——而不是时代的奴隶和命运的傀儡。
最后,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所有组织者和工作者,感谢推荐我的初评委,感谢所有终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