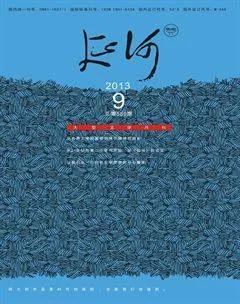散文的回归与创新
《延河》 6、7、8三期连续推出王维亚先生关于碑刻书法的长篇散文,读了令人眼睛一亮。王先生的三篇大作,闪现出诸多璀璨夺目的亮点,颇值得一说。
其一显露出散文的回归与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纯散文的出现是魏晋以后的事,至唐宋慰为大观。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桐城派”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散文家,都想把散文推向极致,到了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号称“南秦(牧)北杨(朔)散文名家,总算把散文推向了极致,但因程式化,即“引出——描述——联想”,千篇一律的“三段式”,终于把散文引向了绝路。王维亚的书法碑刻散文,跳出了“三段式”创作樊篱,用自己多年对书法研习的“自得”之见,挥毫时的“自由”之笔,酷爱书法的“自然”之情,以及临摹创作中萌生的“自在”之趣,一一彰显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这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创新。
其二突显了散文如水,贵在自由散漫的特性。李涂在《文章精义》中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把散文比作水,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了散文的特性。王维亚的这三篇散文正像涨潮的钱塘江一样,咋看无什么章法,但却真正突显了水的特性:滔滔汨汨,无间无隙,绵长贯通;性上自然,随物赋形,自然贴切;顺势而泻,波澜起伏,委婉磅礴。
其三,王维亚的三篇习作为作家学者化起到了个示范作用。审视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作家学者化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纵观中国历史,作家能够学者化,也必须学者化才有出路。先秦散文,诸子百家哪一位不是学者?唐宋散文八大家,又有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朱自清等人个个不都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么?作家一旦学者化,他的价值取向就会独特而科学。首先他们能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其次把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权威,同时依据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再次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不同于以任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这三个层面应既是学者的本质内涵也标志着学者的最高境界,同时还廓清了学者和有知识有文化人的界限。
统观王维亚这三篇散文,无疑是作者多年研习秦地历史上碑刻和书法大师的成果展。三篇散文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面对众多的碑刻和书法瑰宝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同时读者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解读这些碑刻书法时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更能领略到作者所具备的带有某种学者色彩的人文情怀。
清人周济论创作时说:“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王维亚从总体上把握审视秦地先贤大师们留下的碑刻书法,在进行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准确地把握了“入”与“出”的辩证关系。“入”则让读者得到了除碑刻书法审美经验之外的许多宝贵的历史事实;“出”则又让读者感到王维亚站在一定的高度,或大胆指出先贤们书法的不实之论,或用“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等戏称封建时代的士人和官员,就像毛泽东在一篇新闻中称“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身于南阳一带”一样诙谐、有趣、生动,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纵观古今中外,不论历史题材创作,还是其他文艺创作,甚至包括文艺批评,都存在一个“入”与“出”的关系问题。没有“入”便没有“出”,但光“入”不“出”也不行,只有先“入”才能后“出”,才能做到“入极而出”,“入透而出”。在这一点上,王维亚不仅做了个尝试,更是做了个示范。这无疑又是这三篇散文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