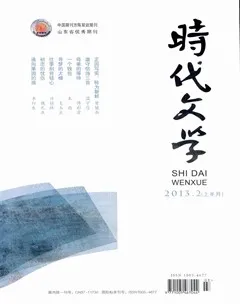为奴隶的隐忍
摘 要: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通过聚焦一个封建社会下典妻的生活状况,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在中国社会里穷苦妇女这一角色的悲惨命运。作者用细腻独到的笔法,捕捉这些命如奴隶的女性的生活剪影,组成一幅幅让人不忍卒读的血泪隐忍。笔者将就柔石笔下“春宝娘”这一形象展开论述,探讨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妻形象,极其背后的人道主义内涵。
关键词: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典妻;隐忍
一、《为奴隶的母亲》的创作背景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写作于三十年代初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或“轰毁”或退却的种种痛苦选择,知识者个人与革命的思考己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朦胧呐喊;而且1928年提出“革命文学”口号,一个崭新而令人兴奋的革命题材,正在强烈地吸引着许多进步的年轻文学家,从革命的角度观察人、研究人逐渐成为与五四文学划分界线的重要标志之一。[1]当时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革命+恋爱”这一小说形式风靡一时,使得作品中出现了口号政治化和人物脸谱化的简单化倾向。
柔石在这一时期却未跟风。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反映的浙东地区典妻风俗,如果出现在“个性解放”的五四时期,并不令人奇怪;但是,柔石似乎并未产生新的时代感觉,仍然重复着10年前“典妻”的老题材,沉溺于单一的狭小的“生的苦闷”之中。[2]这不同于同时期殷夫、冯铿等的“激进”创作题材。但是其所创作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将对人性复杂的关注和特有的人道主义关SqzdSaqQbMW33wTdb+hgcw==怀融入作品,为此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典妻形象的独特性和代表性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它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记载。到了清代,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典妻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名称各不相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典妻现象的存在,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又羞于启齿。[3]
典妻形象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若说中国自古女子地位低下,那么这种低下的表现就在于妻子尽管作为婚姻双方中的一方,却无主动地位,富贵人家中正妻要容忍妾室,穷苦人家中妻子则极有可能因贫困而被丈夫买卖,或入娼,或为典妻。然而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下,典妻要忍受的不只是易夫的内心煎熬,更有契约到期时,和承典夫家儿子的分别的难舍,以及回到原来丈夫家受尽白眼的羞耻,这种多重的折磨,使得典妻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摧残,同时也使得典妻这一形象具有独特的悲剧性。
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作者选择南方一隅的典妻风俗,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度下典妻的形象,她身上浓缩了所有典妻几乎相同的特点,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在乡下的丈夫家过着贫苦卑贱的生活,被典入秀才家里,又要作为一个生育的工具和“妾”,寄人篱下,任人摆布,遭受正妻的指使和被赶回旧家的经历,以至于和自己的一个儿子分别。这些农村妇女,我们连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在作品中,只知道这位母亲叫春宝娘,因为春宝是她的第一个儿子。
柔石的笔下,春宝娘这个形象蕴含的不止是典妻命运的悲苦,更折射出了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女性因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被忽视和践踏的人性。然而柔石并未一味痛斥这种制度,而是在一开始便分析了造成这种制度的原因,即当时落后的农村经济和小农思想,正如文中所提到的: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祥,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狼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
春宝娘的丈夫并非无能,家境在一开始时还算殷实,但由于其丈夫小富即安,缺乏自律,败光了家产,才沦落到穷困潦倒、苦不堪言的地步。一家人不能糊口时,使得女人地位的低下就充分体现出来,卖妻卖儿的现象便开始滋生,这便是《为奴隶的母亲》的深刻所在。只看到典妻制度,只是一个表面,应当挖掘其背后的成因,而作者这么写,也正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细节中表现隐忍
《为奴隶的母亲》中善于通过细节对典妻“春宝娘”进行刻画,从而展现母性痛苦。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细节描写,将春宝娘的遭遇展现淋漓尽致,而这一描写,又非夸张的浓墨重彩,而是选取了母爱这一出发点,以细节母爱观之命运,无限悲戚不言而喻。
譬如文中这一段:
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底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底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底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单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
对于这样的情景,春宝娘尽管心如刀剜,但仍是默默哀叹:“唉,苦命讶!”她没有起身反抗,因为受到落后的封建理念的影响,女人天生就是从属于男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力,所有的母爱也只能尽数归于内心的折磨。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春宝娘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将这种隐忍变作一种习惯,而这种摧残和泯灭了中国女性几千年的无知的隐忍,才是最让人心痛之处,所以对于下层劳苦人民的同情也因此生发。
再有这样一个细节,春宝娘听说春宝生病,将秀才给她的青玉戒指给了前夫典当,被秀才发现后他们之间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没有借你五快钱么?”秀才愤怒地。
妇人低着头停了一息答:“五快钱怎么够呢!”
秀才接着叹息说:“总是前夫和眼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
秀才并没有关注春宝娘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疼爱,而是将这种疼爱绑定在她的前夫身上,认为她的内心是从属于前夫,而非自己,这是中国古来有之的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尽管,作者没有把典妻者写成一个荒淫好色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而是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识礼、文质彬彬的秀才,他平时并非一个穷凶极恶的嘴脸,甚至对春宝娘温婉关心,但是并不是将她真正的作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而是对于一种玩物的占有,春宝娘想着大儿子,便是想着以前的家,由此便是想着前夫,秀才这种病态的认知基于对自己尊严维护,即使其人性的复杂,也是陋俗和封建观念的深刻表现,春宝娘在这种不受理解的境况下,并没有更多的为自己辩护,她或许不知道一枚青玉戒指对自己接下来两年命运的影响,这是她作为农村妇女的憨厚愚钝,试想她若是一个机灵多心的人,那么她或许会将那枚青玉戒指保留,然后顺着秀才的心思,说不定可以多过几天好日子,但是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母爱的本能,由于对春宝的思念和爱护,她将手上值钱的东西拿去给丈夫典当,为春宝看病。可是在秀才不理解她的时候,她只将所有痛苦隐藏起来,兀自“一天天地黄瘦了”。
这是一个作奴隶的母亲,无助的在命运中挣扎,经受着来自周围环境的折磨,无论是皮匠丈夫、秀才、秀才娘子有意的折磨,还是春宝三年之后不再认她的折磨,她都摆脱不了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摧残。春宝娘的一生展现了旧社会妇女只能作为被卖物品、生育工具而存在的悲剧现实。自然,悲剧的形成在于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4]
但是春宝娘的最痛苦之处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同,祥林嫂受到的精神上的摧残主要来自于贞洁问题,不论是无论嫁给祥林,还是嫁给贺老六,或者到了鲁家做长工,祥林嫂都能有生活的基本保证。而《为奴隶的母亲》在一开始便介绍了春宝娘的生存条件,她是一个由生计所迫的女性,在这种生活背景下,她能所想的已经并不是只停留在贞洁问题上,而是因两个孩子不能同时在她的身边所形成的一种矛盾心理,这边是秋宝,那边是春宝,都是自己的孩子,抱着一个却丢着另一个。所以这篇同样控诉封建制度对女性精神摧残的作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女性的悲苦命运,即母性和母爱的角度。祥林嫂是因贞洁问题而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而春宝娘所面临的却是不仅没有劳动权,甚至连为人母的这样最基本的动物的权利也要被剥夺。
四、总结
作者塑造了春宝娘勤劳朴实的性格,和她凄惨的命运,三年前,她舍不得孩子春宝,却无力反抗;三年后,在秀才家生下孩子秋宝,却又被迫回家。无论哪个时期,她都生活在矛盾中,生活在“不情愿”中,生活在折磨的痛苦中,两个孩子也终将离她而去,当一个被剥夺的仅有母爱可以依存的女性连母爱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的时候,她成了一具空壳。
柔石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以其人道主义的视角和冷峻的笔触描写了典妻制度给劳动妇女所造成的难以名状的精神虐杀和心灵创伤。我们感受到细节中流露出的对下层人民关怀,应当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思。
注释:
[1]丁言模,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创作成因的考察——纪念柔石烈士牺牲60周年,《社会科学》1991年第08期。
[2]丁言模,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创作成因的考察——纪念柔石烈士牺牲60周年,《社会科学》1991年第08期 。
[3]典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9928.htm。
[4]张小萍,从《为奴隶的母亲》看旧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0年05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