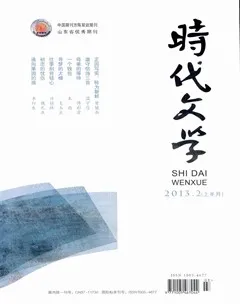浅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隐喻能力的培养
摘 要:隐喻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能力,也是人们熟练掌握一门语言的标志。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重视隐喻能力的培养,将有助于学生思维的流畅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本文试图从词汇教学方面讨论外国学生汉语隐喻能力的培养,来寻找改善汉语词汇教学的新途径。
关键词:隐喻能力;词汇教学;对外;汉语
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还是在精心雕琢的书面语言中,都有不少隐喻的出现。隐喻又是一种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哲学家关心如何建立隐喻认知的完整理论模式;语言学家关心它对语言的阐释功能;而作为汉语教师的我们,则应该关注其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隐喻沉淀于语言中,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指出,根据语言事实,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的大多数概念系统实质上都是靠隐喻来表达的。那么汉语中,也必然存在众多的隐喻词汇。对于一直处于母语环境下的本族人来说,理解这些隐喻词汇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对于那些靠推理来习得汉语的外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瓶颈。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会有学生被这样那样的隐喻性词语难倒,比如“首脑”“吃醋”“跑龙套”“打酱油”“月光族”等等。但当前,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隐喻能力培养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词汇教学中隐喻能力的培养,以寻找改善词汇教学的新途径。
一、隐喻能力
(一)隐喻。
说起隐喻能力,就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隐喻。20世纪八十年代,Lakoff 和 Johnson 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隐喻:隐喻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本质上是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 目标域是认知和理解的对象,始源域是用来认知和理解目标域所借助的概念。[1]其实说白了,就是 “用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个事物”。其中“理解”即“认知”,指明了隐喻的功能。这也基本已经是当代语言学者公认的定义。
(二) 隐喻能力。
“隐喻能力”一词最早由Pollio & Smith提出来,而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的是Danesi。他认为“隐喻能力”指的是在说话和写作过程中使用和辨认新隐喻的能力。隐喻能力包含两个方面:语境适合性和操作性策略,前者指对目的语中隐喻概念所包含的心理影像的识别能力,后者指在交际中正确使用概念图式的能力。根据Bachman(1990)的交际能力模式,Littlemore对隐喻能力的内涵作了更加合理的探讨,他阐释了隐喻能力的四个方面:(1)隐喻的原创性;(2)隐喻阐释的流利性;(3)理解隐喻含义的能力;(4)理解隐喻含义的速度。王寅在他的《认知语言学》中也指出,隐喻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认知主题中的,能够识别、理解和创建跨概念域类比联系的能力,这里不仅包括能被动地理解、学得隐喻,而且还包括能创造性的使用隐喻的能力;更高目标还可包括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的创新思维能力。[2]虽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对于隐喻能力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从上面各位学者的观点概括,隐喻能力就是在交际过程中,能够识别、理解、使用以及创造隐喻的能力。
二、隐喻能力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一)隐喻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词汇教学都在汉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教学实践中重要的环节之一。然而很多学生获得第二语言的概念流利性差,在利用隐喻构筑目的语的概念方面缺乏系统训练,由此导致虽然已经学会了很多汉语词语,但却经常在理解、运用上存在众多偏误,学习兴趣低下,信心不足,语言表达干涩乏味。由此,探讨如何提高学习者隐喻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也都将语言教学中隐喻能力的培养放在了一定的高度。国内学者束定芳等指出,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语言教师可利用隐喻理论来解释语言意义的变化发展过程,解释词汇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3]王寅先生在《认知语言学》中把隐喻与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的培养并称为“三合一”的语言教学观。他认为,隐喻不仅是一个帮助我们丰富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创新思维、语言习得密切相关。因此在语言教学中除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之外,还应加上隐喻能力。因此,在我们的语言教学大纲中,应充分体现出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最新观点,认真考虑“隐喻能力”培养的具体方案、内容、举措。[2]
(二)汉语词汇教学中培养隐喻能力的方法。
如何将隐喻应用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或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如何培养隐喻能力呢?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1、 培养隐喻意识,引入隐喻理论。
隐喻意识即语言学习者对语言形式及功能的察觉程度和敏感程度。首先我们要使学生意识到隐喻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网络报刊等媒体,还是日常交流,隐喻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常常要通过隐喻这种丰富形象的表达方式去深刻理解目标域。其次,我们要使学习者明白,隐喻是语言的一部分,是了解目的域语言文化,进行语言扩展和认知发展的有力工具。那么学生便会逐渐有意识地使用隐喻来辨认和理解词汇中的隐喻模式。另外,我们还要引入解释隐喻的理论,如王寅先生的“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本体、喻体、主体、喻底、语境。引导学生在本体喻体化解矛盾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统一。
2、 积累常规性隐喻。
隐喻的理解过程涉及两个域:始源域和目标域。人们根据自身熟知的始源域,通过意向图式进行推理,以找到始源域和目标域相关的特殊结构。这就意味着学习者要掌握始源域和目标域足够的信息,把握一词多义,才能进行理解。美国教学法专家王士元先生说:“理解语言的过程是一种猜测、估计、预想、想象的积极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用具体的、简单的形式来反映、表达抽象的概念和事物,由此汉语词汇具有意合性、联想性、巨象性的特点,很多词汇都是由隐喻发展而来。这也使得很多外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识其形却不知其所云”的现象。由此,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培养学生根据原有的图式,用联想的方式去猜想理解词义就显得比较重要。而联想方式必然离不开常规汉语隐喻词语的积累。很多学生学习汉语多年,但是无论在描写、说明、讨论,还是抒发情感,都不善于使用喻化的语言。为了表达的丰富性和良好的言语效果,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学生要注意收集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词语,积累已有的表达方式和常规隐喻,以丰富自己的表达。教师可以将事先按照隐喻的种类分列出若干专题,比如颜色、时间、情感、运动等。再让学生分组按专题搜集,课外分别讨论专题相关的词汇的隐喻意义和用法。讨论后每组以PPT的形式向全班汇报,教师进行补充和总结。另外教师需要注意在教授词语时,不要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还应该对其内涵义隐喻义有所提及,建立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使学生逐渐形成词汇的完整隐喻概念,帮助其形成词义扩展的能力。
3、注重目的语与母语中隐喻词语的差异,激发母语正迁移。
人类具有很多共同的知识和经验,学习者对于母语和目的语中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隐喻词汇很容易从字面上分析出隐喻含义。比如喻体喻意完全相同的:汉语中“瞳子”原指“瞳子”,得名于瞳孔中有孩童(人像);英语不谋而合,“pupil”一词原意“孩童、小学生”,由这同一喻体,pupil也做“瞳子”解。这类完全等值的词语还有“脚注=footnote”、“兔唇=harelip”、“耳鼓=ear-drum”、“笑柄=laughing”、“一线希望=a ray of hope”。这些词之所以容易习得,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母语产生正迁移。作为汉语教师,可以利用通过汉语与学生母语的共通之处,激发学生的母语正迁移。
但是民族文化都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隐喻也往往受着民族文化色彩的制约。这也使得各种语言之间的隐喻词汇的概念系统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所以,并不能单纯的用母语中的概念系统去任意理解目的语的隐喻词语。比如张德鑫在《中外语言文化漫议》中举过这样的例子:汉语中的“儿戏”和英语中的“child’s play”,字面上看酷似,但各自的意义却差之千里。汉语“儿戏”比喻对工作或事情不负责不认真,如“不能拿工资任务当儿戏”,这一义项在英语中的对等对应词是“trifling matter”。而“child’s play”在英语中的本义则是“something very easy to do(轻而易举的事)”,如说“Driving a car isn’t child’s play even when you’ve had practice(就算你以前练过,开车也并非容易)。”它还表“something not very important(不太重要、不足挂齿)”,如说“His illness is child’s play when you think of how serious it might have been(他的病本来可能很重,现在不要紧了)。若将此句5ba49bc837195a8facbd01200c2f85b6中的“child’s play”译成“他的病本现在如同儿戏,肯定会觉得费解和可笑。可见,“儿戏”含贬义,而child’s play 本身不带负面意义和功能。[4]由此例我们就可以看出,语言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由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让学生知晓汉语隐喻词汇与其母语间的差异尤为重要。
4、利用语境理解隐喻词义。
学习是为了应用,由此我们的教学也应将学习上升到语用的层次,定位到隐喻词语的最终使用中,尤其是在语境中的使用。汉语词汇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而语境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词义和词性,也可以显示词语的搭配习惯及语体使用风格。克拉申曾指出,人类获得语言的最重要的方式是对信息的理解,通过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来获取语言知识。因此,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教师除了帮助学生积累常用的隐喻词语,还应该精心选择和设计隐喻词语使用的具体语境,尽量使其与学习者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或学生感兴趣的点,也就使得学习者在有用的新信息接受中体会词义和用法。同时,又可以在不断的反复应用中比较准确的理解隐喻词语的含义,加深记忆。比如:“这周天天开夜车,才把这篇稿子赶出来。”单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开夜车”,很容易就认为成是“晚上开车”,可结合上下文语境,这个意思明显说不通,而应该是“为了赶时间,在夜间继续学习或工作。”
5、加强文化输入,文化与隐喻互促互进。
“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际,在真实自然的交际中,言语信号是快速呈现的,是转瞬即逝的。这就要求接收、解码5ba49bc837195a8facbd01200c2f85b6高速进行。速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5]而社会文化知识就是影响接收、解码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隐喻如同语言一样,也是深深扎根于社会背景、文化知识之中的。各民族隐喻词汇由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等的不同也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汉语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词语宝库,古代的诗词歌赋、成语惯用语中都存在着各种汉语民族文化特有的隐喻词语,比如“二百五”“狼子野心”“吃醋”“跑龙套”等等。这些词语也直接构成了外国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障碍,影响他们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所以教师在教学中,碰到有言外之意的汉语隐喻词语时,不仅要将字面意思讲解清楚,而且也要对隐喻词语具体的文化语源层层剖析,系统的阐释隐喻词语,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地把握隐喻词语的概念和语言事实,甚而进一步地判断理解当代汉语中鲜活的隐喻词语。比如,汉语“红糖”不“红”的现象,是与中国哲学讲“虚”和“贵在神似”的文化相关联。而西方文化重视科学精确,“红糖”则采用了“brown sugar”的说法。再比如汉语中“龟”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左传》中有“龟兆告吉”之语;“龟旗”在战国中为大将之旗;唐代初品官戴的是龟,古代府第、庙宇等建筑物前也常有石龟。成语“龟年鹤寿”“龟龙麟凤”则更是把“长寿”“美好”的象征表达出来。而在明代以后,“龟”的名声大变,常用来比喻“有外遇者的丈夫”,于是骂人“乌龟”“王八”就变成了极大的侮辱。而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的联想。乌龟也只不过是行动缓慢、其貌不扬的动物而已。教师要将隐喻词语中本国与外国的文化差异讲清楚,讲透彻,让学生在熟悉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逐渐培养起跨文化意思和中国式思维,用联系的方式掌握好相关的隐喻词语,避免理解和运用上的混淆。
6、加强对隐喻能力的拓展,广泛阅读含有丰富隐喻的语言资料,不断更新自己的隐喻词库。
掌握隐喻能力,不仅要学会识别、理解隐喻词语,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用甚至创造隐喻词语。由此,我们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含有丰富隐喻表达的语言材料,尤其是汉语诗歌、小说等,并增加适量的汉语与其母语的隐喻词语对译练习,鼓励学生交流和写作时运用隐喻词语,加大隐喻输出频率,丰富表达。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生适时复习,在学习接触新的隐喻词汇的同时,以旧知带新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断更新学习者大脑中已有的隐喻意象图式,提高词汇理解能力。
参考文献:
[1]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国教育出版.2007
[3]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外国教育出版.2000
[4]张德鑫.语言文化漫议[M].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5]杨惠元.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