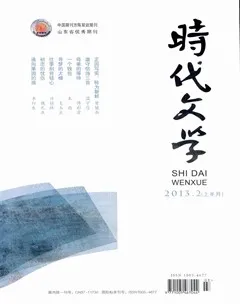浅析《纯真博物馆》的忧伤主题
摘 要:“呼愁”意为忧伤,是土耳其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呼愁”一词在《古兰经》中主要指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化中指因沉迷世俗、物欲而感到忧伤,因替真主所做的事不够而感到忧伤,因无法完全接近安拉而忧伤。“呼愁”是帕慕克创作的主要艺术风格。本文拟从“呼愁”入手解读帕慕克新作《纯真博物馆》中的三重忧伤主题,即为土耳其文明的衰落而忧伤、为求而不得的爱情而忧伤、为自我身份的模糊而忧伤。
关键词:“呼愁”;忧伤;文明之伤;爱情之伤;身份之伤
“呼愁”意为忧伤,是土耳其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公元594年,穆罕默德的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理雍双双去世,那一年被称为“忧伤之年”。“呼愁”一词在《古兰经》中出现过五次,主要指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化中,“呼愁”指一种生命的悲悯意识:因沉迷世俗、物欲而感到忧伤,因替真主所做的事不够而感到忧伤,因无法完全接近安拉而忧伤。[2]86 “呼愁”是帕慕克创作的主要艺术风格,他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题无不散发着忧伤气息。
出版于2010年的《纯真博物馆》是帕慕克获奖后的最新作品,此书历时十年写成,被帕慕克称为他最柔情的小说。在书中,他倾注了一生的情感,以细腻感伤的笔调,讲述了主人公凯末尔的爱情故事,探讨了究竟什么是爱?怎样收藏爱?如何平复爱的痛苦等问题,同时以丰富的细节和意涵展现了伊斯坦布尔往昔的一切。全书文字以忧伤作为基调,讲述生活在忧伤城市中的忧伤之人所经历的忧伤爱情故事,散发出浓浓的忧伤气息。本文将从“呼愁”这个概念入手解读《纯真博物馆》中的三重忧伤主题。
第一重忧伤:忧伤的城市——土耳其文明的衰落之伤
一座都城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的缩影。在小说主人公凯末尔疯狂寻找情人芙颂的那段日子里,我们跟随着他的足迹跑遍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体验到在现代化进程中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忧伤。伊斯坦布尔的忧伤源于土耳其文明的衰落,体现在作家心中那深深的失落感。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永远占据主导地位,经历辉煌之后总会渐渐衰落。伊斯坦布尔曾经是代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主要城市,同时也承载着辉煌湮灭后的泣血历史。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之下,土耳其文明呈现出日渐衰退之势。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西化改革沉重打击了奥斯曼文明,只留下了一些帝国的废墟、遗迹。比如小说中提到的“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躲避整个世界的皇宫、皇宫里的大花园和里面的宅邸,在共和国建立后变成了有钱人家开车游玩和新手学车的一个公园。”[1]453-454以及芙颂参加交规考试时去的贝西克塔什的一个小皇宫,“那里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疯儿子努曼王子为了打发时间听后宫女孩弹乌德琴,画印象派海峡风景画的地方。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变成了一个暖气始终烧不热的政府机构办公楼。”[1]459外物的毁灭即使是彻底的但也不能根除精神上的遗留物,特别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并一直亢奋着的精神构件。[3]21对于天天生活在这文明废墟中的人来说,感受到的只是无奈、不安和深深的失落。废墟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孕育过灿烂的文明,同时也提醒人们,眼前贫穷杂乱的城市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繁荣、辉煌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忧伤啊!
全盘西化的改革完全否定了土耳其本土文明的价值,使得土耳其人心里感到无奈、无助、无所适从,内心埋下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在小说中,帕慕克详尽地描述了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虚伪、做作的所谓“西化”生活。他们喜欢像欧洲人那样旅行、滑雪,喜欢从尼斯带回阳伞,喜欢从欧洲购买名牌时装,喜欢炫耀自己是土耳其拥有电动搅拌机、开罐器或电动剃须刀的第一人。他们急切地从欧洲带回制作蛋黄酱的机器,却发现在土耳其没人能向他们供应这一机器的备件,于是这些作为新事物的伟大代表的机器很快就成了被遗弃的废物。他们在生活中一切向西方看齐,西方就是先进、文明、开化的代名词。如果一个人想表达对另一个人的轻蔑,他会说“太土耳其了”。然而在涉及像女子“童真”这样的敏感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又是那么游离不定,令人捉摸不透。帕慕克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人类学”[1]64问题。
1975年以后,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地中海以南和以西的那些地方,年轻女孩们的“童真”,仍然是婚前必须保护的一份珍贵宝藏……那些拥护西化的人们,随着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乐观地相信这个道德,甚至是这个问题将会被遗忘。但是在那些年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西化和富有的阶层,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和一个男人“走到最后”地做爱,依然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1]64
在对待女子“童真”的问题上,这些“西化”了的土耳其人也感到矛盾和棘手。一方面,他们渴望像西方人那样享有充分的性自由,敢于婚前做爱被标榜为“自由和现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对于性问题的禁忌态度的影响,他们又害怕婚前性爱会影响到以后的婚姻生活。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使他们常常倍感困惑,呈现出一副欲拒还迎的姿态。书中的努尔吉汗是上流社会一个标准的“西化”女孩,在法国上过学,和法国男人上过床,衣着大胆、作风开放,可是回到伊斯坦布尔要谈婚论嫁时,却拒绝和未婚夫麦赫麦特婚前做爱,因为害怕被轻视和抛弃。凯末尔的未婚妻茜贝尔虽然勇敢地忽视了传统和未婚夫婚前做爱,但也是在认定对方是认真的、可以依赖的,相信对方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交出去的。“那些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喜欢把这种和未来的丈夫人选婚前上床的行为,一方面解释为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解释为忽视传统的现代和自由。”[1]64而凯末尔的情人、少女芙颂在婚前就与一个无意与自己结婚的人上床无疑是冒险的,偷尝禁果的代价是她成了一个失去贞洁、没什么可炫耀的女孩,后来草草嫁给了自己根本不爱的邻家男孩,过了八年无爱的婚姻生活。在此,帕慕克表现出对土耳其人在价值观方面的盲从的隐忧。
芙颂的丈夫费利敦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电影人,一心要拍出一部真正的土耳其艺术片。可是在西方电影的围攻下,土耳其本土电影业迅速凋敝。电影人纷纷失业,本土电影无人问津。无奈之下,导演们只好迎合市场拍一些爆米花式的商业电影或隐晦的色情电影。小说的末尾,曾经充满梦想、立志成为艺术片导演的费利敦改行做起了广告公司。帕慕克用这个事件来表达了他对本土文化遭遇冷落的忧伤和忧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和日益衰落的土耳其文明,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土耳其人又该如何自处?帕慕克用他独有的忧伤的语言对这座忧伤的城市中失落的文明做了最淋漓尽致的诠释。
第二重忧伤:忧伤的爱情——求而不得的爱情之伤
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化中,“呼愁”指一种生命的悲悯意识:因沉迷世俗、物欲而感到忧伤,因替真主所做的事不够而感到忧伤,因无法完全接近安拉而忧伤。小说用细腻感伤的笔调描写了凯末尔对芙颂疯狂的迷恋、漫长的追求以及最终的失去。这种求而不得的忧伤贯穿小说始终,蔓延到字里行间。
小说以忧伤的语气展开了叙述。“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1]1这个充满忧伤和悔恨的开头奠定了全书忧伤的基调,向读者暗示了这段爱情的求而不得和注定失去。主人公凯末尔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管理着父亲的进出口公司,是70年代典型的西化了的土耳其人。他在物欲横流、虚伪做作的上流社会里浸淫了30年,“自我”中的“神性”早被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重重包裹不见天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私地将深爱他的少女芙颂“囚禁”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他的秘密情人。直到有一天,他如期与门当户对的茜贝儿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仪式后伤心欲绝的芙颂离他而去,他才开始正视他对她的感情,开始和灵魂深处的那个自己对话,开始明白爱情的真谛。
帕慕克说,“真正的爱情痛苦会扎根于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点上,会从我们最柔弱的地方紧紧抓住我们,会和其他所有痛苦紧紧连在一起,以一种无法被停止的形式蔓延在我们的全身和整个一生。”[1]287芙颂离去后,凯末尔陷入了对她的疯狂思念中。他整日幻想芙颂的容颜,回忆他们欢爱的场景,并追随着她的影子和幽灵深入到另一个穷困潦倒的伊斯坦布尔,发疯般地寻找她的踪迹。他深切地感受到爱情的痛苦,那种求而不得的忧伤在他体内逐渐扩散开来。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正常生活,无心打理公司业务,甚至无法和未婚妻做爱。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家人、朋友眼中的“异类”。自此,凯末尔开始了缓慢的回归“纯真”的漫长历程:撕毁与茜贝儿的婚约,远离“欧化”的上流社会,每个晚上都去陪伴芙颂及其家人,在他们朴素的公寓中看电视消磨时间。在小说中,他为了再次靠近芙颂,置伊斯兰恐怖主义、军事政变于不顾,深入伊斯坦布尔的穷街陋巷,在近八年的时间里,去了他们家1593次。
在这些边缘的街区、铺着鹅卵石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在汽车、垃圾桶和人行道之间,在灰暗的街灯下,在那些用一只半瘪的球踢足球的孩子们身上,我能够看见生活的本质。父亲越做越大的生意,工厂,致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富裕必须过的一种“欧化”生活,仿佛让我远离了生活里那些简单而根本的东西,而现在,在这些后街上,我在寻找自己人生中那消失的中心。[1]224
在此,我们看到凯末尔勇敢地抛开了世俗的遮蔽,放弃了物欲的羁绊,虔诚地向心中的安拉——芙颂靠近。与此同时,他的灵魂也在进行着自我净化。他开始为昔日沉迷于物质享受、感官娱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内疚、忧伤,开始慢慢拨云见日看见“生活的本质”,找到“人生的中心”。他终于悟出“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1]269,开始因替真主(芙颂)所做的事不够而感到忧伤,因无法完全接近安拉(芙颂)而忧伤。比如,他为自己当年没有在芙颂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守在门口而忧伤,为自己没有取消和茜贝儿的订婚仪式导致芙颂离去而忧伤,为没有派母亲去芙颂家提亲而忧伤,甚至为没有带芙颂去海滨浴场这样的公众场合而忧伤。他觉得自己当年应该为芙颂做更多的事,悔恨没有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现在芙颂嫁给别人了,他只能厚着脸皮坐在对面看她,偷偷拿走一两件属于她的小物品聊以自慰,他为无法完全接近她而深深忧伤。
在小说结尾,凯末尔终于完成夙愿,和梦寐以求的芙颂订了婚。正当他兴高采烈准备迎接美好生活时,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芙颂的生命,刚刚得到复又失去。这场忧伤的爱情注定要以求而不得来告终。“由于爱到极深处,无法释怀,无法解脱。如何让爱情延续又不至于让自己崩溃:唯一的办法或许是留住物、追问物、缅怀物、贮藏物、展示物。”[4]37车祸之后,凯末尔为了纪念芙颂和他们的爱情,走访了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并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他把几年来悉数收集的芙颂的小物件一一放进博物馆里。“物件凝聚了主人的气息,又能以可见、可触的形式保存下来,活着的人通过它去缅怀过去。”[4]36他住在里面,觉得“依恋着这些渗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1]538
在小说最后一页,风烛残年的凯末尔站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昏暗的路灯下,满怀爱恋地亲吻了芙颂的照片,并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1]559尽管因为这段爱情蹉跎了半生岁月,他却并不后悔,因为至始至终他都跟爱人在一起,没有违背自己的心。不仅如此,他还悟出了爱情、幸福、人生的真谛,比之世间浑浑噩噩匆忙一生的芸芸众生,他的确是幸福的。帕慕克用饱含深情的忧伤笔调给这个充满忧伤的爱情故事画上了一个忧伤的句号。
第三重忧伤:忧伤之人——自我身份的模糊之伤
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大背景下,每个杰出的作家都会面临文化选择的问题。从世界意识出发,他们自觉地学习欧美文化;从民族意识出发,作家又必须以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为己任,在创作中继承民族文化,追求文学的民族性。[3]21这种矛盾曾经让帕慕克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为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感到忧伤、无所适从。小说中的凯末尔可以看做是作家的另一个“自我”,在法国上过学、富有、“西化”的茜贝儿可以看做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象征,而只买得起国货、贫穷、迷人的芙颂则是弱势的土耳其文化的隐喻。凯末尔忧伤地在二者之间徘徊、反复、难以抉择的样子恰似帕慕克自己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是异常艰难和痛苦的,要经历千百次自我的割裂、分离、重组,因而两者身上都萦绕着一种深深的、挥之不去的忧伤。最后,在经历了失去的万般痛苦后,凯末尔毅然抛弃了原来的生活,选择了美丽迷人的穷姑娘芙颂,走进了她位于穷街陋巷中的家,融入到她朴素的生活中。这就像帕慕克在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后选择了不放弃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精髓,突破了东、西方的界限,在创作中融汇西方叙事艺术和东方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杂糅风格。他的杂糅特点揭示了土耳其民族身份问题,他通过写作为现实中逐渐西化、丧失文化根基的土耳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民族身份。这种民族身份具有“雅努斯式”(janus-faced)的两面性。帕慕克向我们揭示:文明的本质不是冲突,而是融合;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模仿和相互吸收。一方面,我们借鉴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必须依托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徜徉于民族文化的光辉灿烂之中而停滞不前。只有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才能为文明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陈竹冰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张虎.帕慕克与苏菲主义[J].外语教学(6):84-86,2010。
[3]陈光.是无奈的祭奠,抑或是殷切的期望?[J].文学界(5):20-21,2010。
[4]支运波.情人、物件、文化之恋:评《纯真博物馆》的幽灵性[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1年春季号):34-39,2011。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