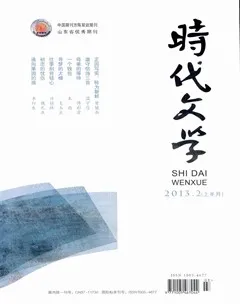白人文化殖民下的黑人悲剧
摘 要:托尼·莫里森是历史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她的小说《最蓝的眼睛》通过讲述一个黑人小女孩的悲剧,深入探讨了内部殖民境况下黑人文化身份问题,展现了黑人群体如何在白人社会的文化霸权压迫下逐渐迷失自我并走向毁灭的过程。通过这部小说,莫里森想努力唤醒迷失在白人主流文化中的黑人,促使他们保持并传承自己的黑色文化底蕴,珍视自己的种族特性,发挥黑人社区的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建构民族身份。
关键词:殖民文化;黑人身份;价值观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作为历史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浪潮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星。她的作品深深扎根于美国黑人的历史、传说和现实之中,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最蓝的眼睛》是托尼·莫里森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因肤色黝黑,一直生活在周围人的冷落与鄙视中。她整天企盼能有一双被白人文化规范视为美的蓝眼睛,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众人的喜爱。其母亲波莉对白人的生活向往倾慕,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她的白人雇主家中,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管不顾。父亲乔利酗酒成性,酩酊大醉后将佩科拉玷污,使其生下一死婴。母亲的殴打,周围人的嘲笑令孤独无助的佩科拉精神崩溃,在神志失常的状态中幻感到自己拥有了一双“最蓝的眼睛”。通过这部小说,莫里森探讨了内部殖民境况下黑人文化身份问题,揭示了美国白人文化价值观对黑人的影响与残害,展现了黑人群体如何在白人社会的文化霸权压迫下逐渐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的末路。
二、白人文化殖民下黑人身份的迷失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宗教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等。尽管文化与种族一样,从本质上说并无贵贱优劣之分,但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相遇时却可因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弱势文化群体会在强势文化所引领的价值观、大众传媒中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若放弃自己的本位文化,迷失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中,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主体身份的丧失。
美国黑人通过长期的斗争赢得了一定的权利,但仍然无法摆脱多年来积淀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顽固蛰伏于白人以及黑人内部肤色较浅的人的头脑中。在小说中当佩科拉满怀喜悦地到白人店主的杂货店里买包装上印有一个蓝眼睛小女孩的玛莉·简糖果时,她看到店主对她露出漠视和厌恶的神色。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藏着这种神情,并认定这是由于自己的黑皮肤,自己的“丑陋”引起的。她想要变得美丽,盼望白皮肤、蓝眼睛的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佩科拉对包装纸上印有蓝眼睛、白皮肤女孩的玛丽·简糖果的喜爱,反映了美国社会大众传媒对黑人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内部殖民状态下的美国不再像奴隶制度时代那样对黑人进行公开的剥削和奴役,代替它的却是白人强势文化对一切的权威性操纵。这种操纵一切的权威比比皆是:小学的课本中介绍的是安逸舒适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小说的叙述者克劳蒂娅的父母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是金发碧眼的洋娃娃;佩科拉喜欢吃的糖果包装纸上是一个蓝眼睛的白人女孩;佩科拉母亲波琳所看的电影中褒扬的是白人的俊男靓女,而屏幕上的黑人演的多是外貌可笑、言行拖沓的傻子、仆人之类的角色。这些人物给白人的浪漫故事平添了不少趣味,实际上却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白人凭借他们在媒体上的强势,大肆宣扬白人文化,并通过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体以及音乐、服装、杂志等宣传工具,推行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向黑人及其它少数民族显示其优越性。
三、白人殖民文化下黑人人格的畸变
美国黑人族群是个在很短时期内形成的有着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犹如美国内部的一个殖民化小国,由于早先的奴隶身份,他们在获得自由之后仍然被白人歧视,他们的文化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状态。美国黑人的这些特质,令他们进退维谷:黑皮肤成为他们无法抹去的种族印记。《最蓝的眼睛》体现了20世纪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杜波依丝所阐述的“双重意识” 理论。美国黑人的非洲性和美国性的冲突使他们不得平静,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两种公民资格、两种灵魂、两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中一个。然而无论选择哪一个,另一部分的自我都不得安息,挣扎在心狱的藩篱中。他们中有的人在内外交困中内心失衡、精神分裂;有的人则在追求被认同的过程中心灵异化、行为变态;有的人为获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挤入上等社会,抹去自己黑色身份的耻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陷入一种自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而不能自拔。
通过杰拉尔丁和切丘,莫里森揭露和批判了“混血儿审美意识”。 杰拉尔丁出身于黑人中产级家庭,因皮肤呈浅棕色而自认优越于深肤色黑人,为被白人主流文化接纳,她不但使用各种药物和化妆品以消除其作为黑人的外部特征,还极力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摒弃自己的种族亲情和黑色文化底蕴,直接导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的丧失。同杰拉尔丁一样,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误以为自己的混血血统可以让其高人一等的牧师--切丘。切丘是被西方文明扭曲得最为严重的一个。从那些或许有些不列颠贵族血统的混血儿祖先那里,他学会了要把自己从各个方面与非洲祖先的一切隔绝。为了弃绝自己的黑人性,他与黑人社区格格不入,结果将自己置于孤独状态中,离群索居,行为变态。切丘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黑人在放弃弱势文化本位、转而追逐强势文化过程中发生的价值错位和迷失。在给上帝的信中,他承认像他这样的黑人资产阶级接纳了白人最恶劣的一些特征。在这种异化了的人格中挣扎着的黑人,不顾亲情、友情、种族情和爱情,甚至抛弃了最起码的同情心和良知,扭曲人性,压抑生命。切丘的遭际体现了莫里森对“白化”黑人自我的一种批判。
四、黑人文化的坚守者与歌唱者
莫里森曾说过,她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其作品的立足点是如何唤醒在西方社会的精神奴役下产生精神危机的黑人,促使他们寻找自我,寻找黑色文化底蕴并最终返璞归真。为此,莫里森塑造了克劳蒂娅·麦克蒂尔一家。这一家人尽管家境贫寒,终日为生存而奔波,却尽力避免因种族主义和经济贫困所导致的“精神贫困”。他们自尊,自爱,自强,富有责任感。在乔利放火烧了自家的房子后,是他们收留了佩科拉。他们精神上的强大在于他们保持住了两项黑人的文化传统:音乐和社区责任感。黑人自从被贩为奴隶,美洲大陆上便飘遍他们的歌声,白人压迫得了黑人的身体却压抑不了他们的歌声。通过歌唱,他们毫无保留的传情达意,并把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由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因此,音乐使他们免于死亡,是幸福和自豪的源泉。女儿克劳蒂娅回忆母亲哼唱的曲调时说:“如果妈妈有情绪唱歌,事情就不会太糟。她会唱到艰难的时刻,糟糕的时刻”。黑人布鲁斯音乐中包含着黑人妇女的女性诉求,更重要的是,布鲁斯把黑人经历的艰难困苦转化成生存的抒情源泉,以至于像克劳蒂娅这样的孩子,从母亲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中听出“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
五、结语
《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真实再现了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的两难困境, 并深入探讨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的迷失。一方面,由于本国“内部殖民”的影响,黑人作为弱势文化群体在主流文化的激流中无所适从,盲目认同白人文化;另一方面,黑人由于不能完全摆脱奴隶制的阴影而身心受到戕害,人格畸变、心灵异化、行为变态,是黑人传统文化的弃绝者。同时,黑人社区的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未能得到有效传承,产生文化身份的断层感。但是,黑人中也不乏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种族亲情的维护者。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才为黑人的精神自由和民族身份的良性构建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榜样。通过对克劳蒂娅一家的赞许, 莫里森号召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儿童唱“自己的歌”,强调黑人坚持自我和保持社区团结的重要性。表达了对黑人重塑民族形象和建构民族身份的希望与信念。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41。
[2] 关丽丽,探析《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根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3)。
[3] 徐露露,从《最蓝的眼睛》中透视黑人自身弊病[J],安徽文学 ,2010(4)。
[4] 李美芹,黑皮肤,白面具——《最蓝的眼睛》中内部殖民境况下黑人文化身份探[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