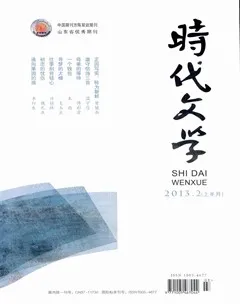历史的印记
摘 要:萧红作品中不乏对生命的诠释,描写和刻画了自然生物的生命律动和必然死亡,自然季节中春之欣喜和冬之沉寂,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字里行间透露出她所刻画的那个时代人物对生命意识的困惑,同时呼唤对生命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生命意识;困惑;觉醒
萧红出身在于中国的东北,她的生命历程与创作时期都处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期,她的作品有着历史的烙印,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的历史困惑。萧红饱经人生苦楚,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诠释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一、 对自然生命的诠释
萧红作品充满了对自然生命的描写和诠释:“她笔下的花草树木都有声响,虫蝶蜂鸟都会说话,风云雷电都有颜色”,①她珍爱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但也感触自然生命的灰色。 “树林里的秋叶呼叫着回旋着,落叶依着墙根哭泣,秃叶的树在惨厉的风中脱去灵魂一般呼啸着……有的虫子叫在人家的坟头上。”萧红的作品中不乏这样颓败、荒凉的图景,描写自然生命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萧红对死亡的动态描写使人不禁寒颤,在对自然生命凋零的悲悯之余,有着对生命陨落无可奈何的感慨。
萧红对悲凉情绪的释放大量出现在对冬天的描写中。在《呼兰河传》的开篇有这样的描写:“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这里漫天封冻使北方成为一个凝固的世界,生命似乎在这里冻结,没有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冬季里,生灵的生存状态让人担忧,让人窒息。从被冻开裂口的大地的狰狞看出萧红对生命冻结的绝望和恐怖。在萧红的作品中,令人绝望和恐怖的严冬背景总是预示着可怕的事情的到来。在《飞雪》中,萧红描写了冬天里的一片死迹。“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萧红的创作时期正好处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期,她生活在东北这个始终受到日本侵略铁蹄下的特殊区域,其作品带有这个特殊时代的印记,现实的残酷表现在她对冬天的描写中。
在萧红的作品中绝望与悲凉的情绪终结于春天的来临,她对自然生命的希望亦寄托于春天。“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垠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自然界的苏醒,是萧红对阳光下自由的生命极具感染的描写,她所展现的生命如此绚烂自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残冬过后生命更加美好,是作者的一种希望和期待。我们还可以从《小城三月》里对春的描写中来揣摩萧红的期许。“春天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头走到那头”,“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这里萧红在高歌生命,在灵魂深处期待自由生命的降临。
生命是可贵的,在萧红的笔下出现了自然生命两极化的特征。冬天里自然界的枯竭和冻结,生命是无奈的、绝望的,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萧红所处的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春天万物复苏,自然生命的自由与奔放,是作者对自由生命的期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萧红显然对未来充满期待,现实终究要成为历史,一切绝望和苦痛都会过去。
二、对生与死的态度
萧红作品展示了东北的生存景观,透视出民族深沉的心理结构,描绘出凝重的社会氛围,对处于此种环境下人的生命意识的关注尤为独特和深刻。
在萧红的作品中,成年人对孩子生命的态度多不正常。她在《生死场》中这样阐释到:“乡村的母亲们对孩子们永远和对敌人一般”。在她的笔下,母亲摧残着自己的孩子们。平儿偷将父亲的靴子穿出玩,王婆发现后让平儿赤着脚走在雪上回家。少女金枝不小心踩到一颗菜,就遭到母亲暴怒地恶骂。在萧红的眼里,母亲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性被苦难的生活所压抑已然麻木、残酷。女性如此,男性尤甚。婚后,在生活困顿的压抑下,金枝经常遭到丈夫暴骂,孩子也不能幸免,有一次丈夫在气急之中竟然将自己的孩子摔死了。
人们似乎对自己的生命并不认真。在《呼兰河传》中,人们知道是得了瘟疫的死猪肉,却抢购来吃,他们宁愿认为“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里淹死的”,“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吧便宜猪肉来”。人们得病时不去先进的新式西医那里去治疗,而是将就着请本地的土医看看。更有一家,破房子漏着风,刮起来大棺、马梁、门杠、窗框等都喳喳的响,但“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要倒的这回事,毫不加戒心”。忍饥挨饿的人们对生命的草率、麻木与心存侥幸,已经使他们面对生的忧患与死的恐惧感到无助。
在萧红的作品中不乏有对待生命终结的认识,人们表现出对死亡的麻木和对世俗与鬼神的敬重。《生死场》中的农人们“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和困顿的生活环境下,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已然丧失,他们已虽生犹死,他们的生与死已经如同其它动物一样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呼兰河传》中也有对死亡麻木而漠视的描述。染缸房淹死过一个人,两三年过后,已久远的不只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小团圆媳妇死后,有二伯和老厨子埋了她,酒足饭饱后回来,只记得酒菜不错,只字不提埋葬之事,在他看来,“人死还不如一只鸡”。王寡妇的儿子死了,能够掉几滴眼泪的只有王寡妇一个人,哭后还得去卖豆芽菜。在对死亡的麻木和漠视中,《桥》中小良子跌进水沟淹死、《哑老人》中年轻的姑娘小岚被工厂的女工头毒打致死、《叶子》中少年莺哥得肺病无钱救治而死、《小城三月》中翠姨为无法实现的爱情忧郁而死等等,皆如过眼云烟,无法触动人们的神经。
萧红笔下对世俗传统与鬼神的敬重让人生畏,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崇拜鬼神而轻贱生命。《呼兰河传》中,在东二道街上有一个阻碍交通的大泥坑,经常弄得人仰马翻,淹死猪、狗、鸡、鸭、猫等,呼兰河人总是会想方设法通过这里,却永想不到去填平它。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不慎掉进了大泥坑淹死了,人们只说这是龙王爷发威了,是农业校长遭到了因果报应,其原因是这位校长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雨不是龙王下的。在东二道街上,最为恢宏壮观的当属这里的扎彩铺了,场面庞大,有喷钱兽、大金山、大银山、丫鬟、使女、厨子、猪倌、小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等等各种物件,应有尽有。萧红对扎彩铺的着意描写,无非是告诉这里对鬼神敬重的根深蒂固,这里的人们都知道“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怕没有这些东西,故要将这些各种物件带去,“穷人们看来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呼兰河人还每年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来表示对鬼神的敬重。跳大神是为了表示对鬼的敬重,唱大戏是为了取悦龙王,河灯是给鬼放的,这样就可以让鬼顶着等去托生。在娘娘庙大会上,人们也要烧香磕头以祭鬼。在世俗、鬼神面前,人的生命似乎显得尤其渺小与脆弱,在萧红的作品中不乏世俗、鬼神戕人生命的描述。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就因为“太大方了”,没有像其他妇道人家那样合乎传统,“不像个小团圆媳妇”,而被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还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体,被当众剥光了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之后用凉水浇了三遍,经过一番折腾,小团圆媳妇就这样结束了十二岁的生命。萧红极尽笔力刻画了神鬼、世俗的残忍,向人们揭示正是我国长期封建主义下所形成的人的愚昧和麻木造成了这一件件人间悲剧。
三、 生命意识的觉醒
萧红的作品中还塑造出了一批打破世俗、争取自由幸福的人物,他们是在人性畸形的社会中与现实社会抗衡的生命世界,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生命意识,即使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要为自己的信念而抗争。
《呼兰河传》中有一位老王家的王大姐,人们对这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常常赞不绝口,说她是一个手脚勤快、人见人爱的姑娘,夸她是个能够兴家立业的好手,她似乎成为人们眼中的模范人物。但是,王大姐并不乐为人们世俗眼光中的宠儿,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偷偷地爱上了穷磨倌冯歪嘴子,并与他暗中生了儿子。王大姐对幸福的追求却遭到人们肆意地诋毁和恶毒地中伤,认为她这种不符合他们传统思维习惯的行为是伤风败俗,将她视为异端。王大姐的抗争最后终被世俗所吞没,她为自己的幸福追求失去了年轻鲜活的生命。萧红从现实中走来,她深知世俗力量的顽固和强大,王大姐的命运结局是对世俗社会的揭露。《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受到过时代风尚的感染,从一个“咸与维新”的家庭中感受到“开通”与“随便”的好处,意识到读书识字对于人生的意义,在受到大学生接待后,体验到了被男性尊重的快乐,她追求幸福,反抗包办婚姻,最终她的生命被世俗所吞噬。她临终对自己所爱的人说:“我也很快乐……,我求的我都得到了。”萧红借这些抗争者之口,表达出对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无悔,哪怕是失去最珍贵的生命。
在萧红的作品中,人们能从同样与世俗抗衡的冯歪嘴子等人的身上看到希望。冯歪嘴子追求婚姻自由与王大姐结合生子,住在四处透风的磨房中,只能用面口袋为刚出世的小孩避寒,他被赶出磨房,周围人讥笑甚至巴望他一家遭殃,在王大姐死后,期待着看冯歪嘴子的热闹。“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养子似的,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模仿力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小说中透出的是生命的韧性。同样,在《后花园》中冯二成子在赵姑娘的笑声中复苏了人性;《商市街》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和郎华虽食不果腹却还常常施舍乞丐,帮助老人。这些生命意识的觉醒者虽步履蹒跚,却如此醒目和执著。
注释:
①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政治格局、多元文化、国家关系等为视点》”(11XJJC770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新疆与中央政府关系”(11BZS078),新疆大学西域文明发展研究基地项目“民国中央政府新疆政策决策机制研究”(XJEDU010412B08)、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民国前期新疆稳定策略研究”(BS090216)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