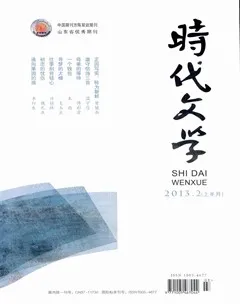正因写实,转为新鲜
一次在山东武城县,一次在北京,我参加了两次张曰凯的长篇小说《悠悠玄庄》研讨会,每次都作了发言。这期间还曾接受过《德州晚报》的一次采访。现据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德州晚报》的采访记,综合起来,重加理路,增删,润饰,原拟写成漫谈数则,不意竟成长文。
一
前些年我旅居美国,很少再接触当前小说新作。回国之后,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老朋友张曰凯的《悠悠玄庄》。刚开卷的时候,我还带着一种超然淡远的心态:“且看老张写得怎样吧”;但读了几章,我就肃然起敬,刮目相看了。宝成、宝雁的农村少年儿女情愫,赵太世一家勤劳、温饱的耕织生活,乡土中国基于血缘、系于宗族的稳定、温厚、又不无苦涩的亲情,赵家与玄庄悠悠流动的生活恒流和旧中国乡村萧索败落,苦于兵、匪、官、绅的灾变祸乱……小说写的生活是那样真切自然,人物是那样鲜活可扪,质朴可爱,故事是那样波澜不惊而又环环相扣,让人不忍释卷。2011年9月23日上午,我赴山东武城县参加研讨会,刚上火车的时候,读到第三十三章,当了军官的赵安禄第一次回乡探亲,在进庄的路上却遇到因“失节”被休的媳妇;到这里小说大概还有三分之一没读完,我就在火车上接着读,也顾不上跟同行者聊天了。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又在房间里读到十二点,第二天凌晨四点多又起来读,终于把它读完了。连同冯立三的前言,书后的跋《雾灵山夜话》都畅读了一遍。并不是因为要参加这个研讨会才那么上心地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得到了久违了的读小说的乐趣,引起了欲罢不能的兴味。就说小说最后那几章吧,真是奇峰迭起,波澜横生,结尾赵太世父子在冲突中同日而死,给人极大的震撼,也开启了意味深长的反思。长篇小说常见的毛病往往是开卷气势不凡,笔力健举,越写到后头就越是捉襟见肘,气短力弱,塌下去了。曰凯第一次试写长篇,三十多万言,始终笔饱墨酣,文气连贯,最后还能推波助澜,戛然而止,留有余响,这真不简单。古人讲写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要求开头漂亮,中间饱满,结尾有力,移用来评说长篇小说,最为允当。《悠悠玄庄》可作为此说的一个艺术的印证。
为什么《悠悠玄庄》这么好读、耐读?为什么这部小说不容浏览了之,只许细读慢品,有逼人俯气静心来研读的艺术魅力?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冯立三同志的序言里说的,它是回归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上来了。张曰凯在文艺学习上,始终师法《红楼梦》、《金瓶梅》,潜心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度。他多年的编辑生涯,使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小说创作流派和技法,长期揣摩、比较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对他而言最适宜也最熟悉的古典小说的写法。经过多年潜修默炼,精心准备,他有了在自己的创作中追踪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艺术美的功力,所以他成功了。我很为我的老学长、老朋友高兴。蛰伏多年,不飞不鸣;借写玄庄,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依古定法,望今制奇”,刘勰所言,也可以说是《悠悠玄庄》的艺术之旨吧。
从新时期文学掀开序幕以来,我一直是当代小说的职业性读者、评论者。我的工作需要我不间断地阅读当代小说家各种各样的作品。读的时间长了,即使是读已经写出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的名作家的作品,也会产生厌倦的感觉。厌倦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大多数作家已驾轻就熟了的当下文体和流行语言的麻木无感,也即阅读的新鲜感和受激感的丧失与钝化。这种当下文体和流行语言,或表现为洋腔洋调,或表现为社会小新闻语体与网络流行语的混搭;不再以创造典型人物为指归,也不再以白描手法的干净利落、简洁精炼为美感,为力度。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和语言的形影,在很多当代小说家的笔下,已经很难寻觅了。当我在惯熟了的当下文体和流行语言中徜徉得太久了时,为驱除困倦,一般情况下我就会随便拿本中国古典小说来读读,使脑筋得到清洗和苏醒。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常常是拦腰切入,读它几回;而《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老残游记》、《浮生六记》等等,则不时重温,如与老友晤对。在美国家居时,我还曾把蔡东藩的全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读了一遍,在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完整而细密的中国历史概观的同时,也欣赏了这位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历史题材作家非凡的组织力与叙事手腕,并对他把丰赡、典雅与明快、通俗互相交织的小说语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小说文体和语言审美上回归古典的趋向,起初我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的,后来才渐渐地引起我自己的醒悟。这种情况,与许多写新诗、读新诗的人,后来却转向旧体诗词,是不是有些相似呢?这次我读了张曰凯的《悠悠玄庄》,在探寻其文体与语言魅力之源时,又一次得到振醒:这种久违了的熟悉的陌生写法,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真髓之显现呀,也即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白描技术的遗响呀!
作为一个多少已有点审美疲劳的小说阅读者,读了《悠悠玄庄》,我是非常高兴的: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能带来阅读乐趣的书!我要把我的喜悦告诉曰凯,也告诉大家,这部小说真的是值得读,经得起读,应该慢读细读的书。而且,它是不怕人们这样读的。有的小说是作者写出来后自己觉得很好,因为艺术家没有不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美的嘛。但是不是经得起大家细读,这个就很难说了。《悠悠玄庄》之所以不怕人们慢读细读,因为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新鲜感,是来自于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来自于鲁迅所提取并运用于创作实践中的成功的古典小说技巧——白描手法。小说描写了风雨飘摇、神州震荡的大时代里鲁西北农民的生活和遭遇。在小说里,整个故事的进程像日常生活一样普通、习见、亲切,但透过单纯明快的情节和典型化的细节,人物的性格刻画得细緻生动,写一个活一个,有的笔触还能探触到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有高度文学性的。作者通过把绚烂融入淡远的,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创造画面,创造形象,创造意境,有力,有美,读了使人为之心折。小说所以有别于一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味之作,能够脱颖而出,让人一新耳目,其源盖出于此。这是我谈的第一点,也是小说给我的第一印象。
二
第二点我想谈谈《悠悠玄庄》的主题。看题材,论主题,观人物,赏语言,这可能是那种现在看来有点老的批评小说的方法,由于积习,我还是比较习惯于用这样的方法。鲁迅说,对作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这里说的便是对作品主题的分析和概括,提炼和阐发。这是有效的文艺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透过小说展开的人生的色相、人生的况味探寻小说的主题时,我注意到冯立三同志前些年在张曰凯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祭歌》的序中,谈到那些小说一以贯之的揭露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迷信、僵化、违情的主题时,他用了一句话:“严峻而有分寸”。他认为曰凯的中短篇小说着重揭露那些带封建性、宗法性的传统文化当中冷酷的、悲凉的、严峻的一面,同时他又认为写得有分寸,不作极端之论。这是很有见地的。我读《悠悠玄庄》,感到它给人的总体审美感受、审美基调,却是温馨而不乏冷峻的。小说所画出的乡土农家生活的恒流,不乏苦涩和阴凄,但总体上却是温馨的、和谐的、令人感到欣悦的。作家的调色板上,当然也有冷的颜色,但小说的基本色调,却是暖的、热的、舒熨人心的。过去,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描写旧社会中国农村底层生活的黑暗、落后、残酷的作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这样的小说出现了很多很多。但是那种能够让我们看到乡土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中的美,看到这种乡村生活本身自然纯朴的美,维系并浸润在这种辛劳、和乐生活中的伦理的美,以及这种美的生活带来的温情、温馨的作品,却很少读到。孙犁就感慨地说过:“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他还说:“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悠悠玄庄》最感人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传统的耕织之家劳动的美,生活的美,伦理的美。小说通过赵太世一家这个宗法性颇为浓重的耕织之家的生存状态、劳动过程、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在婚丧嫁娶,各种节庆游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行为、文化心理、风土人情等等,写出了乡土中国人在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与拼搏中显现出的正直、明达、刚毅、温厚等优良的品性。这部小说看下来,里头有许多细节让人看了不能不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能不陶醉于劳动的诗意和美的生活画面与情景。作家写传统文化中宗法制农民生活中的伦理,不是演绎式的,而是显现式的,完全溶化到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去。鲁迅在讲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艺术时,曾说了八个字:“正因写实,转为新鲜。”《悠悠玄庄》这部小说,新就新在这里,就是在传统伦理的真实描写这一点上转为新鲜了。读《悠悠玄庄》时,我甚至联想到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称赞。他有一次正在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击节赞叹之余,情不自禁地对来访的高尔基说,“在这位伯爵以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列宁说的是宗法制下既有改变现状的要求又有妥协性、幻想性的农民形象。在曰凯的这部小说里,出现了非常精采的农民形象:赵太世、赵安福。就形象的社会意义而言最重要的是赵太世。但就形象的个性化程度而论,写得最精彩的要数赵安福。赵安福是赵太世的长子,是赵家的顶梁柱。他虽不是一家之主,但他支撑着赵家的现在,彰显着赵家的未来。这个形象刚出现的时候,像是赵太世的影子,纠结在他身上的情节、故事、生活矛盾比较少,动作性不强,说话也少,给人感觉晦而不显。但也有一些情节,凸显了他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如带弟弟赵安禄去卖香椿芽、吃老豆腐,写出了兄弟之间的伦理和他的俭省。又如因媳妇没按他的要求在午饭时炸油香而冲媳妇发火,朝媳妇把笤帚扔了过去,这不仅表现了他的夫权观念,也潜伏着他对赵太世在家里安排一切,自己在吃食上也不能自主的不满。尔后看妻子隐忍含泪去麦地劳动,他又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表示自己对妻子委屈的理解和疼惜,这个情节是写夫妻伦理的精彩之笔。越到后来,这个形象写得越好、越鲜活、越丰满,也越有深的意味。日本人占领了德州城,赵安福跟赵占魁、赵连根一起上城看望儿子赵宝成、赵明理,路过南门,因为没有向日本人鞠躬敬礼,日本兵就打了他们几个耳光。这一下子,一向老实巴交、蔫不拉叽的赵安福急了,对日本兵怒目相视,质问日本兵:“你咋的打人呢?你咋的不讲理呢?”赵占魁见势不妙,拉着赵安福勉强鞠了躬才躲过一劫。事后,赵安福觉得憋屈,边走边唸叨:“俺一辈子还没有挨过打哩,这小日本咋的欺负人呢?咋的不讲理呢?”这个细节写得意味深长。赵安福等中国农民因不鞠躬而挨日本人耳光的事,在日本侵略者欺辱、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中,实在是小而无奇者,但它却深深伤害了赵安福的人的尊严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千百年来形成的那种道义和伦理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中去了。这种道义和伦理,为民族命脉所系,为生民立身所本,是立国立人之宗旨,为人处世的准绳。一旦遇到不讲道理,毫无人性的外来横逆势力的压迫摧折,就会激起敏感而深沉的反感,引发猛烈而持久的反抗。小说中作为另一条重要故事线与玄庄故事的历史背景而存在的鲁西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曲折、悲壮的故事,虽然写得不那么生活化而更多地带有传奇色彩,但在小说的结构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而赵安福在初遇日本人时朴素而强烈的屈辱感,则深沉地透露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大批大批地起来,为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自由与尊严,自己的道义、伦理而发出的最后的怒吼。
小说写到结尾处,当赵安福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后,有一个细节给我极深的印象。赵安福这么一个节俭、拘谨的人,有一次突然结结巴巴地跟悉心伺候、照料自己的老婆说:“等我病好了,带你到县城去逛逛,下馆子,看戏。”安福家里的又高兴又有点害羞,喜笑着嗔道:“守着儿媳妇的面,别说些老不要脸的话。”在一旁听到这对话的、离婚不离家的儿媳高立英不好意思地抿嘴笑笑,同时也自觉这笑意里掺杂了多少苦涩的味道。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赵安福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感激所作的许诺,是多么平常、简素、真挚。他的一生,都生活在父亲赵太世的身影覆盖之下,生活在带宗法性的乡村耕织之家的恒定的秩序之中。在这种秩序之中,只要还没有分家自己挑门过日子,年轻夫妻是没有多少表现自己的情感,表现夫妻的恩爱,享受农村日常生活中的难得的乐趣(如下馆子、看戏)的空间的。以致赵安福说出的愿望,作出的许诺,在妻子听起来,都觉得突兀,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赵安福病倒之后,才有时间也有条件回想自己一生的生活,才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缺憾,说出来久藏在心底的愿望。这个形象在这里一下子亮起来了,活起来了,尽脱其晦暗、固执、僵硬的一面。请想一想,他原来是一碗老豆腐也舍不得买,出外卖布只舍得住土地庙,一点苜蓿让人偷割了之后就要把大粪泼到苜蓿上防盗的农民,是大水追来了还拼命抢收庄稼不肯撒手的苦受狠做的庄稼人,现在虽然表达出追求生趣的愿望,却离生命的终点不远了,这是怎样的悲剧啊!这是鲁迅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才是真实到让人感到心的震颤的悲剧。
《悠悠玄庄》就是这样,通过对赵太世、赵安福一家生活的质朴无华的、真实无讳的描写,写出了过去很少人写到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在的活力和秩序,写出了中国乡土这种耕织之家、这种宗法制农民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和谐、美和诗意的一面。小说实际上提出一种观察我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观察宗法制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角度。从“五四”以来,我们一直批判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其落后的一面、伪善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作了尽情的揭露和批判,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巴金的《家》,再到路翎的《财主和他的儿女们》,都是走的这样一个路子。但这种批评也容易走向一种极端,对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形态几千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的内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因素,对使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的制度建构、道义、伦理的正面内容,就容易忽略了。我曾比较认真地看了钱穆的《国史大纲》,特别是书前八万多字的前言,还看了张岱年先生年轻时写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我觉得这两个学者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封建社会的制度建构、运作程序、道义伦理,有许多精微独到的见解,为我们过去所忽略,应该重新引起大家的注意。比如钱穆,他认为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用一两句话就全给否了,好像只是“一片黑暗”,只是“停滞不前”就完了,他主张对我们老祖宗的历史,要取一种同情的、解释的、认知的态度。“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又如张岱年,他的书里,对三纲五常,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中的稳定性和积极的、促进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机制,做了一些正面的评说。这表现出对历史的一种认知的科学态度。这种思路和角度,我以为可以作为我们已习惯了的否定的、批判的态度的一种补充。任何一种理论的命运,都要视其满足社会的需求的程度和自身更新的活力来决定。世易时移,一种倾向为另一种倾向所替代,这是很自然的。曰凯的《悠悠玄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存在着、发展着的那种宗法制的农村以耕织为本的和谐的、温馨的农家生活,也即构成社会生活底色和基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图景。而维系这种生活图景的,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我们看到,这种溶化在农民生活的血脉、肌理中的中国传统美德、道义伦理,维系着一个家庭,维系着一个村落,维系着一个族群,维系着一个国家。当日本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人民就会本能地、自发地奋起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坚决地反抗这些不讲道理的野蛮人。《悠悠玄庄》的主题和艺术表达的新鲜之处,深刻之处,就在这里。
三
《悠悠玄庄》集中笔力写出了赵太世一家那种在艰辛的劳动中求得温饱,也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及其精神生活和心理特征,当然也写到这个家庭跟外部各方面的关系,借以把笔力辐射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去。比如小说写了石榴红这样一个不安于命运的安排,生活道路变迁和漂移的幅度很大的农村女性形象。一方面,作者赋予这个富有艺术天分和才华的农村女艺人以浪漫主义的色彩,让她的生命在玄庄的抗日自卫军如火如荼的斗争烈火中放出了炫目的光彩;另一方面,作者又按照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生活逻辑,给她安排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嫁给马德昌当二房的灰暗的命运。人物性格的不变的单纯和桀骜不驯与生活环境大起大落的跌宕变化,深化了这个“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农村女性形象,也大大扩展了小说波及的生活幅度。又比如,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极其鲜活的印象的哇儿哇儿。作者借助这个悲剧性人物生活道路的抛物线,把笔墨甩出去,就把柴三猴子这样恶霸型的地主形象和虽然挂匾立牌坊却终身凄苦的旧礼教的牺牲品桃个儿的形象也带出来了。这些次要人物的生活故事,性格刻画,都与赵太世一家的生活故事有着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联系。这就拓展了小说表现鲁西北农村社会生活的广度,丰富了小说的社会生活内容,为主要典型人物赵太世、赵安福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深广而又工细的典型环境的描写。我们透过赵太世一家的生存状态和家运的起伏变化,透过出入赵家、出入玄庄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更加完整地看到了鲁西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全貌,看到各种各样的农民家庭,各种各样的地主家庭,各种各样的乡土中国的儿女,也看到了这些家庭,这些人物之间的交织、溶合、排斥,终于汇成了一条穿越民族解放战争风云而走向自由、解放的人民生活的河流。在这条河流的冲刷激荡中,我们更加看清了赵太世一家、赵太世父子的典型性。
在我读过的农村、农业、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情势下的农民家庭、农民形象的典型。有《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一家;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一家;也有《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一家和严志和一家;还有《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家和鹿子霖一家。这些农村家庭和人物,各有其不同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同的真实性,不同的审美价值。如果把赵太世一家放在上述家庭、家族形象的文学画廊里,那就不难发现,它的地位是颇为独特的。赵太世一家,在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上,应该说是温饱无虞,而且家境正在上升的殷实农家。这样的家庭如果不遭逢乱世,再向上发展,就会渐渐走到类似白嘉轩、鹿子霖那样的地主之家的行列中去;如果遇到不测灾变,家境跌落,那就会下降到梁三老汉那样的贫苦状态。旧社会农村的两极分化和两极换位,是进行得很频繁的。《悠悠玄庄》截取了处于相对稳定并渐有上升趋势的赵太世一家的一段家史予以艺术的再现,应该说是把握住了中国农村在那个时代最具本质意义的社会生活的基准线的。在乱象中逼现本相,在变动中凝视恒常,这就是艺术的集中和概括,也即是文学典型的创造。
最后,我还想谈谈《悠悠玄庄》的文学语言。曰凯长期以来,潜心学习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别是《红楼梦》、《金瓶梅》的语言,他简直达到了已经烂熟于心,可以本能地应之于手的地步。所以有些情节,如宝成与宝雁的少年情愫、儿女恩怨之类,让人有过于肖《红》之叹。当然,他的语言的主要来源,是自己青少年时代亲历的生活,是故乡玄庄乡亲们活的口语。写作过程中,他又几度回乡访问故老,采风观俗,对武城、德州乃至整个山东的人民口语、土风旧俗,作了尽情的汲取,无痕的化用。在刻画人物、描写细节方面,他善于学习、运用鲁迅所提倡的“白描”手法进行艺术的创新。我们关于小说创作的道理,可以说上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条是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深广的主题也好,饱满的生活内容也好,诸如人物形象刻画,故事的演进与结构的弥合,丰富的情节安排,微妙的细节选炼等等,都要靠语言来实现。语言是小说艺术生命的物质的外壳,是思想、感情、印象、想象的外在显现,是作家气质、品性的流露。一切全靠作家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看能不能把生活的本色真香表现出来,能不能对生活作带露摘花,连泥拔草式的截取与再现。在语言的学习、锤炼、创造方面,《悠悠玄庄》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整理这篇笔谈时,我对一年前读过多遍的一些章节又一次重读,仍然被作者的生花妙笔所深深吸引。例如第二十五章“祈雨、棉花谣”,把安福家里的和宝成媳妇菊个儿婆媳俩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和她们的对话、歌唱写得多么有诗意,有温情,写得多么美。为了把纺纱、织布的多道工序写好写准,曰凯曾利用回家的机会让善于织布的妹妹给他细细讲解,并做示范,这才能把这一章写得如行云流水,生态并作,妩媚多姿。棉花谣唱到酣处,农家乐写到极致,却又引发安禄家里的怨望苦涩之声,劳动的诗意和伦理之情的缺憾一并流出,使这一支明朗欢快的棉花谣变得深沉,带有沉思的气质了。高妙的文学语言,创造出来深新的文学意境。还有第四十六章“夫妻识字”,也是展现曰凯文学语言功力的一个好例。这一章写的是已经当了区文化教员的宝成教已离婚的前妻菊个儿“识字”的情景。这是难堪而微妙的一幕。仳离而仍有余情,新生却罩着阴影,难以描摹,更难声状。这里,自然与做作的界线,间不容发;个中几微与分寸的把握,其难度,几乎同于捕风捉影。但曰凯却举重若轻地全都写出来了,而且写得那么精微、那么自然,那么传神。真可谓寸水层澜,回环往复,纤笔细摹,曲尽人物情态。就连宝成、菊个儿所用的《识字课本》,也带着历史的风尘,呈现了久违了的真实。曰凯为了写好这一章,还曾在潘家园旧书摊上,花100元买了一册山东解放区的识字课本。这件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轶闻,不正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明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