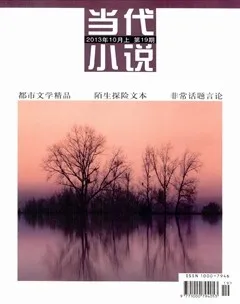截锯
孙玉美起诉赵兴光离婚,法院受理后,正式开庭前,先组织一次庭前调解。3月下旬了,天气很好,高屋法庭院内小花园里的连翘,熙熙攘攘地伸展着挤满鲜黄花瓣的枝条。调解室在法庭三层办公楼的一楼,窗子上是当年建设时流行的蓝绿色玻璃,阳春的光线透进来,不带多少温度。赵兴光感觉手脚发凉,头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心口发紧。劣质二手烟充满了调解室的边边角角,赵兴光把手中的烟屁股扔到了地上,又照着红火头使劲蹍了一脚,习惯性地伸手往右裤口袋里一摸,掏出一个哈德门烟盒,里面已经空了。他叭地把烟盒摔到了墙角,懊恼地扒了扒头发,像秋风吹过的荒草一样东倒西歪的头发,也像荒草被秋风吹得换了个姿势趴着。
孙玉美直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红色的羽绒服开着拉链,里面人瘦瘦的,挺着肩,红色的晴伦方围巾已从头上抹到了脖子上。她一直低着头,不抬眼看赵兴光,只看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揉捏左手的食指,两只手上的指甲都修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很干净。
怎么会到离婚的地步呢?赵兴光真的不大敢相信。两人虽然是经人介绍的,但他们是一眼就彼此相中的。在此之前,赵兴光已经相了二十多个对象了,孙玉美更厉害,相的对象过了三十个。说来蹊跷,就这么两个被人笑称为“挑花了眼”的青年男女,竟然一见钟情。赵兴光相信这是缘份。看对象后交往了半个月,两人就交往到床上了,处男处女初经人事,又过了两个月,孙玉美怀孕了,接下来,所谓的奉子成婚。虽然当时赵家父母借着这事,认为孙玉美非他家不嫁,在彩礼一事上一再压缩,闹了些不愉快,但终于还是顺利结婚了。农历五月结婚,当年年底,孙玉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人欢天喜地。那时候,谁能想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到法庭上闹离婚?
“到底怎么样,你就不离婚?”赵兴光问。
孙玉美抬了抬头,看着赵兴光:“你说,咱这日子能还舒舒坦坦地过下去吗?”
孙玉美知道赵兴光爱她,很爱;她也爱赵兴光,很爱。但那又如何?她实在撑不住了!
赵兴光在高屋镇淀粉厂当工人,合同长期工,一个月两千多点,只靠他一人的工资养着老婆孩子,很吃力。孙玉美没有奶水,儿子赵小龙从小靠吃奶粉,就生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不敢给他乱吃,定期由赵兴光到县城的大超市里买名牌奶粉,婴儿奶粉贵得离谱,一个月总有千数元的开销。赵小龙七八个月时,孙玉美也想出去找份活儿干,结婚前她在菜籽庄纸箱厂上班,稍累点,白黑倒班,但厂子里很忙,效益还不错,工人的工资也可以,一般每月都能过两千。但是,孩子谁给哄呢?在菜籽庄,奶奶哄孙子,天经地义。赵兴光的母亲却提出来,孩子可以主要由她哄,但她不能一年到头天天哄。
赵家父母很年轻,还都不足五十岁。赵兴光下面有个妹妹,正在上高中,学习不错,读完高中,肯定还要考大学,在农家,供应个大学生不是件轻松事。赵父是个盐场工人,虽然有份固定工资,但工资不高,比起村里外出干建筑或种大棚的男人们,远差了一截,就图再有个十年八年就退休了,到时可以消闲地拿到退休金。平时家里的大事小节,就靠赵母张罗,赵母很能干,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到人家大棚里干季节工,秋后外出给人家拾棉花,她得扎头竖腚地给女儿攒学费,儿子当年学习成绩一般,初中毕业就算了,但女儿学习好,考上了重点高中,说啥得也供她上大学。如果赵母全天候哄孙子,她就相当于“失业”,直接影响给女儿攒学费。
赵母提出的要求看起来很有理:她不再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了,那个太占时间,收入也不算高,但是,大棚里的季节工、秋后拾棉花,她还是要去的,这时候她干一个月,能顶赵父两个多月的收入,也差不多能赶上赵兴光或孙玉美的两个月工资,一年总共才那么两个月左右的黄金机会,不干太可惜了。要么,在这两个月时,由孙玉美先不上班,来哄孩子,要么,到时候由小龙的姥姥哄着。对于孙玉美,长期干着的活不干了,离开一个月两个月哄孩子,再回来时,这岗就可能让人给顶了,不合适。而且,虽然一大家子人还在一起吃饭,但各自的账务是独立的,老两口赚的钱是老两口的,小两口赚的是小两口的,婆婆赚的钱再多,也顶不了孙玉美的工资。让姥姥哄小龙,这更不现实,孙玉美在家里也是老大,她有妹妹有弟弟,一个上职专,一个上初中。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对于小儿子还有将来盖房子娶媳妇的大事,孙家父母的生活压力更大,没有空闲时间哄孩子。在菜籽庄,奶奶哄孙子是义务,姥姥哄外甥是人情,姥姥不哄,谁也说不出什么。
为哄孩子这事,小两口没少闹了别扭。赵兴光很孝顺,很为自己的父母着想,也是为妹妹着想,但是,这样就不替媳妇着想了。双方亲家也没少闹了矛盾,气得孙玉美的母亲说:“俺闺女麻麻利利地给你们姓赵的生了孙子,烧包不是?要是结婚后三年五年不要孩子,让你们猴急上几年再生孩子,到时倒贴钱你们也拿着当宝贝疙瘩抢着哄!”
到了吵架的份上了,谁也不会说好话,赵兴光的母亲反唇相讥:“要不是你闺女浪着急急忙忙上俺儿的床,也不能这么麻利生了孩子!”
“谁浪跟得上你浪?要是有一个相好的就在脸上点一个痞子,你满脸点了痦子都装不下!”
“有本事,也让你闺女满脸点痞子去!”
因为婆婆的作风问题,全家老少更是没少吵了架。在菜籽庄,人们管女人作风乱叫“创殃烂”,“殃烂”的意思本是指脏、乱。菜籽庄是个大庄,一个自然庄,五个行政村,赵家在菜籽二村,孙家是菜籽五村的。在孙玉美和赵兴光谈对象时,孙家父母托人打听过赵家户情。婚前打听对方及家庭的为人、风评,当地叫“捎听”,男女结婚前,双方一般都各自找人捎听捎听。孙家父母捎听到了赵母的作风问题,很不同意这桩婚事,都说“媳妇跟婆脚”,他们怕自家闺女嫁过去受人笑话。但是,孙玉美和赵兴光这两个都为看对象阅人无数的青年男女不仅看对了眼,而且,赵兴光迅速地以播种的方式占领了高地,孙家父母不好再使劲反对。“要是有一个相好的就在脸上点一个痞子,她满脸点了痞子都装不下”,这是孙家父母托人捎听到的一句说赵母创殃烂的原话。从一开始,孙家父母就很看不起赵母,这事儿,他们也和孙玉美说过,并嘱咐她,嫁过去之后一定要和丈夫好好过日子,千万不可受婆婆的影响。
新婚后,小两口还继续胶着恩爱,奉子成婚,他们的恋情像初春的嫩叶一样没长够身子,还得继续长着直到盛夏能洒下最浓郁的阴凉。孙玉美平时就住在婆家(在农村,很多新媳妇结婚后未生育前,仍习惯于住在娘家),只有在赵兴光值夜班的时候,,孙玉美才住到娘家,赵兴光下了夜班,电话打了,知道媳妇在岳母家,他会直接赶到岳母家,先睡一觉,然后接着媳妇回家。
那一天,下了夜班的赵兴光在岳母家补了觉,领着孙玉美回家时,已经傍晚了。到家,道门口的大铁门打不开,是从里面关着的。孙玉美没有多想,在大门上拍了几巴掌叫门,咣咣咣,赵兴光却抓住了她的手:“别拍疼了手!”赵兴光脸色很难看,他掏出手机打电话,好一会儿,电话通了,他只说了两个字“开门”。时隔不长,赵母出来开门。孙玉美扫了婆婆一眼,婆婆的脸色不正常!而且,怪热的天气,婆婆外面穿着件厚外套!孙玉美一下子全明白了。
赵母讪讪地打招呼:“回来了?我这就做饭去!”赵兴光没理母亲,拉着媳妇的手直接往小两口的房间走——家里共有五间北屋,两间住着老两口,另三间收拾成了小两口的新房。推开门。孙玉美看到床铺上不像她走时收拾得那么齐整,心里顿了顿,没说什么。她往床底下的暗橱里放置几件随身物品,一件军绿色的男式内裤就在床前地上!内裤很肥大,一看就是经过长久穿着和水洗的,绝对不是赵兴光的!
孙玉美原以为,虽然婆婆创殃烂的事儿在庄里并不是秘密,但媳妇嫁过来之后,婆婆会收敛或谨慎,肯定不会让媳妇‘看戏”,男女相好这事,一般都是避人的,长辈更怕这点儿事让小辈撞破。没想到,新媳妇嫁过来不足一月,就知道婆婆的创殃烂不仅仅是传言,而且,婆婆竟然趁她不在家,用她的床铺!这让孙玉美恶心得不行。
结婚后还没出“满月”,新媳妇就要着分家,孙玉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显然,赵兴光对于母亲的事是心知肚明的。但作为晚辈,这事怎么说?
以后,孙玉美每次回娘家,或较长时间外出,都要在新房门子上锁一把黄铜的三环锁。大铁门她没法从外面上锁,有时回家,仍不免会遇到大铁门从里面关着。她不再伸手拍门,和赵兴光一起回家时,就由赵兴光给母亲打电话,她自己时,就先在道上或到邻居家里站站玩玩。有时,也有多事的村民瞅一眼孙玉美手里提的包或方便袋,意味深长地说一句:“家里关着门啊!”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这类话,让孙玉美从脖根到耳根都泛红。
一天,她又提着包到邻居家坐会儿,这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二嫂,她看孙玉美手中的包或袋子时,都是不着痕迹,有时在路上遇到,很真诚地说一句,“兄弟家的,到俺家坐坐玩儿吧!”孙玉美有时就过去拉点家常,她觉得二嫂不是多事儿的人,觉得和二嫂挺投缘,聊天儿时也不仅限于客套话、无聊话。这天,孙玉美不自觉地说起了婆婆,话里很有埋怨和不齿。二嫂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么多年了,大叔都不管,大婶子也很不容易,大叔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至多两次,再就是忙秋忙麦、过年过节时回来,平时家里就靠大婶子一人撑着。有些事儿,我这侄媳妇本不该乱传言,不过你是自家人,有些事知道了反而好些。我嫁到赵家门里也有小二十年了,记得才来时,常听见大叔大婶子吵闹、打架,那时,大叔真是往死里打大婶子,然后大婶子就跑回娘家呆上好几天不回来。后来慢慢就没大有这些动静了。听说,大叔的亲兄弟,就是咱二叔劝过他:“自己有毛病你还没数?有这么个老婆,给照顾着儿女家下,就行了!只要她不提离婚,她不离家出走,她爱怎样怎样去吧,反正坏名声也早都捂不住了,你还较个啥劲儿?”听说大叔有点毛病,好像是前列腺炎这类的,关键时候下面就疼。唉,你想想吧,这两个人也都挺可怜的!”
孙玉美听了二嫂的一席话后,在心里仍然有些瞧不起婆婆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可怜她了。不过,婆婆的这种殃烂事撞见了,孙玉美很难装作没事儿人。孙玉美想到了眼不见,心不烦。她和赵兴光商量,和公婆分家单过吧。分家本不是难事,但是,赵家就这么一个儿子,只有这一口五间北屋的房子,分了家,也还是要在一个院子里。孙玉美的意思是,在院子里打一道隔墙,公婆走一个道门,小两口自己另开一个道门,不从一个大门口里出入了。这让赵兴光很为难。小两口和老两口住在一个院子里分家各自起炉灶过日子的,在农村不少见,但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却从中间垒上一道墙的不多,在整个菜籽庄,还没有这么一户人家。他怕让村里人笑话,既是显得他不孝,有了媳妇忘了娘,又印证了赵母创殃烂的传言,说明赵母的行为让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忍无可忍了。赵兴光也能体味妻子的感受,别说没有血脉关系的儿媳,就是他这亲儿子,其实早也戗不了母亲的创殃烂了。他淀粉厂的同事们,和他一样多数是高屋镇附近村庄的,别人下了班一般就赶回家,结婚前的赵兴光,却宁愿下班后住在厂宿舍里,除非回家拿东西、放东西、忙秋忙麦、过年过节或父亲歇班时,他很少回家。垒墙这事儿,赵兴光没直接说不行,他说,这事儿得问问父亲的意见。赵兴光心里说,如果父亲没意见,父亲都不嫌说来没面子,那大家皆大欢喜,如果父亲不同意,这道墙就不能垒。
赵父要保持他最后一丝作为男人、作为家长的尊严,他不同意在院子中间垒墙。
这道墙终究没有垒起来,孙玉美越觉得日子越过越堵。
这户人家的院子里,越来越热闹起来。
有人闯到家里,指着赵母的鼻子骂,撕着她的头发打。最厉害的一次,来人拉着七八人的队伍大闹,把出来说情的孙玉美也打了,一巴掌甩在她的鼻子上,两行鼻血立即淌过了嘴唇;来人砸了赵父赵母屋里眼皮底下的所有家什,还到孙玉美那边,砸破了电视屏,摔了影碟机,推倒了饮水机,掀翻了茶几子。
小两口吵架,吵完了,孙玉美又抱着赵兴光哭,赵小龙也在一旁吓得哇哇地哭。
婆媳吵架,然后见了面不搭腔。
亲家之间打架,孙母领着儿子、侄子来赵家闹,还把赵家老两口的门窗玻璃砸烂了。
赵家对外说起来,“儿媳妇光听她娘家瞎出主意,事事都听她娘的,自己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孙家对外说起来;“女婿其实也刚好,就是太听他父母的话。他是要和媳妇过一辈子,还是要和娘爷过一辈子?”
小两口的日子就在这种疙疙瘩瘩,打打闹闹中过了近三年半。孙玉美感觉自己要疯了。孙母说:“当初我说啥来?不让你和他家做这门亲事,你着了魔,不听,现在懊悔了吧?我算是看透了,除非是你婆婆死了,你这种日子过不到头。不如趁你年轻,早和他散伙吧!”
乍听母亲说这话,孙玉美的心里像被一把钢钎狠狠凿了个洞。婚后的日子,是过得很委屈、不舒服,但凡事都要图个面,她和赵兴光,赵兴光和她,都是有爱情的,虽然他们早过了热恋期,感情也被磕磕碰碰的日子磨得很平淡了。难道,他们的爱情之树在春天舒展了新绿的嫩芽,盛夏洒了一地的浓郁阴凉,经过肃杀的秋风扫落叶,马上要迎来全面凋零的严冬?自然界尚有四季轮回,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那么,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也会四季轮回吗,过了这个严冬,还会再有春天吗?
孙母说:“你提出来离婚吧,看看赵兴光他们家怎么答复。要是他们答应,院子中间打道墙,各过各的舒坦日子,也行,你们一家三口,毕竟小龙还有亲娘亲爷。要是他们不答应,我看就算了吧,你这苦日子过不到头。小龙是男的,离婚肯定跟赵家,他爷爷奶奶还年轻,他掉不到地上,而且,我们家也离着近,他们敢差待了孩子,我们就把孩子要过来!”
陪赵兴光来调解的,是赵父。在儿子收到法庭送来的离婚诉状和传票后,他曾就此事专门咨询过菜籽庄一个干律师的同村人程律师。程律师刚参加工作两三年,家里还保存着上大学时的一些法律教材。咨询过了,赵父还专门借了一本《民法学》,研究关于离婚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掌握的法律知识,他知道,虽然是儿媳起诉离婚,但现在,是否会离婚成功,主动权是在儿子手中。赵父想劝儿媳收回离婚的想法:“玉美,你这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如果兴光坚决不同意离婚,法庭不会判离的!”
“哟,你连这也打听清楚了?我起诉的,我当然知道!我也打听过了,一回起诉离婚不成,法院判了不离六个月后,我可以再起诉,到那时,他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法院也得判离!”
“看来你铁了心要离婚?你以为这个家离了你就不转了吗?”
跟瞅着父亲和妻子戗了起来,赵兴光转头劝父亲:“爷,你先出去透透气,俺俩先商量商量!”
儿子的一句话,让赵父一下子憋红了脸:“都说山鸹尾巴长,有了媳妇忘了娘!你天天向着媳妇,不听爷娘的话,她照样不是要和你离婚!”
陪孙玉美来调解的,是孙母。这时也忽地站起来,尖尖的嗓音提高了许多:
“他向着媳妇不听爷娘的话?如果不是你们老俩口在背后乱戳事,他俩何苦要离婚?”
这种场合里,没有心平,没有气和,什么刻薄的话,也都可以跑出嘴。但最终承担这个结果的,还是赵兴光。他不愿意因为双方父母的原因,而加速自己离婚的步伐。他使劲跺了一下右脚;“求你们了,都别说了!你们先都出去,俺俩的事儿,俺俩自己先商量商量!”
赵父:“哼!”
孙母:“哼!”
两个老人还是打开调解室的门,都走了出去。
小小的调解室里只剩下这对夫妻,一下子显得很空旷。赵兴光朝妻子呶呶嘴,示意她坐下,他怕两人站着,不自觉地就高声吵嚷起来。
“咱俩,还没到离婚的份儿上吧?”
“不离婚,咱这日子怎么过,你拿个主意啊!”
“老的,也挺不容易,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要是不住在一起,什么一般见识二般见识,光咱一家三口,绝对用不着天天鸡飞狗跳!”
“我不相信你会狠心和我离婚。是小龙他姥姥的意思吧?你别总是只听你娘的!”
“我们亲娘亲闺女,不听俺娘的,听谁的?你还不是什么事都听你爷的?”
“我还听你的啊!老婆最大!”
“那好,回家马上在院里垒道墙去!”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又何苦非得逼我做办不到的事?”
“我逼你?是你们全家人都在逼我!这日子怎么过?你就是宁肯离婚也不肯垒那道墙?”
“那,我再回去和咱爷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说动他。”
“只要那道墙垒了,好说,我跟你回去过日子;不垒这道墙,这婚非离不可!我嫁个男人,都不能给我争取利益,我图个啥?”
庭前调解,以一种僵持局面结束。
离婚案件如期开庭审理,法官调查两方的基本情况及关于离婚的一些事实和理由后,还得先行主持调解。说来说去,双方又说到了垒墙的问题上,孙玉美坚持垒墙,赵兴光却做不到。陪着到庭的赵父发话了:“玉美,你要是非得坚持不垒墙就离婚,那我支持你们离婚!两口子日子过得是不是顺心合意,和那一道墙没关系!长锯没有截锯快,日子没法过了,利索索地早散早好。你早再嫁,俺早再娶!”
赵父心里吃准了孙玉美并不是真心想离婚。哼,她就是想通过起诉离婚,来提条件,赵兴光这么好的男人,她到哪里另找去?再说了,就算离了婚,凭自家的条件,儿子说不定再找个大姑娘,还可以再生二胎,说不定他就可以再抱一个孙子了;而孙玉美,离婚的回头女人,还能再嫁个小青年不成?肯定是改嫁越改越差,只能找个年纪大些的,很可能还得去给人家的孩子当后娘!
赵兴光同意了离婚。这是孙玉美第一次起诉离婚,却不是法庭上常见的那种一方起诉离婚,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很快下了判决,儿子赵小龙由爸爸抚养。
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兴光还有一种不真实感。下了夜班后,不由得掏出手机,想给孙玉美打个电话,号码都拨上了,才反应过来,已经离婚了!回到家里,屋子里空荡荡的,孩子跑到道上疯玩去了,或者在奶奶那边看动画片。天黑了,只有等他亲手打开灯才有一室清辉,那节能灯,初开时惨淡淡的散着冷白,要过好一阵子才逐渐明亮起来,能照出拒子、电视橱、床头橱上积攒的薄薄的一层灰尘。十多天了吧,屋里竟然没有打扫一次,地上有一团干巴了的黄色桔子皮,三两张花花绿绿的糖纸,一个亲亲虾条的空包装袋,都是儿子制造出来的些许垃圾。没有炒菜做饭的烟火气息,也没有洗涤、晾晒衣物的香精味或太阳味。半夜醒来,只有儿子幼小的身子蜷在他身旁,不再有妻子那份温软,赵兴光甚至开始怀念孙玉美夜里打嗝、磨牙、放屁的污浊气息。
相爱的两个人,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爱情,难道不是婚姻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他和她,真的就无望再一起生活下去了吗?也许,如父母所说,分开一段时间,孙玉美就能领悟出赵兴光这个男人的好处,也许,就会主动提出来复婚呢,那时,她和她娘家人的姿态肯定会低些了,复了婚,平平静静过日子,还是和和美美两口子。只是,在这段离婚的日子里等待复婚,太难熬了,到底有几成希望,赵兴光越来越没有把握。有时,实在忍不住了,赵兴光会给孙玉美打个电话。开始,孙玉美还接电话,虽然语气是冷冰冰的,但对他及孩子还都有些关切,后来,接了电话,那边没什么言语了,再后来,有时根本不接电话了,有事得由赵兴光先发个信息,她才接电话。
离婚两年多了,复婚的事还没有眉目,另娶,也还只停留在赵父当初的豪言壮语上,菜籽五村那边却传来,孙玉美家正在给她忙活再婚!赵母心急了,她赶忙给丈夫打电话,“你不是说,他们肯定能复婚吗?孙玉美她不等咱儿子了!你快点托上人,去她家里说和去,只要她能提出条件,咱就满足,分家就分家,垒墙就垒墙!”
孙玉美新婆家还是当庄,菜籽一村的。孙玉美早年曾和那男的看过对象,当初她没看上他。
孙家一派喜气洋洋。赵家父子及家族长辈进了孙家,赵父自己在床沿上坐下,招呼自家长辈也坐下,赵兴光自己找了个马扎,也在屋门口里边低头坐下。孙母冷眼看着:“你们这是来干啥?来给小龙他妈道喜的?俺受不起!”
“嫂子,小辈们年轻,有点矛盾就闹离婚。咱这不是还有小龙嘛,亲娘亲爷的一家人多好啊!”
“你早怎么不说这话?是谁说的‘长锯没有截锯快’?是谁说的利索索地早离早好?我们还是那句话,孙玉美和赵兴光离婚,不是为赵兴光不好,要怨就怨他爷娘!”
“当时就是为垒道墙!我们回去垒墙还不行?”
“你当我们闺女是啥?你们赵家门说不要就不要,说要她就再回去?晚了,我拿闺女的登记证给你看看?”
孙玉美再婚了,赵家也得张罗再娶。只是,赵兴光一个普通的乡镇企业工人,拖着“油瓶”,还是男孩,家里还有一个创殃烂的娘,大姑娘自然摇头不看这种对象。就是离婚的,丧偶的,也少有人愿意和他看对象。这事急不得,赵兴光也不心急。
赵小龙平时跟着爸爸、爷爷奶奶,有时也去妈妈那里或姥姥家。孙玉美再婚前住在娘家,小龙到姥姥家时一般是赵兴光接送。孙玉美再婚了,那里还有一个男人,赵兴光过去送总有些别扭。而且,小龙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学校就设在菜籽一村,平时都是小龙自己上学放学,自己去看妈妈或者回家,路很熟。
腊月十五那天,是小龙的六周岁生日。下午放学后,他从学校直接去妈妈那里,妈妈早和他说了,给他买了生日蛋糕呢。早上在家里,奶奶给他做了长寿面、煮了鸡蛋,但那些他不稀罕,一天在学校里,心里就盼着早点放学(幼儿园孩子中午不回家),软软的蛋糕,甜甜的奶油,嗯,上面一定还有漂亮的小黄花,小龙感觉自己能吃上一整个大蛋糕。不对,蛋糕得切开,让妈妈也吃,能不能捎块回家,让爸爸也解解馋?老师一说放学,小龙一溜烟就背着他的小书包跑了,同学们还在慢腾腾地出校门呢。一条胡同,两条胡同,再过三条胡同就到妈妈那里了,小龙呼哧呼哧跑得正欢,因为用力累得小脸红通通的。胡同里忽然蹿出了一辆摩托车。
“吱……啪……”摩托车没刹住,撞上了小龙。
小龙朝前飞去,摔在地上,惯性带着摩托车继续向前蹿,前轮轧过了小龙的右脚。变了调的童声撕裂着嚎叫在胡同口,凄厉,惨痛,像炮弹炸出的碎片一样流落到附近的角角落落。一两分钟后,后面的同学来了,近处的村民来了,孙玉美也从家里跑出来了……”冬日太阳落得早落得快,西天边,落日的余辉映得一团一团的紫灰色云彩泛着黄晕,也映得人们心里惶惶不安。
小龙右腿下端血肉模糊,只是哼哼,神志不清,摩托车早已不见影儿了。孙玉美吓傻了,只知道抱着小龙哭,她丈夫急忙拨打120求助,接着又给赵兴光打电话。赵兴光正在上班,摘了脸上的防尘面罩就往外跑,当值的班长看见他慌张的祥子,问他干么去,他才记起上班外出得请假:“我儿子放学后被人撞了,我得去医院,你帮我请假吧!”赵兴光边说边走,没有回头看班长,班长却跑过来一把扯住了他:“你带钱了吗?还是带着存折?”赵兴光想起自己身上没带几块钱,存折,也是在家里。班长把上班的十几个同事们都喊了过来,大家一听这事儿,都掏自己的口袋,班长拿着纸笔帮着大体记了一下,连整带零,两千来块。班长说:“先拿着这些钱去,用不着最好!你直接去医院吧,打电话让你父母从家里带些钱过去!”
孙玉美跟着120急救车陪小龙到了王河县人民医院,随后赵兴光来了,赵父赵母也来了。医生给小龙实施了截肢手术,从右小腿末端往下,都已经没有办法修复再造了。小龙还在昏迷中,头部撞伤,脑积液,引流无效,需要手术。
到底是谁撞倒的小龙,无人看见。后来小龙清醒了,他只记得是辆摩托车撞了他,骑摩托车的是个小青年,他不认识。
小龙在医院里住了39天,医疗费花了五万多元。医生说,再过一年多时间,小龙的右腿下面可以安装个义肢,练习走路。
当初小龙住院时,孙玉美从家里带着了所有的现钱,一千多块,后来的治疗费,都是赵兴光交的。以后小龙安义肢,也将是一笔不小开支。赵父想了想,这不是个事儿,虽然离婚了,但孩子还是叫赵兴光爸爸,叫孙玉美妈妈,孩子受伤,爸爸作为抚养人有义务拿钱医治,那做妈妈的,就没义务吗?况且,这还是小龙在去孙玉美家的路上受伤的!赵父又去咨询程律师,得知,离了婚的父母,原则上一人一半承担孩子的医疗费。赵父请程律师代写了诉状,到法院交了诉讼费,以赵小龙、赵兴光的名义,要求孙玉美支付小龙住院医疗费及将来安装义肢费用的一半。开庭时,孙玉美没有到庭,法院缺席审理并判原告胜了官司。判决后,孙玉美也没上诉,判决书很快生效了,赵父又向法院申请了执行。
赵父没能看到法院执行来小龙的医疗费及义肢安装费——事实上,后来赵兴光也没有在执行上再较真,任其不了了之。
孙玉美再婚后不久,从赵家迁走了户口。一年多后的秋后,村里大调地,要赵家把原来分给孙玉美的地退回来,什么时候加了人口,再从机动地里给分地。要退回的那块地里,曾盖了一间小屋子,用于瓜菜成熟期晚上看地。屋子很简易,黄土加麦秸穰子和泥垒墙,几根旧檩条,上盖旧瓦。赵父趁着休班,到地里拆这个小房子,想把旧檩条、旧瓦拾掇一下运回家里。他半下午时从盐场赶回了家,往地里走时,天已向晚。拆小屋子的工程量极小,预计吃晚饭时就能回家了。赵母做好了饭,加炒了菜,和小龙在家里等着。天早已全黑了,在家里能听到邻居们刷锅刷碗的叮当声,赵父还没回来。赵母给他打了个电话,却没人接听,她忽然间慌了神。菜籽庄的地离村庄较远,赵母叮嘱小龙先吃饭,自己推了自行车往地里骑去。赵父斜卧在小屋南墙边,两根檩条压在他身上,空气里迷漫着血腥的气味,天已经全黑了,赵母却能清楚地看到赵父头上及檩条上凝固的暗红血迹。
盐场给了两万来元的抚恤金——赵父属于非因工死亡,抚恤金的支付标准很低。事发时,离赵母的55周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再过这两个月,她才是法律意义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是丈夫的被扶养人。差了这两个月,她还属于有劳动能力的人,因此,虽然丈夫去世了,丈夫的工资也停发了,但是,她却不能按月领取遗属补助。顶梁柱倒了,赵母的天也塌了。
赵父过了一周年祭日,全家人脱了服,赵母希望,家里能有点什么喜事冲一冲,去去家里这几年来的晦气。她又到处张罗着托人给赵兴光介绍对象,模样不论,离婚或丧偶不论,有无子或女不论,要多少彩礼不论,只求女方能痛痛快快嫁过来,和赵兴光正正经经过日子。她盼着,家里能像个正常人家。
赵兴光又开始了看对象,陆陆续续地看了十几个。虽然对方都是拖儿带女有婚史的,情况不比赵兴光好,但是,看过对象后,都没了音信。一年多后,终于有个女人同意和赵兴光结婚过日子。女人是四川人,七八年前,从老家过来,嫁到了王河以东的张家村,离菜籽庄有二十多里路。女人生有一个儿子,10岁了。不过,女人的户口一直没有从四川迁过来,和张家村的男人只是举行了结婚仪式,并没有登记。女人说,那个男人总喝酒,喝了酒就打人,所以,不和他过了。想去法院离婚来着,但本来没有登记,法院也没法给判离婚。她离开张家庄到处打工生活,已经三四年了。开始时,那个男人还有时跟踪上她,然后找人把她弄回家,打一顿,关在家里,但不久她再想办法跑出来。这一年多了,那个男人没再找她。只是,她自己带着儿子,不敢回去问那男人要儿子的生活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赵兴光和四川女人结了婚——说是结婚,就是让人看了日子,选了时辰,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把女人迎娶进门,并没有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婚后,赵兴光托人,把女人的儿子安排在了菜籽庄小学读书。赵兴光以为,他接下来的人生,可以这么安安稳稳、有妻有子地生活下去了,赵母也这么以为。这几年来,赵母的作风收敛了许多,从来不再在家里创殃烂,类似的暧昧,总能避着儿子、孙子。四川媳妇娶上门后,婆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媳妇带来的孩子,她也是细心的照料,表面上看不出多少与对待小龙的差别。媳妇好吃不懒做,性格很温和,做事却很麻利,只要不刮大风下雨,她天天外出打工,纸箱厂,大棚内,建筑工地,劳务市场,哪里工钱高,她就到哪里干活儿。虽是再婚夫妻,两口子看起来却很和谐,赵兴光把工资折交给女人拿着,女人下工回来,经常从路过的夜市上买些肉食、蔬菜、水果、孩子零食等,家里的伙食不再仅靠赵母一人采购,全家人吃得不错。一个多月后,村里的人都说,后娘没虐待小龙,他明显长高了一截,白胖了,身上的衣服也比原来光鲜了。小龙管四川女人叫妈,四川女人的儿子也管赵兴光叫爸。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女人说:“我要领孩子去趟王河县城,给他拍套写真集,然后寄到我老家给他姥姥看看。”赵兴光说:“带足钱,拍得好点,也洗几张大点的拿回家挂上。你看哪个照相馆好,有空我也领小龙去拍,他还没拍过呢!”女人起了个大早,赵兴光也起了个大早,用摩托车把女人娘俩送到菜籽庄西三里路处的大路口坐客车,然后,赵兴光直接上班去了。傍晚赵兴光下班回家,女人和儿子还没回来,赵兴光想打电话问问,女人的手机却提示关机。赵兴光想起了什么,打开了一个抽屉。结婚时给女人买的“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坠,女人平时并不戴,今天出门时也没见女人戴上,但是却不见了,平时女人放在里面的身份证不见了,总放着的十张八张粉红百元钞不见了,再底下,赵兴光的工资折不见了……
门口,红彤彤的过门钱鲜艳如血,双喜字、对联上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大字还都乌油油地泛着亮。房屋前脸在结婚前用铝合金门窗包了厦,新刮了瓷粉的墙面白得晃眼。新床,新被褥,新橱子,新柜子,新电视,新电脑。刷了鲜亮黄色油漆的后窗子打开着,一阵风透进来,从天花板中央扯到四个墙角的红绿拉花沙啦啦地响。结婚还不满百天。摆设一新的新房没能再等回那个四川新娘。
后来,赵母再托媒人给儿子介绍对象,赵兴光又陆续看了四个。第四个对象是在媒人家看的,媒人也是菜籽庄的。女人听媒人介绍了赵兴光的情况后,和媒人说:“只要男人没有打女人的毛病就行。”女人左眼视网膜脱落,右耳耳膜穿孔,都是她以前的男人打的,她是看在儿女的情面上,才没把那男人送进监狱。女人比赵兴光大十多岁,她的女儿已经结了婚,儿子也订了婚。女人坚持离婚时,女儿和儿子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劝过母亲不要离婚,但又心疼母亲。一场婚离下来,女人的神经也受了刺激,有时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好在,儿女都大了,她想再找个人家,只要男人能和她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看完对象,女人对赵兴光很满意,女人顺便到赵兴光家看看宅院。女人要走,赵兴光去送她。出了胡同往大道上拐时,赵兴光从摩托车反光镜里看到,小龙身子藏在胡同口,只向外探出头来,朝着赵兴光前行的方向张望。
晚上吃完饭,赵兴光在看电视,小龙在做作业。忽然,小龙站起来,走到了爸爸身边坐下,低着头,并不看电视,一会儿,他拉了拉爸爸的衣袖。赵兴光看着儿子,想起他送女人时儿子藏在胡同口的目光,笑了笑:“有什么事你说,是不是你不满意我看的那个对象?”
灯光下,小龙的脸明显涨红了:“她太老了,都快跟上奶奶了!也太丑了,都没奶奶漂亮!”
“奶奶不能照顾咱一辈子啊,咱以后还要照顾奶奶呢!我再找个人,就是为了以后照顾奶奶,也照顾你!”
“哼,你再结了婚,是不是就不要我了?你会不会再生一个孩子?我同学们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爷!”
“哪能呢,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就像你说的,她都那么老了!不会再生孩子了,还是只有你这一个儿子!”
“妈妈不要我了,爸爸你可不能也不要我了啊!”小龙的话里带了哭腔,泪珠子已经淌出来了,迎着电视,蓝莹莹的闪亮。
赵兴光伸手给儿子擦去了眼泪,他觉得自己脸上也痒痒的。想起来,和孙玉美离婚,整整十年了,小龙已经十三四岁了,接下来,就是小龙的青春叛逆期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