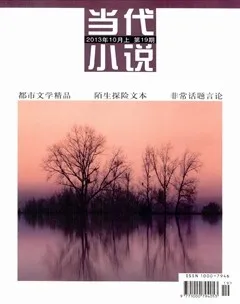2013年夏天那个游荡的魂灵
2013年夏天那个游荡的魂灵
张丽军
2013年夏天,烈日炎炎,不仅热死了几个英国人,也热死了几个上海人。这注定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季节。随着余华小说《第七天》的出版,文学对当下社会生活关注的热度也随着在不断升高。那个在地域和天堂之间“死无丧身之地”的孤魂野鬼在2013年的夏天游荡,不仅在《第七天》,在乔叶的《认罪书》中游荡,也在柏祥伟的《断指》和程相崧的《动棺》中鬼魂附体。
余华是我多年关注的一位作家。但是近年来,余华的创作,不符合我的阅读期待。即对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唤》等名篇佳作的余华,在2007年创作出《兄弟》这样对生活做匍匐行走姿态,我是很不满意的。作家不仅要表现对生活的活灵活现的描绘,更需要对生活的批判和反思。但是,我这次依然是失望了,因为余华的《第七天》还是对当代生活中的“荒诞”做了虚拟化的艺术想象,塑造了一群群“死无丧身之地”的孤魂野鬼,在“无地之地”流浪。然而这想象依然是贫乏的、缺少生机的,乃至有某种人为地噱头的嫌疑。这种评价,是我余华这位成名作家的苛求。实事求是地说,比起一些同时代作家,余华对现实生活荒诞性、怪异性、悖论性的表现,是让我尊敬的。余华是一位贴着生活地面飞翔的作家,至少贴着地面、接着地气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就在于,仅仅贴着地面,对于一位优秀的,乃至是包含着某种伟人作家期待的作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作家要拿出思想性,能够进行超越时代的精神审判。
余华的问题和局限,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今年夏天在一次作家对话会上,一位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时代生活的生动性、复杂性、荒诞性已经超出了文学,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即生活远比文学还要精彩得多,那文学还有何用?作家还有何用?作家还能够做什么?
这个作家问得很精彩,这不仅是她的困惑,也是很多作家的困惑。我对此坦言,文学就在这里显现出它独一无二的精神魅力和艺术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新闻报道和纪实书写可以更逼真,但是它们依然代替不了文学。文学是作家对生活的充满独特生命感情的审美发现和书写,里面凝聚了作家对故事中人的命运、情感、心灵的关怀和思考,是对生命个体的情感抚慰利悲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个荒诞的事不是主体,其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对人的细致入微、无所不在的关怀。余华《第七天》不缺少的“情与爱”,缺少的细致入微的关于人的细节和深入骨髓、痛彻心扉、酣畅淋漓的生命激情。从这点而言的话,《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乔叶的《认罪书》,恰好弥补了这种欠缺。
乔叶这位70后作家在写作了一些优秀散文作品后,开始转向小说创作,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突出成绩。乔叶的中篇小说〈指甲花开》、《最慢是活着》、《旦角》、《叶小灵病史》等作品都写得摇曳生花,引人入胜。这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认罪书》是中国70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突破。《认罪书》的题头说,“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小说以一个出版社编辑的叙述人讲出了故事,采用的故事套故事,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的叙述模式,一步步把那个“游荡的鬼魂”引出来。深刻的是,小说不仅写出了一个80后女孩心中的自我所时时隐匿的“鬼魂”,而且写出了梁知利梁新一家人所隐匿的“鬼魂”——“梅梅”。小说中的“我”就是“梅梅”鬼魂的再现和复生。不仅梁家家人在认罪、赎罪,而且那个“文革”时代的所有人都在认罪、赎罪,即连80后的“我”也在认“我”自己的罪。显然,70后作家乔叶触及了余华等50、60后一些作家所不愿触及的、深入灵魂的“原罪”的问题,具有浓郁、深厚的精神意蕴。
与余华、乔叶相类似的故事叙述者,是山东作家柏祥伟。《断指》是柏祥伟发表在2013年第6期上的《山东文学》上,讲述了一个“我”去寻找被小煤窑硐死在地下的父亲灵魂的的故事。“我”从呜呜的风声中,感觉到了父亲的灵魂:“虽然我看不见风,看不见我爹的灵魂,但是我听见呜呜的风声了,我听见我爹在呜呜的风声里奔跑。”怪异的是,我遇到了过着猪狗不如日子的老姚。老姚听完了我爹的故事,说:“我要赚钱,像你爹一样赚钱。”就在这一瞬间,我爹灵魂钻进了老姚的皮囊。故事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混合了我爹灵魂的老姚选择了自我断指、跳楼自杀的方式,来换取生命的“价值”。这无疑是当代中国荒诞故事的新佐证。人兮,抑或鬼兮?人情未了。
山东80后作家程相崧在2013年第5期的《时代文学》进入了赵月斌主持的“鲁军新势力”专栏,发表了《响器》和《动棺》两篇小说,呈现了不俗的实力。这两篇小说也呈现了“游荡的鬼魂”景象。《响器》明明是为死去的鬼魂抚慰灵魂的哀乐,在当代中国乡村却演变成了竞相争夺金钱利益的流行、性感演出,这不仅昭示时代整体的心灵梦魇,也显现出内在精神“原罪”,正如赵德发在以往发表的《路遥何日还乡》的小说名作中所展示的当代乡土中国民间原有文化的衰落和荒芜,谁来接纳这些刚刚逝去的鬼魂,又有谁来救赎这些正在沉沦的物欲灵魂?救赎之路迢迢,不仅遥远,而且无期。程相崧的《动棺》中的乡村权力者却无法让失去的祖先灵魂安宁,为了利益动起了“动棺”的念头,乃至最后精神出了问题。小说结尾耐人寻味:爹慢吞吞对我说,“你这个病,若是能让你二叔穰治穰治,保准早就好啦。娃儿啊,你说说,你二爷爷啥时候能回来哩?”这是现代性医学所无法医治的乡土中国精神心病。
此外,《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上的鲁敏的《小流放》,《时代文学》2013年第5期常芳的《如果蝉活到第八天》、张锐强的《隐形眼镜》、叶炜的《狗殇》和刘照如的《刘兰的婚事》,《当代小说》2013年第11期彭兴凯的《于大美的等待》、刘爱玲的《霍普金斯国际机场》、李立泰的《认干娘》,《当代小说》2013年第13期柏祥伟的《易时水》,马卫巍的《做暖》,《传记文学》2013年第6期设“中国思想肖像”专栏对邵洵美进行重新勾勒的《“沙龙”中的文人》等同样较为精彩。
我们该如何面对岁月的残忍流逝
乔宏智
今夏的文坛较多地出现了关注生活、表达情感的小说作品。下面是两个有关“逃离”的故事。短篇小说《流年》(李心丽,《当代》2013年第4期)讲述了一场大妻之间带有离奇色彩的逃离。闫江平和陈若兰是两口子,因为闫家里老宅拆迁,是否将闫的父母接过来暂住的争论竟成了二人矛盾的导火索。一直对妻子没好气的闫江平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了,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妻子一直渴望着丈夫对这半个月里发生的一切做个解释,而丈夫最想讲给的一个人,也是妻子。但他就是拧着,不给她讲。“互相拧着,直到半年后离婚。但离婚并不是二者的本意。”二十多年的婚姻,彼此都感觉就像是一晃而过。“在时间的流逝中,他有了倾吐的欲望”。离婚一年后,闫约陈若兰讲述了当时的一切,尽管陈若兰惊讶不己,但他们已无法再回到过去。流年让他们活得越来越明白,但流年也将他们的幸福婚姻剥夺。
第二个有关逃离的故事是鲁镇烟讲述给我们的《西班牙哪有马赛港》(《钟山》2013年第4期)。小说开头写道:“我是怎样离婚的,已经忘记,但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怎样结婚的”。小说接近末尾处又写道:“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离婚了,但是,我真的不是为了离婚而离婚的”。有趣的是,读完整个故事,我突然发现作为读者的我也无法说清到底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怎么样就离婚了。小说题目中的马赛港是在法国,可生活中我们却常常遇到类似于马赛港在西班牙的事情。小说里学中文的“我”与学财经的妻子在交谊舞培训班里相识,三年恋爱后我们走在一起。“我”在电视台工作,妻子在海关一家附属公司工作,尽管我们的婚礼办得仓促,没有那么风光,可外人看来良好的职业应该能保障家庭生活的幸福。而婚后我们却因为买菜、做菜等这种小事导致夫妻关系难以维持。又因为丈夫是一个书痴,一直有着文学梦的追求,不仅是妻子难以理解他,面对电视台里的尔虞我诈他也不愿意同流合污,事业发展也一度跌入谷底。但在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妻子却背叛了丈夫,有了外遇。人生低谷期丈夫欲借发廊发泄愤懑,却没等发生什么就被抓进了公安局。尽管丈夫凭借自己的才华从风花雪月事件的肇事者升迁为电视台的广告部主任;但他却一直想要逃离鲁镇,逃离现有的家庭。于是丈夫为了离开,选择了考研。并最终成为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生。随着他的逃离,婚姻也完结了。这篇小说在叙述上采用了叙述人跳出文本的技巧。小说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开始部分作者便跳出小说进行了介绍。文章结尾作者又采取第三视角叙述对曾经的自己进行反观,这些都是作者对叙述技巧的运用。
尽管以上两篇小说作者不同,行文风格也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我们生活中最平常的夫妻、家庭生活,尊重我们情感的真实。观照人本身,观照人内在的情感,才是文学最应具有的情怀。遵从内心情感的逃离,恰是文学真实的回归。除了以上两个故事,今夏的文坛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现简评如下:
长篇小说《家有真经》(央歌儿,《当代》2013年第4期)以江家的两个女儿秋慧和秋萍的婚姻家庭生活为主线,用家庭情感伦理剧的叙述手法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青梅》(姚鄂梅,《大家》2013年第3期)和《不信时间能治愈》(卢岚岚,《人民文学》2013年第7期)是两部少女遭受性侵犯的伤痛文学,作家将人文关怀的视角移入心灵深处。《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邓一光,《钟山》2013年第4期)借电影编剧“喜子”的一段经历讲述了深圳繁华背后发生在老一代建设者们身上的故事。文中对酒吧光怪陆离的描写颇具“新感觉派”的感觉。《银子》(罗伟章,《人民文学》2013年第7期)是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将“八大王屠川”的故事进行了新的演绎。史实与传言的结合使文章引人入胜,让读者不禁对张献忠的故事又产生了兴趣。《轨道八号线》(邓一光,《大家》2013年第3期)讲述了几个模具车间的工人在下班后乘坐轨道八号线进程的见闻和感受。在他们些许怪异举动的背后,都市的迷幻展露其间。《消失的喇叭声》(陈吕瑞,《钟山》2013年第4期)讲述了在阶级斗争年代寡妇乔翠与吹喇叭的艺人老翁之间围绕一个弃婴发生的悲剧。将人性的善恶与那段历史的荒诞揭露无疑,读罢令人感慨唏嘘良久。
《我的颂乃提》(了一容,《人民文学》2013年第7期)讲述了伊斯兰男孩伊斯哈格举行成人礼的故事。通过它,我们了解了“割礼”这一伊斯兰民族习俗。《我的特务生涯》(宋海年,《人家》2013年第3期)根据国民党特务罗丙坤的真实故事改编。小说在形式上独特,开篇便是第七章“点杀行动”,全文共十小节,而第一小:口的内容却直接省略了。《射日》张宜春,《钟山》2013年第4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在抗战年代专用绣花针杀鬼子的抗战英雄葛柳的故事。小说可读性强,读罢令人直呼过瘾。《狮子山》(包倬,《人民文学》2013年第7期)是一篇具有实验色彩的短文,川简短的标题将文章分为六部分,用片段化的手法反映了狮子山风岭镇人的生活状态。《秒杀——〈艳遇指南〉之二》(蔡晓玲,《大家》2013年第3期)讲述了记者如歌和社科院专家未名之间的一段情感纠葛。其间夹杂着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神童》(薛忆沩,《收获》2013年第3期)没有落入俗套,去讲述神童成功史或重复伤仲永的故事,而是关注了所谓“神童”的心理,将关怀点下移到不为人知的隐秘地带。《羽仙记》(崔曼莉,《大家》2013年第3期)借天上羽仙的一个梦,将古时候众人随一长衫人游山乐水的见闻记录下来,亦真亦幻,似梦非梦。《在路上》(张宇,《莽原》2013年第3期)讲述了作者一行人往南极旅行途中的所思所见。西藏的尼玛石、阿根廷独立广场……让我们难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人对异域风情的怀想有了线索。
《回南方》(王秀梅,《芙蓉》2013年第3期)用短篇小说的篇幅为我们留下的是一对家燕不老的爱情。人与动物虽不能交流,但爱的能力却不分种属存在于万物生灵之中。《驴伴》(安庆,《莽原》2013年第3期)讲述了瓦塘南街最后四个养驴户的人生和家庭故事,其间渗透着家庭亲情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变迁。《刘丽香的春天》(谭岩,《芙蓉》2013年第3期)年近中年的“丽香发廊”女老板突然遇到了一份爱情,走进春天的她愈发年轻,可面对工作中因意外双腿瘫痪的丈夫,她选择了痛苦的放弃。刘丽香,心中承受的是爱情与道德的抉择之难。《路玉珠的幸福生活》(涂强、韩江新,《莽原》2013年第3期)作者用并不离奇的故事,用平淡如水的感动,用真挚的深情为玉珠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该死的脚印》(少一,《芙蓉》2013年第3期)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脚印线索,却惊动了一级级领导直至成为媒体报道的社会热点。经验丰富的刑侦队长,容易破的是案子,难破的是复杂的人心。《来自伊尼的告白》(南翔,《天涯》2013年第4期)选取了东南非莫桑比克托佛海域里最后一只蝠 鱼为叙述者,讲述了与她的“爱人”——潜水员芬亚之间一段超越物种、跨越生死的感情,呼吁着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和热爱。《变革者的咒语》(祝勇,《小说界》2013年第4期)以现代视角重述和阐释了商鞅变法、秦国统一的历史,在叙述史实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历史看法,成功的变革者都未得善终,历史的咒语值得我们思索。
《小故事》(黄孝阳,《天涯》2013年第4期)由9个独立标题的小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都有如寓言般有超越人世的神奇,每一个故事也同样引发着我们的思考。《五道口贴吧故事》(贺奕,《作家》2013年第7期)采用了完全的贴吧讨论的格式,结合北京五道口的历史文化与俄罗斯美女的离奇凶杀案再加上作者独特地构思,小说获得了非常强的可读性。《一头驴的故乡》(王风国,《天涯》2013年第4期)讲述了一个“卖不掉”的驴的故事,幽默背后透出真挚的感情。《广岛之恋》(阮庆岳,《小说界》2013年第4期)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我”的不知真实还是虚幻的梦境,爱侣无缘由不断加剧的病情,不知道是否存在又是否跟踪我们的“他”,这一份恋情神秘又纠葛。《蜻蜓点水》(黄咏梅,《作家》2013年第7期)将关注点放在了迟暮之年的老年男性的心理上。虽已年老,但心里依然有对女性的幻想,作家无意对此进行价值评判,只是一种诉说。《十三大街》(钟文音,《小说界》2013年第7期)“我”是送快递的“大街”,“她”是开理发店的“十三”,两个身心都受过伤的普通人,平凡的生活里互相帮助,真情无价。《暮鼓》(铁凝,《作家》2013年第7期)写了一位一天天走向衰老的贵妇,一位衰颓得甚至分不清性别的女性民工,一只和贵妇一起在黄昏里静听鼓声的老猫,我们该如何面对岁月的残忍流逝?
万语难言一声“家”
计昀
炎炎夏日,作家关注的第一群离家者便是那些为了生存到缄市底层打拼的农民工。茨平的《猪坚强》(《星火》,2013.3期)以写实的风格客观再现了两代农民工艰难的生存处境,老一辈居无定所,新一辈又缺少像老一辈能吃苦的精神,生活更是步履维艰。王子辰的《种桃》(《福建文学》2013.7)以凄婉的笔调,从另一维度,把农民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显现出来。然而,生活的重压与精神的痛苦并未使他们崩溃,相反,他们以一种难能的坚韧与乐观消解了生活的疼痛,止如杨逍的《白墙》(《星火》,2013.4期),就对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的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小说中奶奶形象的生动塑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可贵,“活着”的幸福。同样是农民工问题,纪江明的《三两半》(同上)关注的确是那些通过奋斗跳出农门,在官场斡旋的“第三代农民”的心灵历程,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他们体面之下的无奈与空虚微妙地表现出来。但是,对于这一类的作品,我们必须明白,“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如何能超越以往农民题材创作的成就,是作家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
然而远离故乡的还有这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来到大都市,甚至侨居国外,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就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蒋一谈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六期的《故乡》就是以淡淡忧伤的笔调抒写了三代人“无乡可归”的疼痛。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美国,父亲决定去已经定居美国的女儿家疗养一段时间,可是到美国后,他更是增添了几分失落。整个故事安排张弛有度,首先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遭受不幸的西班牙裔母子揭示了身处他国者的生存的不易,精神上受到的伤害让他们最终选择以逃离的方式踏上回国之路,但故事到此并未有个完满的结局,作者为我们揭示出更深层的悲剧:即使他们回到祖国也要继续承受无乡可归之痛,因为他们的家园早已经遭受到了破坏。
蒋一谈继而将西班牙裔母子事件连接起老人一家三代的命运。孙女tifa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从小受美国教育的Tifa和日本男孩Rick对于钓鱼岛这样的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再拥有一个本国人对主权维护的敏感,它揭示了华裔后代无家国观念的巨大悲哀。小说叙事的一个重大成功之处就是把时政的热点和家庭的小事并置于故事之中,从而使我们深刻地体悟到“故乡”的双重内涵:大至国家,小至乡土。乡土连接的是一大群离开故乡,来到都市打拼的农村儿女的悲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们回首故乡,发现早已经物是人非,故乡已然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等待他们的,是无限的无家可归的哀鸣。对于女儿这一辈,身处两种文化的尴尬境地和亲情的万般纠葛之中,更是身不由已有国难回。这篇小说十分注意故事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使故事涉及时政大事却又避免了说教的空洞;走进生活细部又避免了气度的狭小,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
亲情和爱情一样,同样是个永恒的话题。余西的《熊猫》(《上海文学》,2013.08期)和《我们都是纸老虎》(《西藏文学》,2013.04期)都表达对舅舅的深沉的爱。但两篇小说相比,前者的生活气息更为浓烈,而后者更多的思辩意味,融入了作者对和平、自由、种族等上升到人类高度的问题的深刻的探讨。除了这两篇之外,刘庆邦的《保姆北京之十三》以一对夫妻退休后平淡的生活印证了那平凡而又永恒的爱情,这种爱饱含着亲情的雨滴,渗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不失为一部佳作。还有一篇作品值得一提,杨逍的《白墙》(《星火》,2013.04期)把母爱的主题与生命的主题惟妙惟肖地融合在一起,远远超出了一般亲爱的抒写,多元的思想内涵耐人寻味。钟二毛就在中篇小说《小中产》(2013.07,《长江文艺》)中揭示了这一点。整部小说叙事的风格很像新写实的作品,讲述的是主人公从一个理想要终生献身新闻传媒的有为青年,如何最后变成一个为了谋生存而彻底放逐自我的小市民的。全篇围绕着“家”与“理想”的相互抗衡展开富有张力的叙述。主人公为减轻首付而与妻子假离婚;为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冒犯了一家大的红木家具厂,最终被迫辞职。失业后的“我”继而又遭受自主创业的失败,长时间收入的入不敷出让家庭艰难为继,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妻子的爱最终让“我”选择离开自己钟爱的新闻传媒,小说的最后,“我”以调侃式的语调说:“与有缘人,做无耻事,赚钱我就干”,这句无可奈何之语为小说的叙事划上一个苍凉的尾号,显示出都市繁华背后人力的渺小,以及80后幸福的失语状态。除了《小中产》之外,郭海燕的《理想国》(《上海文学》2013,07期)同样也是哀叹被现实所磨损的青春的逝去。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两篇小说共有的局限,它们在快节奏的叙事中只抓住了生活的表层,忙于揭露却忽略了对整个社会和八零后生存状态做更深层次的思考。80后的何去何从,社会的弊病如何解决,仍然是我们作家需要深思的问题。
陈永林《堂嫂》(《福建文学》2013.07期)是一篇充满女性关怀意识的短篇小说;邱贵平的《洪水清澈》(《福建文学》2013.06期)和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我想有个小弟弟》(《西藏文学》2013.03期)也通过在农村里和城市中生活的两个孩子心灵的创伤向社会唤起“关怀孩子”的呼声。王先佑的短篇小说《谁打了我一巴掌》(《西藏文学》,2013,04期)就是以主人公在人群中被陌生人打了一巴掌这件事情所引起的风波显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以及人内心的空虚、邪恶等各种精神问题。弱势群体对温暖的渴求,对无家可归状态的拒绝,使得这一类小说拥有了特殊的情感力量,让人读之深受触动。
其实,在这个商业化的后工业时代,人的灵魂的无家可归更为可怖。对于赋渔的《安身之处》(2013.07期《上海文学》),我认为可以以“无处逍遥”来概括主人公朱子安的生存状态。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道出了中国古代精神品质的内核:恬然之乐的逍遥,且这颗逍遥的种子是深深地根植于儒释道的土壤之中。《安身之道》中朱子安就是一个与都市有着紧张关系的抑郁者,他企图以儒、道的力量来解脱精神的枷锁,以实现“逍遥”的愿望。小说的开篇就点出他与《孟子时代札记》的关系和与仙鹤观道长见面的情形,并也由此引出上篇“放生”的整个故事。朱子安从秦淮河到玄武门,从玄武门最后到长江,他始终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给鱼放生的地方。放生其实就是意味着为鱼儿们换了一个行刑场地罢了。这里,生态环境问题被深刻地呈现出来,同时,整个故事也为我们提供思考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作者冷静清晰地揭示出:传统文化已经不具备足够人的威力来化解现代各种复杂的矛盾,解决人与大自然双重流离失所的困境需要另辟蹊径。那么,路在何方呢?或者还是无路可走?作者巧妙地把此抛掷给读者,发人深思。
发表于《四川文学》的《回乡过年》(2013,07)就是以陈尔东教授回乡过年的所见所闻来揭示第三代农民在离开土地之后和传统仁义文化的决裂,他们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道德的丧失和人性的异化面。这种异化将成为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毒瘤,故事中赵楚南和赵楚北两兄弟形象的塑造就是这个毒瘤的最深刻表现。
琴瑟争鸣,亦分亦谐
辛晓伟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爱情与婚姻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不会逃避掉的一个阶段,在思想极度开放的今天,在充斥各种主义、观念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仿佛也变得不再“韧如丝”。所以在琴瑟争鸣中,亦分亦谐,可能奏出一曲和谐优美的双重奏;也会可能琴瑟不调,乱弹一通发出乱耳之音。
《北京文学》2013年第7期刊登的铁凝新作《火锅子》是我们对爱情的完美想象。这篇只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绵延温暖的情感故事。作者不愧是一位有着非凡写作功底的大家,她用简单朴素直白的语言,假以“吃火锅”这一故事载体,干净利落的勾勒出发展脉络,字里行间却渗透着这对老夫妻浓浓的情意。由爱情到婚姻,两人的感情一直都是平淡中见真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并没有变得沧桑,一切还是当初的模样。两位老人在耄耋之年来诠释真爱,的确给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地上了一课。从擦出火花的爱情闪电,到平淡如水的家庭婚姻,小说主人公传授给我们的是“婚姻经营秘笈”。小说中的两位老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经营一场天长地久的婚姻,“由着她的小脾气”可以看作是一剂调和感情的良方。柔情与甜蜜伴随两位老人温柔了时光与岁月,超越了时间的打磨,把婚姻演绎得完美无缺。小说家常的故事题材温暖和煦,却在这种平淡中最接近读者的生活,同时打动心头最柔软的那部分,仿佛是淡淡的微笑,琴瑟和鸣,久久回味。
然而,琴瑟争鸣,一起弹奏出的还有可能是残缺与破离。《飞天》2013年第6期刊登了江雨薇的中篇小说《犬吠》,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对情感世界透彻而又深刻剖析的小说,尤其是女主人公对家庭婚姻的描写、在不幸婚姻之外对幸福的追逐轻易地俘获了众多读者的眼泪。作者把普通琐碎的题材紧贴人物的内心与灵魂来叙述,在惨烈的文字里将情感的起伏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灵与肉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背离把女主人公推向了无边的苦海之中,情感处在无依无靠的悬空状态。小说讲述了一位没有爱情却草率结婚的女性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的煎熬与苦痛,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姻之路走的是那么坎坷。“重男轻女”观念的挑战,小说对这一问题的的揭露令人胆战心惊,具有极强的生活感。琴瑟争鸣,步调如若不一致,就好比夫妻心向不一,也就不可能演奏和谐之曲。小说中林莺的心灵这架竖琴被韩峰拨动后,心弦久久颤动,两人并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直到最后,作者还是只是揭示出灵魂深处的痛苦与困惑,并没有好的解脱的方法。
无独有偶,《飞天》2013年第6期同时刊登了另一位男性作家张运涛的短篇小说《去上海喝咖啡》,这篇小说在短短的几千字之内,讲述了一位有着文艺气息、家庭生活平淡如流水的妻子在一念之间差点和老同学飞到上海喝咖啡的故事,背后当然有很多不可明言的意图。她不满足于现在生活的乏味与平淡,总想追求生活中的那点奇幻与旖旎。其实,这种精神上的追求是很虚无缥缈的,它让人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出门的时候,崔巧其实还隐隐怀着希望,希望老公突然回来。平时崔巧出去打车都要等好久,这天却出奇的容易”。实际上,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跨出这一步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显得是那么荒唐可笑,飞机因为天气故障、机场流量控制等各种原因最终没能成功飞行。当世界上那些巧合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一起发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命中注定。飞机没能飞走,注定崔巧“去上海喝咖啡”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所以小说作者在结尾的地方以这种方式向读者揭示这种做法的不可取。意在告诫万千读者,如若现在的婚姻家庭很幸福,不要放纵自己一时内心的悸动。山河静好,怜取眼前人。
眼前人的存在,是一种踏实,也是一种精神的慰藉。而一旦这个人的离去,琴瑟缺一,留下的只剩回忆,回忆过后教会我们的还是要勇敢和担当。《时代文学》2013年7月(上)刊登了作家寒郁的小说《授粉的女人》。这篇在多处选载的小说的确值得我们去阅读、去思考。小说语言淳朴,意境优美。故事凄美动人,字里行间情真感人,读过之后不禁潸然泪下。原本恩爱夫妻,孰料丈夫横遭车祸,面对家中顶梁柱的轰然倒塌,巧祯一时间缓不过神来,在床上躺了好多天,精神跌倒了谷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坚强勇敢的农家妇女到底还是走出家门,走出了悲伤的阴影。故事叙述的平淡宁静,没有惨烈,没有伤心欲绝,作者以不凡的笔力把小说写的凄美动人,流着泪水却又嘴角上扬。走出悲伤的巧祯用回忆来取暖人生,阴阳两隔,两个人的爱穿越走到了一起。因为在小说的结·尾,“隔着泥土,她终于看到长庚了”。《山东文学》3013年7月(上)薛原的《晚钟》,小说中的周辰同样无比怀念逝去的老伴,给读者带来一份夕阳晚年的动人情愫。
发表在《辽河》(2013年第7期)的《滴水观音》,作者张玉兰以令人诧异的结局让人值得反思,文章虽短小,却耐人寻味,意义深刻,它教人要像观音一般学会宽容与慈悲。长白山的小说《迁坟》则是一篇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微型小说,揭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伪善”“伪孝”现象的存在。谢俊芬的《菜花飘香是归期》的结局同样令人大吃一惊,一张假的化验单召唤亲人的归来,即使是欺骗,仍让人觉得十足的幸福和甜蜜。而赵欣的《朋友的漂亮妻子》则是一篇道德感厚重的小说,它呼唤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要真诚善良对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鸭绿江》2013年第7期刊登的李兴泉的小说《画驴》写出了当今社会在拜金主义腐蚀下人们的良知面临何等严峻的考验,文化人能否坚守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
刊登在《延安文学》(2013午第4期)的三篇小说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来阐释了当下众生的生活姿态。杨耀峰的《占炕被子》从民俗入手,看似滑稽可笑,但也从中渗透了对人情、道德、义与信的评判。而刘国欣的《城客》则写出了一代人对现世的困惑,对未来的迷茫,终日忙忙碌碌却依旧浑惑无知,左雯姬的《暴涨》更是写出了物质消费下亲情关系的冷漠,甚至是缺失。2013年第4期的《西部作家》发表的蒋九贞的《河那边有什么》讲述了一个好故事,给人向善向上的力量,但在结尾不免落入俗套。林仁清的《实习课》看的令人瞠目结舌,小说简短,却耐人寻味,直面现实,发人深思。2013年第5期的《北方文学》(上)发表的几篇小说很值得一读,小米的《不知道是谁在唱歌》讲述了神秘感极强的故事,通俗化的语言道出了淳朴乡村爱恋的朦胧美。王子的《虎年明信片》,欲扬先抑,一张明信片暗含的世态人情的冷与暖,用薄薄的一张明信片检验出人间真情。余显斌的《走过城市的红尘》令人,心痛,金钱的魔力,情感的被摧毁,谁来恪守那份真挚,一切都是未知。2013年第7期的《延河》刊登的小说《春夏秋冬》是一篇颇有哲理意味的小说,作者宁可将自然现象和人联系在一起,借自然现象影射现实社会,刻画冷漠的人情世态,喻·义深刻。选自2013年第7期《山东文学》的《瑞土军刀》,作者刘宁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疯狂爱情故事,但其中又不乏一些宿命的东西。艾丝丝的《水边的阿狄丽娜》直面当下最现实的问题,紧贴生活,但其艺术性又高于生活,重拾人们对真情的向往。郑小驴的《最后一个道士》故事虽然有点俗套,但终究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诟病,我们所缺失的、匮乏的,那就是对信仰的坚守。
2013年第7期的《黄河文学》发表的庞善强的《蚂蚁葬礼》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小说,浓重的魔幻主义风格,小说在娓娓叙述中把现实问题一一点名,不突兀、不生硬,通过人与动物的对话语言,趣味性强,又有令人深思的一面,的的确确的是一篇好小说。梁弓的《相聚》则告诫人们当责任与逝去的情感发生冲突时,当下的责任撼是最重要的。第6期的小二的《阿桃的心事》是写出了青年一代面临情感、工作选择的重要性,小说结局的发呆神态依旧在暗示没有出路。2013年第5期的《时代文学》刊登的三篇小说都是对淳朴农村人们的刻画与书写,刘照如的《刘兰的婚事》语言朴素却动人,对人性真善美的颂扬感人至深。徐岩的《消失的鸽群》刻画的农村进城人遭遇的生存尴尬,同样值得关注。聂鑫森的《苞谷飘香夜》既有对仁厚土地的歌颂,,又有纯真感情的怀念,情思兼备,温情中不乏对人生的反思。2013年第6期的《飞天》刊登的刘宏伟的中篇小说《全剩时代》向人们诠释了当今社会都市情感的虚无缥缈,缺失的真情把人们变得麻木冷漠,不再会“爱”了。但是叶子的短篇小说《螟蛉子》以曲折悲惨的故事情节,沉重地揭示了人的感情的不可逆转性,被抛弃的三娃最终与父亲形同阳路,泼出去的亲情覆水难收,徒留一地的叹惜。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