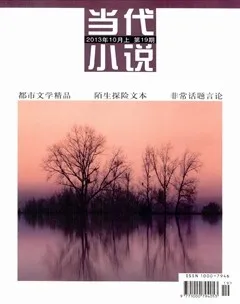调音师的依米酱奈
人一生中起码有几个难忘的独处的时间。在彼时你或许漫步在灌木丛生的荒野,或在沙滩上无所事事地画着圆圈,在桥上,在树下,在高楼之顶,在某个密闭的屋子里,或许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餐厅,靠着窗前,周围人来人往,头顶上还放着喧嘈的音乐——那绝不是普罗科菲耶夫式狂野的高雅,也不是Nirvana乐队式反叛的吼叫,总之就是平俗透顶,看似无关痛痒、像什么慢慢、轻轻地啮咬着你的耳膜。环境只是辅助性地让你进入独处的状态。进入状态后你会暂时忘却眼前的一切,同时让自己内心深藏着的情景,事物,场面慢慢浮现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一段长长的建在堤坝上面的跑道。不知为何那种画面感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白色的路面、两侧低矮的护栏;植在护坡上绿油油的草皮、阳光下汗水透亮泛着酡红的肌肤……像一大群梭鱼似的迅速涌入脑海。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之前它们竟从来不曾在我的记忆中探出头来,连一点点也没有。我甚至以为它们从未具体存在过。那也许是某部电影里的镜头,我想。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与大江共进晚餐的时候,我提起这件事情,他才替我反应过来:
“那不是我们读中学时候学校后面的那条跑道么!”
“是哦!我怎么会把这个给忘了!”
我们瞧着彼此的眼睛微笑。我和大江是初中同班同学,直至九年级第一学期他转学为止,我们俩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不是那种形影不离的表现形式,不会说上个厕所都要陪着,但从精神层面上看绝对算得上是知交。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的兴趣爱好,唯一截然不同的就是跑步。我那时不爱运动,尤其是那种乏味耗时又费力的运动方式。大江则是体育健将,是连续两届校运会长跑项目的冠军。他那时候的小腿又细又长——尽管他现在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跑起来跟两根筷子似的,不过论耐久力当真无人能比。每天傍晚放学后大江都会去跑上半个小时,大多数情况都去堤道上面跑,有时候会拉我一块去。尽管不情愿,但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堤道四周的风景其实相当不错,在上面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水域,湿地上的白色鹭群,绚丽的云霞,还有一条横跨东西的新干道。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的同校生两三成群地在上面活动,当然还有附近的居民,偶尔还会碰见一只皮色干净的贵宾犬。其中一段废弃的堤道靠水库的一侧,是一片广阔的防护林区,林地下方的沙子十分洁净,那里是适宜情侣幽会的地点。每次我和大江经过,都会忍不住朝那里望上几眼,虽然几乎看不到什么,但对我们俩旺盛的好奇心都是极大的满足。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女朋友,对成熟或趋于成熟的异性身体仅仅处于纯粹的幻想时期。当时学校实行口头上的“禁欲主义”,不过仍有不少的学生跑到那里去偷食禁果。若挑个好时间走进林子里,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弃用的避孕套及其包装纸,有的甚至还挂在了树枝上。清洁工会不定时地清理掉它们,快则一天,慢则一周。那家伙究竟长什么样儿我都几乎忘掉了,不过焚火的场景倒是记得很清楚。我跟大江也曾私底下焚烧那些垃圾来着,总觉得很好奇,也不嫌脏。清洁工每次将林子里的避孕套清除后,会把它们堆在靠近堤道的地方烧掉。只要我们跑到林子附近就闻到了,多余的荷尔蒙夹杂着天然橡胶一起烧焦的味道,同产生的浓烟像草蛇一般嚣张地向天际扩散。
我是去年年底才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重庆,过完年后大江一个电话打过来,我才知道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接着就是约会、聚餐,几次过后我们似乎终于填平了时间所造成的沟壑,像当初那样无话不谈,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东西终究是回不来了。从交谈中我了解到大江未婚,独住,有一个调音师的工作。“是那种去别人家里,调调钢琴什么的吗?”我问。
“不是,”他马上笑了,“你是由那部叫《调音师》的电影联想到的吧?哪有那么浪漫!不过就是在舞厅啊酒吧啊里面弄弄音响的小角色罢了。”
“每天都上班吗?”
“只有有演出的时候才去。一般都是夜晚,到那时候晚饭只有留到深夜才有空吃,忙得要死,特别是碰到还要彩排的情况。”
“听起来很苦逼的样子啊。”
“可不是么。”他用筷子从餐盘里夹起了一只蟹脚,放进嘴里咬得咯吱咯吱地响。银蟹冷盘是每次我们聚餐时他必点的菜式,我则比较随意,哪怕是碟糟糕的意式面条也能填饱肚子。他对饮食方面颇有一番研究,这点不难看出。“男人得对自己的舌头照顾点,”他说,“你这么随便可不行。二三十岁的年纪,风姿英发,吃得好点,又不会有啤酒肚之类的后顾之忧,何乐不为!我跟你说,江北区内大大小小的餐馆我也吃过不少,但要论真正做工精致,味美料佳的,没有几家。与此相比,老板们更愿意把心思花在环境和服务质量上。”
“有道理。我来这里还没在外面吃过几次呢。都是在单位的食堂吃,嘴巴都快腻出盐来了。”
“改天去我家坐坐,”他说,“我亲自给你下厨好了。反正我白天也是闲着。”
“那怎么好意思呢?”
“别跟我客气,要知道我可是很少主动下厨的哟。我这人也懒,虽然自己会弄,但嫌麻烦,所以不常在家里吃。”
“以前可没听说过你还会厨艺,”我说,“深藏不露哈。”
“后来才学的,”他说,“读书那会哪会这种东西,那时候还只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呢。做饭烧菜什么的,都是跟前女友分手了之后才自学的。”
“前女友?”
“准确地说应该是前未婚妻了,”他说,“婚期都订了,戒指也买了,就差一步,但最终还是吹了。”
“到底怎么了?”
“说来话长。”大江啜了一口啤酒。
进入初三第一学期后不久大江便突然转学了,据说是由于家庭破裂的原因。两周后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寄信人地址竟是外省的某所私立中学。他在信中提到自己转学的缘由,但含义模糊,一笔带过,毫无感情色彩可言。此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跟他保持着通信,可是不能准确地记得是什么时候,这种联系最后也断了。我不记得我们俩是谁最后没给对方回信,问题或者出在他,或者在我,或者在当时那股无形的升学压力身上。无论如何,少了大江这个朋友对我来说,没有产生那么一点点寂寞感的话绝对是谎言。那时候我貌不惊人,成绩差,又没有什么其他特长,是属于那种后天努力无法挽回先天缺失的类型。家人对我早就失去了信心,至少不是最后一名就好了,他们这样跟我说。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事情,就像藏在魔术帽底下,一切皆有可能性。
失去挚友的我仍然保持着一周一次到堤道上跑步的习惯。这一点连我也感到惊讶。我根本不可能喜欢上这项运动本身(直至现在依然如此),又失去了同伴,按理来说早该就此摆脱了才对。但我依旧每周五下午五点半准时在堤道上出现,原因恐怕只有一个——为了碰见那个名字叫橘的女孩。
橘是跟我同级不同班的女生。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初二的上半年,堤道上面,傍晚时分。跑在前面的她上身穿着一件浅色的汗衫,下身是校服的运动裤,头发不长不短刚过肩膀,皮肤在夕阳下显现出一种奇异的白——跟一般女生那种纤瘦的苍白不同,她的白首先体现出了具体的质感,像鱼白,像粉绒,像蒲团,其次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朝气蓬勃、青春洋溢的美。怎么会有人拥有如此完美的皮肤!我在心里暗暗感叹道。大江跑在我旁边,也瞧得眼睛发直,但他并非第一次瞧见。因为接下来我们从她身旁跑过的时候,我看到他朝她打了一声招呼。她微笑着予以回应。她的脸部虽然没有她的皮肤那么无懈可击,比如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什么的,但给人感觉十分耐看,一丝不协调感也没有。她的笑容亦是。自认识她开始,在我印象里她就没有过多复杂夸张的表情,每次大江跟她打招呼,挂在她唇边的毫无例外是一抹淡淡的、神秘的微笑。她的名字是我不久后从年级组长的口中得知的。半年一次的年级大会上,组长从手中的奖励名单中念出了她的名字,接着她走上台来,接过红色的奖状。我当时坐在前排,看得一清二楚。我从未想过她会是如此优秀(为何在跑步遇到之前毫无印象?),那一刻心情既诧异又沮丧。她跟我不是一类人,我这样想,并且强迫自己打消要接近她的念头。每次跑步相遇,同她打招呼的向来都是大江而非我,不过奇怪的是,除此之外两人也再无过多接触,连一句例外的问候都没有。大江似乎跟她也没什么交情,我看在眼里,心想莫非大江有着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从不在大江面前提到她,大江也是。我感觉我们之间存在这样的一种默契——尽量与她保持距离。因此不管是在堤道上还是校园里,碰到橘都会让我们之间(至少我是这样觉得)感到有些尴尬。
橘跟我一样每周跑一次步,而且只在星期五放学后,这点是我后来观察并实验得出的结论。所谓“实验”,就是随便找个借口跟着大江每天都去跑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累得精疲力尽。结果前四天她都没来,只有星期五那天她的身影才在跑道上出现。我们像往常一样从她身旁跑过,然后大江向她打招呼,她回应,接着各跑各的。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天我多跑了两圈,也感觉不到什么疲惫。
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足够的神秘感,比如她的皮肤,笑容,爱好,交际等等。她似乎不是那种喜欢黏着朋友的女生,不管是去哪也好,都是独来独往。只有一次跑步时带上了个同伴,是一个小个子的女生,长相很可爱。两人跑了两三圈后就靠在围栏后面的树下休息,我们经过时能听到她们大声地说笑,似乎在谈论着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还看到橘趴在小个子女生背上,看不见表情,天鹅般的后颈笑得一抽一抽的。直到天黑下来我们决定回去的时候,她们还坐在那里。她们还不打算回去吗?我边走边想,她们在想些什么?我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我跟大江分别后又偷偷返回,借着夜幕的掩护躲在暗处观察她们。她们这时候不再说笑,只是静静地依偎在一起,像是睡着了一般,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大概过了十分钟,当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时,她们突然活动了,手牵着手站了起来,绕过围栏走到堤道上。她们开始沿着堤道不紧不慢地走下去。我悄悄地跟在后面,与她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一会儿后便到了那段废堤,左侧便是那片种满了木麻黄的防护林。我看到橘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然后听到她突然在里面大喊了一声;有人吗!这仿佛是恶作剧的一个举动把我也吓了一跳。
林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怎样?有人吗?”小个子女生问。
“一个也没有。”橘回答。
她们两人的声音虽不大,但听得清清楚楚。接着她们钻进林子,我也跟着进去。她们的脚步声踩在干净的偶有枯枝的沙子上面,发出细微而干脆的声响。我不敢靠得太近,只能放慢脚步以免被察觉。她们似乎在寻找着某个地点,且由于林子里光线实在不佳(虽然没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她们走得也不快。终于她们在一处较为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随后蹲在地上,用手指在地上扒拉着沙土。她们像是挖出了一个塑料袋的物体,接着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倒了出来。“都齐了。”橘说。小个子女生点点头,把一根根像是小管子的东西插在沙地上。那是什么?我蹲在一棵树后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们。橘用手中的打火机燃起了一撮明亮的火苗,将她们周围的一切照得透亮——原来地上那些“管子”竟是蜡烛。只见她将地上的蜡烛依次点亮,我大略数了数,少说也有十多根。布置完后两人相视而笑,烛光打在她们脸上,像是裹上了一层松脂。
“寿星公生日快乐哈!”
“谢谢!”小个子女生笑着回应。
她们相互开了一会玩笑,然后开始唱生日歌。虽然是很简单的旋律,但她们唱得十分认真。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橘唱歌,她的声音娴静动听,透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吸引力。完后她们又一块儿唱了几首流行歌,我记得其中有一首是王菲的《红豆》。四周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灰林 的嘟叫,仿佛是一张乐谱里跳跃的小倚音。这是我从未见识过的橘的另外一面,活泼、热情又有点女孩子气。跟以往的印象相比,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最纯粹的她,但那时候她给我的感受确是无比真实的。我听得渐渐入了神,以至于连被夜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头发都觉察不到。似乎过了好久好久,一阵幽幽的啜泣声才把我惊觉。我转回去一看,地上的蜡烛已经不知何时扑灭了,一大一小两道人影依偎在一起。较小的人影似乎在哭泣,较大的人影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她。然后两人开始相互抚摸对方的身体。
周末我应邀到大江家做客。因为是之前通过电话商量好了时间,所以他招待得很充分。大江住的是租来的公寓套房,两房一厅,虽然很小,但一个人住,也勉强过得去。客厅内布置得简洁而整齐。黑胶木柜上面摆着一台大概只有二十一寸的二手电视,两旁是插着塑料花的环形花瓶,花瓣上一尘不染。DVD机摆在另一侧,同样是旧货,可以看出顶壳与其他部分颜色上的不协调。架子上排列着许多唱片,绝大多数是古典音乐的巴赫、勃拉姆斯之流。
我到他家那会,他已经差不多弄好了饭菜。等他把最后一只瓷罐加热后端上来,我们便坐下来开始动筷。不得不说,大江的手艺果然非比寻常,尽管餐桌上的大部分菜式我都准确地叫不出名字,但只要尝上一口,必定会印象深刻。我边吃边向大江询问菜名、材料以及做法。
“这是京都排骨,”大江指着一盘色泽明亮的肉块说,“老北京的名菜了。做法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尝试着做做。超市里有袋装的肋排,买来后放在冷水里浸一浸,洗干净后切成小块,然后加入一些调料,像生抽、蚝油、料酒之类,最好有点胡椒粉或者咖哩粉。腌制程序是最费时的一道,你得保证味道都进去了,均匀了,再打上一层淀粉,放入油锅里炸上一诈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还是很复杂的样子啊。”我说。
“这种事得慢慢来,”他说,“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学这个,特地买了几本菜谱,第一次弄了半天才弄出一小碟。后来熟悉了,就知道怎样能够最省时最简单地烧出最好吃的菜。”
“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尝过你的手艺的吧?”
“有啊。一般是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哥们谁谁生日了,就凑我家里来。他们负责买食材,我负责厨活,整出一大桌来。吃饱喝足后大家会很自觉地帮忙收拾餐具,垃圾分成几份装进胶袋里,每人带走一份。”
“很有意思啁,”我说,“都是同事吗?”
“不尽然。有的是同行,有的是在舞厅的酒会上认识的,玩了几次就熟了。干我这行的,会碰到各种各类的人。当然,也会有不少的艳遇哟。”
“怎么说?”
“但凡在那种场合出现的年轻女性,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或者不满足的类型。她们到那种地方,不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外表上好好打扮一番以吸引男人的眼球那是不可能的——但你仍然可以从言谈举止中分辨出哪些是有知识有教养的,哪些是没有的,哪些是假装有的。对她们来说,即使不一定能够招来奇遇,单单坐在那里,享受着他人对你目前的外观状态的注目,也足以弥补现实中失去的自信心什么的.最可靠的一点反而是陌生感,在那里谁也不认识谁,喝酒也好,跳舞也好,接吻也好,上床也好,疯狂一刻,然后各奔东西。”
他边说边用勺子将面前的瓷罐里的东西盛入碗中。那是类似米糊的东西,白中带黄,其中似乎还有其他佐料。自一开始我就对那只显目的瓷罐感到好奇,等他一说完我便指着他碗里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嗅,”他眉毛动了动,“依米酱奈’——我给它起的名字,是日语‘意味がぢぃ’的谐音,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
“怎么会起个这样的名字?”
“之前跟你说过的吧,”他说,“我是跟前未婚妻分手后才开始学习厨艺的,第一个学会的就是这个,不知怎么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名字。当时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
“看来那件事对你打击确实挺大的啊。”我说。
大江上次大致跟我讲了一下他跟他未婚妻的事情。两人是两年前在酒吧里认识的,当时她刚分了男友,心情很低落。大江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她从沮丧的心境中恢复过来,并且接受自己。她人长得漂亮,有份不错的工作,能烧一手好菜,对大江百依百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上佳的配偶。双方的父母都见过面了,商定在去年年内举行婚礼,两人还制定了蜜月旅行的计划。一切看起来都朝着美满结局的方向发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婚期的前两周,她突然向大江提出分手。
“我当时惊呆了,”大江说,“直到我要求她重复一遍才确认她想表达的意思。我问她为什么。开始她不做声,过了一会抽泣起来,然后才说是她那位前男友回来找她,说了很多忏悔的话,他说他是一时糊涂才看上了别的女人,现在请求她的原谅并且要求复合。她发现自己很难拒绝他的要求,因为自己还深爱着他。那男的态度很诚恳,说只要她回到他身边就立马娶她。她啰啰嗦嗦说了许多,我当时犹如五雷轰顶,大脑一片混乱。我说难道你就没有爱过我一点么?她流着眼泪说两种爱的性质不同,那男的跟她还是读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感情一直维系了好多年。她是个恋旧的人,很看重这份感情,不想失去。我对她声嘶力竭地大吼,那你就忍心这样对我!我情绪激动地将床头的茶杯摔碎在地板上。她肩膀缩了缩,哽咽着说,你不也一直这样,对自己的初恋念念不忘?我说我哪有?她说那封信,那封夹在《圣经》里的信她看过了。她一提到这个像是戳中了我的软肋,我一下子说不上话来了。”
“什么信?”我问。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跑步时总遇到的那位身材高挑,留着齐肩头发,皮肤很白的女生么?”
我当然记得。但是我还是装作思考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那时候她是我的暗恋对象,”大江说,“转学前我给她写了封表白信,但没成功。她还是很有礼貌地给我回了信,信里拒绝得很委婉。之后我就一直保存着那封回信,没想到给那位前未婚妻发现了。她当时就问我,这就是你多年来一直没有女朋友的原因吧?我是不是长得很像她?在你看来我是不是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一连串的问题,虽然只是出自她的猜测,但个个击中要害。我无话可说。”
“她问的是真的吗?”
“虽然没有那么绝对……可起码从一开始,我就是因为觉得她长得酷似那位自己暗恋过的女生,才想着去追求她的。她这么一说,使我对她产生了愧疚感,我就没有否认。”
“接下来呢?”
“还能做什么?”大江黯然摇头,“话已至此,再接下去恐怕她就要跪下来求我了。所以好说好散,第二天我们就去解除了婚约。父母们虽然对此感到很生气,可也没办法。”
以上就是大江跟我讲述过的内容。如今在他家又触及了这个话题,我就问他能否借那封信让我看看。他很慷慨地答应了,起身到卧室里取来那封信然后递给我。信封是那个时候流行的款式,上面用清雅娟秀的字体写着收信人的地址。这是橘的字。我打开信封,取出信纸,只见上面用淡蓝色的笔迹写着:
江同学:
见信好!你的心意我收到了,十分感谢你的真诚。但是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份珍贵的感情。请原谅我的选择,如果不介意,我希望能与你继续保持友谊。
林橘
回信十分简短,下面是写信的日期,一个跟现在相差了十三年的日期。如今我手里拿着的是一封来自十三年前的信,我提醒着自己,闭上眼睛,感觉有东西在黑暗里滚动。
看完信后大江让我尝了尝“依米酱奈”的味道。口感很独特,甫一入口很滑溜也很香甜,但吃多了就感到酸涩。我向他询问做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他笑着说,“就是薏米牛奶,牛奶放少一点,加上大米,土豆泥和梅干。后面那些是我自己琢磨着加进去的,结果一试,还有那么点意思。刚开始是怀着自暴自弃的心态做成的,没想到吃着吃着就上瘾了。现在每天都少不了要吃一罐。”
大江是个坦率的家伙,这点跟我就大不相同。从他说刚才那番话起我就在思索着那股酸涩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根肉刺长在了不合适的地方。终于我想明白了,是那封信上的某些字句的缘故。我很想告诉大江那所谓的“某些特殊的原因”是什么,想告诉他那天晚上月黑风高的林子里,我如何被夜里冰冷的露水浸湿了头发,受了寒而回去后大病一场的事情,想告诉他灰林 的嘟嘟叫、蟋蟀的细鸣、夜风的吟唱汇合而成的音响是多么地动听,但是我的喉咙被“依米酱奈”堵得满满的,连发声都感到十分困难。因此即使到最后,我和大江你一勺我一勺地将瓷罐吃得见了底,我还是没能将想要说的话说出来。
作者简介:索耳,本名何星辉,1992年10月生,广东湛江人,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此三篇小说系作者首次发表作品。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