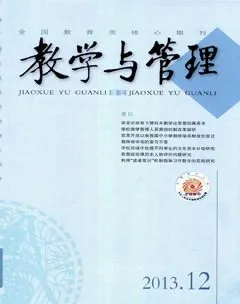英语活用型词汇的认知策略研究
英语学习者水平的高低可以从理解技能和表达技能两个层面加以测评:理解技能即我们常说的听和读的能力;表达技能分为说和写两项技能。其中,写作更能客观反映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近三十年来,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与原有的哑巴英语相比,学生的表达技能有了明显进步。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学生在实际英语表达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以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的写作为例,学生仍然存在很多表达不清或大量中式英语[1]。就这一现象,不少语言专家及二语习得研究者指出,学生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中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表达词汇造成的。“英语表达词汇水平对英语写作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们在英语写作过程中,常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词表达自己的思想,放弃了很多有一定内容和深度的想法,转而去写他们认为可以用英语表达的简单思想”[2]。常见的外语教学以结构主义语言观为指导思想,课堂教学一直以词汇和语法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那么,为什么学生一直以词汇学习为重,却在表达技能中仍然受制于词汇这一要素呢?可见,要想培养学生真正具备词汇运用能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一、词汇认知层次划分
Verhallen提出“语言学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习得足够多的词汇进行表达”[3]。词汇可分为认知型词汇和活用型词汇。认知型词汇(也称为消极词汇)“是指认识但尚不能自由运用的词汇,一般只知其最基本、最核心的意义”[4]。活用型词汇(也称为积极词汇)是指语言学习者可以随时根据表达思想的需要而自如运用的词汇。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表达能力,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必须要更注重培养学习者对词汇的运用能力,通过具体的词汇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有效地将已知词汇从理解层面的应接型消极词汇转化为表达层面的活用型积极词汇。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学习的过程也是心理认知活动的过程。这一认知过程可以分为信息的输入、处理和输出三个阶段。首先,在信息的输入阶段,学习者必须收集并吸收适量的认知信息知识;其次,在信息处理阶段,学习者需要运用各种具体方式对输入的认知信息处理和加工;最后,在信息输出阶段,学习者在输入和加工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不同情境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思想。著名教育学家Bloom从认知视角将学习概括为六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5]。识记和理解停留在较为简单的认知层面,视为学习的输入阶段,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认知阶段,视为学习的加工和输出阶段。显然,在英语词汇学习中,记忆和理解的认知阶段有利于词汇的初步掌握,但距离词汇活用这一目标还相距甚远,表达技能中所要求的积极词汇需要学习者在记忆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经过应用、分析等较为复杂的认知层次才能最终实现。
二、活用型词汇认知策略
围绕较高层次的认知需求,英语课堂教学需要帮助学生从记忆和理解的认知阶段顺利跨入应用分析层次。传统的以句法分析及词汇单独讲解的英语课堂教学以学生的理解能力作为教学过程的主要目标,虽然学生能够分析、理解词汇意义及句法结构,但对语言词汇的学习多停留在理解记忆这一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词汇活用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此相比,任务驱动型教学以语言使用为导向,围绕任务进行课堂组织和教学,学生需要按照要求运用语言知识完成多种不同任务,例如描述图片中的场景、表达关于某一现象/场景的看法等。词汇认知中的分析和应用层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更好的展开。本节围绕认知活动的三个阶段以任务驱动型教学的相关环节为背景,逐一讨论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词汇认知策略。
1.输入阶段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学习的认知过程可以分为输入、加工和处理、输出三个阶段,其中输入部分最为基础,是认知过程的初级阶段,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和浅层理解阶段。在任务驱动型教学中,表现在词汇学习方面的输入环节包括教师在布置任务时对内容的选择,为学生讲解分析词汇的具体策略,以及如何唤醒学生心理词汇库中与内容相关的已有词汇。
(1)任务的选择:同一英语课堂的学生词汇掌握程度参差不齐,而教师在面对既有教学任务、无法灵活选择教学素材时,该如何有效兼顾各个层次水平的学生,使其最大可能的吸收理解场景词汇?输入作为词汇认知的初始阶段扮演着极其重要的铺垫性角色。这一层面包括课堂任务的选择、对学生已知词汇的唤起、帮助学生感知并注意相关词汇。在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6]的指导下,教师在导入课堂任务时需要预先将学生已有词汇水平考虑在内,如果所选内容过于容易,那么学生会认为学习没有挑战性,没有新鲜知识可学,对于只是“炒冷饭”的课堂教学,学生会缺乏学习的兴趣。同样,如果教师所安排的内容难度远远超出学生现有水平,即使通过努力也很难完成任务,这样势必会打击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产生厌学情绪。
(2)心理词汇的激活:为了达到教学目标,确保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教师通常需要根据教材内容的相关主题安排热身过程(warm-up activities),这个过程通常为口语或书面语表达,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发掘与此任务相关的词汇,即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的相关信息,为开展核心教学任务做好铺垫。例如,以“buying clothes in a store(商场购买衣服)”场景作为表达任务,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小组配对(pair work)形式讨论,课堂中每个学生都是参与的主体,都可以或多或少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当前场景的服装种类而言,学生能够在讨论中提取心理词库中的表达词汇,比如:T-shirt,blouse,cardigan,pajamas,evening dresses,pants,jeans,casual clothes等。通过参与任务场景讨论,学生已有心理词汇得以激活和扩展,这样既能增强他们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导入。在此基础上,小组成员可以将讨论成果融入任务场景,分析场景中可能的命题以及相关备用词汇并加以概括和分类。同时,学生还可以根据生活经验结合语言知识推理出顾客(customer)、商场服务员(shop assistant)、服装种类(type)、尺寸(size)、颜色(color)、材质(material)以及价格(price)等词汇。显然,基于任务场景的预热活动能帮助学生激活其心理词库提取积极词汇,而丰富的小组活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其积极词汇,从而有效完成唤醒和感知等输入过程。
(3)焦点词汇的引入:作为课堂任务的发布者和监控者,教师首先要尽可能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并唤醒其心理词库中的积极词汇。而在任务讲解过程中,不仅要对新出现的焦点词汇进行基本释义和模仿造句,更应注重培养学生新旧知识的对接能力。知识对接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加工和处理已输入信息,整理并扩大其心理词库,达到灵活表达的语言输出目的至关重要。在新旧词汇的对接过程中,以形态学及语义学理论为指导,以词汇构词与语义关联为线索,能有效培养学生扩大语义场、增强词汇辨识的能力。
2.加工整理阶段
在完成信息输入的基础上,学生还需运用具体方式对相关词汇进行分析、加工和处理,为语言输出做好准备。信息加工处理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方向的引导者,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形态学及语义学知识来扩展心理词库,辨识词汇间的语义关系。
(1)词根词缀:词根词缀知识的积累与应用在新旧词汇的对接认知中必不可少,例如,在“megabus,megadose,megacity”当中,如果学生熟悉“mega-”这一前缀的基本语义,不仅可在篇章阅读时推测整个词的意义,而且可以在口语交际过程中将词根词缀的知识作为推测会话内容的线索依据。显然,在新词学习的过程中,词根词缀不仅有助于对特定词汇的理解,还有助于任务表达时的选词和造词。
(2)词义关系:英语词汇可以分为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一词多义、同音异义和形近词等多种关系。在词汇学习过程中,将已知词汇与新词通过以上词义关系进行对比辨识,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记忆,更有助于学生在任务表达(即语言输出)时的词汇甄选。例如:“buy”和“purchase”作为同义词,虽然基本含义相同,但是在使用场合及搭配词上存在显著差异,“purchase”作为新词讲授时,不能仅仅用“buy”做为释义词,更要区别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使学生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对于形近词的区分,如“price/prize、imaginative/imaginary、respective/respectable”等,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词与词在意义上的差异,更为学生在语言表达时扩大选词范围奠定了基础。再如,在上下义关系结构中,上义词包含内容更广,可使用的场合也更普遍,但其区分度却较差;相对而言,下义词所指更为具体,使用范围也更确定。以“flower”为例,其下义词包括“rose,jasmine,chrysanthemum,tulip,violet,carnation”等。频繁使用上义词不仅使表达显得枯涩,也无法凸显所表达内容的典型特征。相反,变换使用上、下义词不仅能使表达内容更清晰,而且能让表达方式多样化。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此作为认知信息中词汇输入的教学策略,培养学生运用联系的观点衔接新旧词汇和分析词汇关联性的能力,从而提高其口头或书面语表达时词汇运用的准确度,扩展其活用词汇量。
(3)语境分析:除上述解词策略外,如要将词汇更完整地转化为积极活用词汇,还须分析词汇的使用方式及语言环境等因素。语言环境不能仅局限于词汇的搭配及上下文,还要融入文化背景以及认知方式等较高范畴。以tough-minded/ruthless为例,虽然两词属于同义范畴,但使用语境却有本质不同,如果谈话人意图表达褒义赞扬的态度,那么“tough-minded”很显然更符合其需求,而“ruthless”的贬义色彩更适合批判式的语言环境。从文化角度来看,如果学习者在表达过程中忽略母语与外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即使合乎语法的表达方式仍然可能带来交际失误,以“hello”一词为例,在汉语中常常被译为“你好”,但事实上在特定的语境中,“hello”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隐含意。假设场景为夜晚美国某一城市的街头,如果一位女士以“hello”和陌生人打招呼,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街头女郎,事实上,在英美文化中,在公共场合寻求帮助或引起注意时应使用“excuse me”而非将中文中的“你好”直译为“hello”。由此可见,在词汇的加工和处理过程中,只有明确词汇使用语境,才能在输出阶段准确无误的表达其思想。
3.输出阶段
信息的输入和加工过程为表达(即语言输出)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不同情境的需要恰当地表达思想。根据教育目标分类,输出阶段包含了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较高层次的学习目标。在任务驱动型英语课堂教学中,通常以课后口语和写作练习作为对学生语言输出能力的测评。完成某一表达任务时,需要兼顾众多语言内部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环境。
(1)母语迁移:正确的输出要求学习者根据自己要表达的信息进行语言组织。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他们所积累的知识,而是一个加工和建构的过程[7]。母语对二语习得的负迁移一直以来都是外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外语学习者构建的英语表达介乎于母语与英语本族语之间,学生在表达过程中往往会进行字面翻译而产出中式英语(Chinglish)。比如,英语常用“law and order”表达“社会稳定”,中国学生则可能会用“social stability”;在表达“接触社会”这一思想时,我们常常会见到“touch the society”这样的表达方式。显然,在词汇的输出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只考虑到了“touch”一词的“触摸”之意,简单地将“touch”与“接触”对等起来,却忽略了各自的不同内涵。由此看来,学生在语言输出的过程中要避免字面直译,将词语的选择与具体语境割裂开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因为语义扭曲、文不对题而导致表达错误、交际失败。
(2)英汉对比:从词义的层面看,英汉两种语言有时是对应的,有时则会出现空缺;有时表面对应,实际却大相径庭(潘文国,2010)。人类在认知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必定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在外语表达输出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对应的、共同的成分是较为容易把握的,甚至可以简单的使用直译法。然而,英汉两种文化在思想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造就了两种语言中的独特词汇,为外语表达输出带来一定困难。以中国传统服装“旗袍”为例,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类似服饰,在这样的词汇空缺状态下,交际者要想让读者/听者较为准确的理解这一词语的含义,不能简单的音译为“Chi-pao”,还需考虑添加适当的注释。对于貌似对应实则大不相同的词来说,外语学习者尤其需要注意其中的陷阱。比如:汉语中“宣传”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中性词,但与其貌似对称的“propaganda”在英语文化中却有蛊惑人心的含义,是典型的贬义词。综上所述,在输出英语表达时,有意识的进行英汉词义的对比有助于概念的定位和表述。
(3)视角转换:视角是指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选择的位置和角度,视角取决于交际者的文化知识、社会阅历、地位层次以及说话时的心理状况等各种因素。在交际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要尽量的站在对方的文化生活背景考量其对待语言表达的态度及心理,比如,当听话人是一位黑人女性时,说话人在谈论和种族有关的话题时就要在词汇的选择上格外考虑听话人的社会背景及其本人对待这一话题的态度。尤其在口语交际中,作为外语使用者,我们不仅要尽可能了解听话人的背景信息,也要通过信息反馈、语气语调等线索及时调整交际策略,其中就包括词汇的选择,比如委婉语的选用、释义的添加等等。
(4)自我监控:如前所述,在学习活动的较高认知水平中包括了自我评估的能力,对于中高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在语言表达时,尤其是书面语表达过程中,完全可以根据语言知识、文化背景、语篇衔接和语境预设等对已经构建的语言进行反复品读,从词语的用法、词义的辨识、文体的把握等各个角度来衡量词汇选择恰当与否。只有及时监控、评估并进行必要的修正才能确保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在自我监控的过程中,学生能够从中发现其在语言学习中的缺漏之处,促使其在以后的学习中有的放矢。
三、结语
词汇的知识系统非常复杂,“词汇的发展也不只是熟悉新词而已,它还包括深化已有词汇的知识,词汇知识的深度和词汇量有着同等重要性;习得词汇知识也不只是熟悉词形和标记,它还指熟悉各种意义、概念和已知词的概念意义关系”(戴曼纯,2003:143)。尤其在语言表达能力中,词汇的提取与选择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在英语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表达技能,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翻译或释义层面,只有将词汇放在更大的语言环境中,将词汇的搭配、词义关系、文化背景、心理视角等各层信息内化为词汇的综合信息,才能帮助学生在语言输出时提取更贴切、更丰富的表达方式。本文从词汇学习的三个层次,即输入、加工处理和输出,分析了在词汇习得中的具体认知策略及教师在词汇教学中的指导思想。事实上这些认知策略在实际运用中总是以相互交叉,互相依存的形式出现。而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宏观意识及认知视角更是教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参考文献
[1]陈伟平.增强学生词块意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外语界,2008(3).
[2] 马广惠,文秋芳.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
[3]Schoonen,R&Verhallen,M.The assessment of deep word knowledge in young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Language Testing,2008(2).
[4]戴曼纯.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2).
[5]Williams,M.& Burden,L.语言教师心理学初探.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Bloom,B.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HandbookI:The Cognitive Domain.New York:David McKay,1956.
[7]Krashen,S.D.The input hypothesis:Issues and implications.Longman London,1985.
[8]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潘文国.汉英语言对比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该文为2012年中北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认知视角下隐喻思维在英语习得中的应用与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