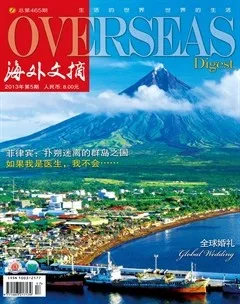永恒的高中


整个高中期间,我朋友健二从未和乔希·格拉斯曼说过话。乔希外表英俊,在校队打橄榄球,非常受同学欢迎(每所高中肯定都有这样的男生)。健二有一半日本血统,他沉迷音乐,多数时候独来独往,最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2012年秋季是我们高中毕业25周年,在酒吧举行的校友会结束后,健二一把抓住乔希·格拉斯曼的三头肌——还是像大力水手的那样粗——笑着问他接下来的派对在哪儿,乔希一下子愣住了。
从心理角度分析,成年后的健二有一本去任何地方的“护照”——外表英俊,谈吐优雅,在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担任软件工程师——这一切让他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自信,能即刻获得对方的尊重。健二抓住乔希时也许只是想开个玩笑,但一愣之后,乔希居然认真回答道派对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在另一个前校橄榄球队队员的家里。当二人肩并肩走进房间时,乔希大声宣布:“看我把谁带来了,当年的模范生!”整个高中时期,健二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派对。但健二说自己不在乎,这次跟乔希过来,纯粹是出于好奇,健二想象不出在中学里当橄榄球运动员或啦啦队队员,中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定居,工作结婚生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但在场的另外一位高中同学,拉里,却不认为健二真的像他表现的那样无所谓。像健二一样,拉里很聪明,在音乐方面有天赋,但高中那会儿他总戴着一副难看的眼镜。同样和健二一样,现在的拉里功成名就,他因为给电影《律政俏佳人》谱曲而获得托尼奖提名,他太太是他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他刚刚当上父亲。拉里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对派对的感觉:“真希望我能在高中时就被邀请,这里就是高中!人是不会变的,永远都想被周围的人接纳。”
记忆最深的青春
对多数成年人来说,高中时代在他们记忆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随机给一名成年人一些信号和暗示,他或她能够想起的事情很大部分来自高中。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名字——“回忆高峰”,它在大型人口样本中不断得到验证,那短短的3或4年感觉就像30年。
如果你对一个人如何成为现在的他感兴趣,你可以从他的高中时代找到答案。过去20年,围绕这一方向,社会科学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比如,对英美数千名白人男性所做的调查显示,男性的收入与他的身高有某种关系,但这一身高并不是他们成年后的高度,而是他们16岁时的身高。体重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后期体重正常,而不是超重或肥胖,他成年后的自信程度会更高。高中时的吸引力影响长远,高中时的优秀直接让一个人以后结婚的可能性更大、收入潜力更好、心理更健康。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青春期时,大脑比生命周期的任何其他时段充斥着更多的多巴胺活动,所以,青少年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更加强烈。“那种强度不会再回来”,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说,“青春期的喜怒哀乐都最极端。”
科学家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他们向三组实验对象(成年人,青少年,儿童)出示一种颜色,同时配上一阵可怕的噪音。结果,实验对象都潜意识地将二者联系起来,一看到那种颜色,人们出汗就更多。过了数日,实验对象再次被集中起来,科学家又把那种颜色展示给他们。结果成年人和儿童都没有什么反应,在这几日里,他们都学会了不再将两者关联起来,只有青少年还像上次那样反应强烈,好像威胁就在身边。
无法逃避的羞辱感
对于许多人来说,高中体验最多的是社交恐惧,或某种羞辱感。一个世纪以前,一旦人成长到十几岁,就开始做很多事情:农耕、管家、工作挣钱。在禁止童工之前,青少年在工厂、纺织厂和矿上做工,他们整日和成年人在一起,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慢慢成熟。而现在,十几岁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调查显示,如今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周交流只有16个小时,而和同伴交流却高达60个小时。当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成年人陪伴时,他们开始产生一种独立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孩子之间的等级关系和权力结构通常由那些最表面的东西决定:相貌、衣着、体育技艺……结果就是,许多人在高中时代都感到过羞辱。
这种羞辱感的影响非常深远。青少年大多选择以下三种策略对付这种痛苦:通过保密来掩盖它,通过讨好别人来逃避它,通过羞辱别人来对抗它。不管你选择哪种策略,当成年后遇到挫折时,你仍会用那种策略。
最不可思议的是,许多父母都表示,当他们知晓自己的孩子在中学里遭遇了某种羞辱(没占到好座位、未收到派对邀请、被别人爽约……)时,他们会受到再次伤害,当年的羞辱感又回来了,以至于很多家长难以对自己的孩子产生同情,不会对孩子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经历过”,而是训斥孩子“我告诉过你别把头梳成那样、别穿那件衣服……”
不光是被欺负的人多年来都带着羞辱感。去年《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米特·罗姆尼(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回忆了当初他们恶作剧的情节:按住一名流浪汉剪他的头发,冲一名内向的男孩喊“娘娘腔”,带一位视力不好的老师朝关闭的门走去……多年后,其中一名受害者表示仍然没有忘记当时的痛苦,但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这群捣蛋鬼们对于他们在1965年所做的坏事感到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在2012年公开表示悔恨。其中一位是退休的检察官托马斯·布福德,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时至今日,它仍困扰着我。”他带着那种羞耻感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迷失的年代
在高中时,我们总认为自己知道现实是什么:我们知道谁瞧不起我们,谁骑在我们头上,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但大量研究显示,青少年往往曲解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孩子在青春期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别人的性格,或读懂别人的行为。2005年,研究者在美国中学做过一项大规模调查,要求孩子们写下自己最好朋友的名字,结果发现,只有37%的友谊是互相的。这些统计表明,十几岁的孩子在自己被拒绝时体会不到,还在叫着:“伙计们,等等我!”或者在自己被别人接受时仍无知无觉,“那时候我以为你很讨厌我。”
犹他大学的黛博拉·托德教授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她让实验对象看一张人脸,辨认那张脸上的表情。结果成年人看后一致确定那个表情是恐惧,但青少年就不一样了,有人说是愤怒,有人说是疑惑,还有人说那是悲伤的表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但其结果总结了整个高中经历,高中生们把人们的恐惧误认为是别的东西了。
永恒的高中
高中是在我们在选择人生道路前最后一段共同的生活经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中的价值观和成年人的价值观没什么不同。例如在美国大多数公立高中,拉大提琴的女孩、参加仪仗队的男孩往往都不受欢迎,为什么聪明竟变成一个负担?可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成年人也不喜欢大提琴或仪仗队。人们对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大提琴家、小号演奏者,还有书呆子也许能在成年人的世界找到他们的位置,甚至是身份和自尊,但那只能在他们的圈子内。
如果你把一群成年人放入类似高中的环境——将他们空降至一栋大楼里,大家互不相识,且鲜有共同点——你会发现种种类似高中生的行为。好像真人秀一样,人们会分成部落,形成联盟,相互排挤。你会在很多成人世界里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养老院、书友会,甚至国会。
如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互联网让我们的声誉掌握在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手里,就像回到了高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公开、更加互相关联。突然遭受羞辱的可能性再次出现——现在是以有损形象的照片,或恶意传播的谣言出现。全世界成为一群互相打交道的中学生。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高中生活,那些年所有的孤立、羞辱历练了我们。但我们是否也该怪罪高中?在那几年最脆弱的年纪里,我们一次次陷入困境,被正确或不正确地塑造。
无论是为了辩护还是为了肯定,无论是出于自我惩罚还是自我安抚,很多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重温高中岁月。这是件疯狂的事情!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人在Facebook上朋友的最大比例——22%——来自高中,上过和没上过大学的美国人都一样。事实上,Facebook自身也发挥着作用。在有Facebook之前,人们和高中时代的自己是断档的。然后,马克·扎克伯格横空出世。于是,原来要休眠的高中记忆现在被激活了,而且永远保持畅通。
这也许是最终让我去年秋季去时代广场附近那家酒吧参加校友会的原因。在Facebook创立之前,很多高中同学我都快忘记了,但现在他们重复地出现在我的消息公告中。所以,我去了,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来的人中有豪迈的前橄榄球队队员,仍旧摆出好像拥有这家酒吧的做派,只不过更加慷慨。也有美女,她们依然美丽,但看上去少了些自信。如今的我们都正值盛年,大家因曾经有过的共同纽带再次相聚,此情此景令人感动。我在想,如果我们高中没在一起度过,而是成年后才结识,彼此的印象会不会更好。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没在一起上高中——如果我们高中时对彼此更仁慈些——那我也许根本不会在乎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