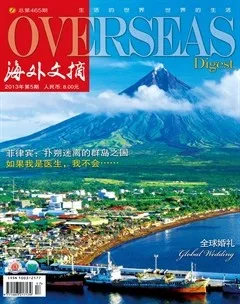我的女儿有自闭症


假如你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每天下班后去接他,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今晚我必须刷牙吗?”无论你怎么回答“是的,同昨晚一样”,接下来的20分钟到两个小时都可能在争吵、哭喊、发脾气或者歇斯底里的崩溃中度过。等他刷完牙,你俩已经精疲力竭并互相发誓这种情况不再发生。然而第二天,你去接他时,他问你的第一句话仍然是:“今晚我必须刷牙吗?”
我和我的女儿格蕾丝每晚就经历着这些,只不过她的问题是:“今晚我必须做作业吗?”格蕾丝的作业其实并不多,每周有四天晚上需要做半小时作业。我很高兴学校留作业,学习对她来说很重要。但是,每天督促她做作业简直让我发疯。这句话还不足以形容我的真实感受。有时候,即使上班时我很想她,心里仍然有着离家出走的想法。做作业这个过程本身比谈论它更让人痛苦。监督格蕾丝做作业时,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两岁的贝蒂可能正在旁边吵闹,而我同时要准备晚饭。
经历了五年时间等待检查结果、各种评估和重复性的问题测试,格蕾丝去年被正式确诊为亚斯伯格综合症。格蕾丝8岁,我39岁。格蕾丝的父亲和我为了找寻原因多次接受检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格蕾丝的与众不同可能是受到我们离婚的影响。我们慢慢适应她对狗、气球和手机的恐惧。原来亚斯伯格症患者对他们身处的环境非常敏感——普通的噪音对于格蕾丝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她不会辨人,不会对他人表现出好奇,不会参与谈话。
格蕾丝从小很独立,很倔强。她会花很长时间盯着周围的东西看,一动不动。她没有耐心排队等待荡秋千,会发出愤怒的吼声,直到轮到她时,才会平静下来。她的一些特别表现有时会给我一些警示,但是看到操场上同样面红耳赤的孩子和大喊大叫的家长,不好的念头就会被我打消掉。
在我写这些的时候,面前放着格蕾丝的档案。档案里是我保存的有关她所有的重要资料。有她小时候画的画,有一本她5岁时写的小说,名叫《莉莉和美人鱼》,已经装订好,做了注释。档案中的一份报告说,格蕾丝的语言能力属于正常水平的下游,她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概念、想法或解释问题。另一份报告指出,格蕾丝的注意力不易集中,不能得体恰当地社交,经常提出不相干的问题或者离题谈论自己的兴趣。
没有人能准确地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那些专家、医生们也不能。格蕾丝特异体质的根源究竟与她的年龄有关还是医生们的资源有限,我无法说清。那时,跑步是我唯一的发泄方式,能让我抛开焦虑。
我的家庭其实很幸福。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聊天。姐妹们给我热情的拥抱,经常逗我笑。我的第二任丈夫也看到了我的痛苦,他很喜欢格蕾丝,虽然刚认识格蕾丝的第一年里常要忍受她的踢打。我时常和爱我的这群人交谈,孤独感却依然挥之不去。
最终拿到诊断结果后,我忍不住跑回家蹲在淋浴器下大哭了一场。格蕾丝没有朋友,她经常为此而难过。虽然我知道格蕾丝如此地需要我,但我所有的感情心力都已消耗殆尽。格蕾丝的医生给了我一位女士的电话,她在组织一个当地的自闭症帮扶团体。格蕾丝对要见新朋友非常高兴,可当我们走进去时,我发觉我不愿待在这。走廊尽头的两个房间坐满了玩电脑的男孩子。格蕾丝把脸贴在玻璃上,充满渴求地望着我。我点点头,她走进去坐在一个空位子上,开始点鼠标。安顿好格蕾丝后,我来到围成一圈的母亲当中。
母亲们诉说着她们孩子的学校有多糟糕。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累,许多人不修边幅,表情凝重,照顾孩子显然让她们筋疲力尽。望着玻璃窗,我发现自己也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我比她们更加憔悴。我去看格蕾丝。她和男孩们在电脑机房里玩,他们在屏幕前坐成一排,玩射击游戏。格蕾丝坐在他们中间,显得灵巧、安静,看电脑时,她的表情非常严肃。回家的路上格蕾丝对我说:“太酷了,什么时候我们再去?”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她觉得哪里酷,我怀疑她是不想回家练钢琴。我问她:“你和别人说话了吗?”回答是,“没有”。当我们穿过漆黑的街道时,她告诉我,她很孤独。
那天晚上,格蕾丝的爸爸把她接去过夜。他们走后,我坐在沙发上回想着下午的事。我哭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我不想再带格蕾丝去那里。当我在沙发上哭泣时,电话响了。一个温柔的声音问我是不是索菲,然后做了自我介绍。电话来自全国自闭症儿童父母社会服务热线。我瘫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对方温柔地安慰我,直到我不再泣不成声,告诉她我刚过了怎样的一天。
格蕾丝开始接受帮助。面对着无止尽的会面、离开学校、医生的质问,她感到惊慌失措,我也感同身受。但是无论如何我得停止流泪。不久后的一天,学校打来电话,说我的女儿卷入了一场争斗。美术课后,孩子们身上都是木炭。格蕾丝突然被撞到,便用力推了一下撞她的孩子。那个孩子又推了她,两个孩子就这样打了起来。老师赶到的时候,两个孩子已打到地板上,其他孩子正围在他们身边起哄:“打!打!打!”
无论何时,我和自闭症患儿家长谈到格蕾丝的暴力倾向时,他们的建议都是:报警,找律师,如果可能的话找家庭教师,让她离开人群。但没有那么简单。我不能让格蕾丝在家上学,因为我不能不工作。我也不能让她离开学校,因为我们正在申请特殊教育,格蕾丝必须完成中学的学业,否则她就只能去当地的综合学校。
我在一家新闻机构做记者,最终老板同意我每周工作两天,这样我便可以参加各种与格蕾丝有关的见面会。我乘地铁到伦敦金融街上班,头发整洁,化着淡妆。如果忽视我的眼袋和手背上写的必做事项清单,我看上去还像个专业人士。星期五的早上,我和丈夫一起释放压力。我们尖叫或者使劲摔门,这时候,小女儿贝蒂就会看看我,看看爸爸,满脸惊恐。晚上我会洗个澡。此时,一周的担心和痛苦积聚到顶峰,时间仿佛突然静止,我想就这样离开,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简单而美丽。我是个生活的失败者,没有我他们会更好。我想了很久,该如何结束生命。很多次水变冷了,我又加温直到热水几乎让我昏倒,皮肤烫红了。然后我想,等等,我不能这样做。我明天还要跑15英里,我一直在为伦敦马拉松赛备战。
这样疯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突然感到内疚:可爱的格蕾丝、贝蒂还这么小;在生活上照顾我的丈夫和家人还需要我——我的姐姐还盼望我第二天参加她的生日会呢!我要跑步。否则我会失败。跑步是目前我做过的唯一一件成功的事情,我要继续跑下去。
(2012年4月,索菲参加了马拉松赛,为全英自闭症社团筹集了4000英镑的善款。格蕾丝接受特殊教育的申请已得到批准,目前正接受全日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