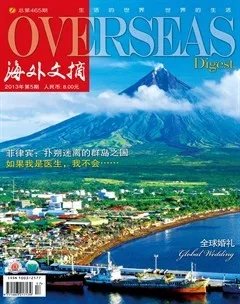一个难民的欧洲流亡之路


2010年12月,基达内·特克利特·亚瑞德决定不再做自己。
朋友们告诉他应该怎样做。这个年轻的厄立特里亚人走进罗马的一个超市,买了一管脱毛剂。基达内忽略了警告信息“使用时间不要超过六分钟”。他用瘦削的手指浸染上这种腐蚀性药膏。10分钟,20分钟,开始是刺痛,后来就是火辣辣的疼。半小时后,他终于受不了,洗掉了药膏。一天之后,基达内把他在油中浸泡过的指尖压在炽热的电炉上。烧焦的手指还要折磨他几天,涂在伤口上的凡士林也不管用。说着这个地狱般的过程时,基达内摩擦着双手,似乎还能感觉到疼痛。
基达内是一个难民。自他2008年到达地中海蓝佩杜萨岛以来,指纹就是他的敌人。它们把他定位为从意大利进入欧盟的移民。现在,他想毁掉它,毁掉这个可怕的咒语。
基达内的故事就是一曲欧洲流亡之歌。它告诉我们,数万到达蓝佩杜萨岛的非洲难民最后的结局如何。他们怎样在欧洲来来回回,一直抱着能留下来的希望。他们怎样因为一部叫做《都柏林Ⅱ》的法令不得不返回意大利,生活在大街上。它证明了欧洲难民政策的失败,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德国怎样把非洲难民推给南欧国家。
在意大利流离失所
这是罗马近郊区一个地铁站附近的贫民窟,约150个难民生活在由门、栅栏余料和生锈的铁板搭成的小屋里,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基达内和他的两个朋友生活在一起,房间里有烧焦的洋葱味,小房间没有窗户,房门上是黑色的字母“上帝帮助我们”。
他本来在厄立特里亚过着体面的生活,基达内坐在已经睡坏的床垫上说。这个26岁的年轻人有着黑色的短发和干净的胡子。他的父亲是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机械师,在厄立特里亚收入良好。他在马萨瓦大学学了5个学期的海洋学。“我的家庭为我的欧洲逃亡之路支付了几千欧元。”基达内用流利的英语说,“本来我可以用这笔钱在厄立特里亚安身立命。”
谈到家人时,他的声音变轻,呼啸而过的汽车几乎盖过了他的话。他很少和母亲打电话,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两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基达内已经在欧洲了,他说他“无法和父亲告别”。
在厄立特里亚,没有基本权利可言,宗教自由也只停留在纸面上。基达内说:“政府关闭了我们的新教教堂,我们在私人聚所秘密祷告。2007年,我们被捕,在监狱关了7个月。”在一次转移罪犯时,他成功逃出,决定离开家乡。“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再次将我送进监狱折磨我。”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被禁宗教团体成员在厄立特里亚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困难”,常常被捕或监禁,柏林外事局证明说。
偷渡者带基达内越过边境到达苏丹,货车载着他们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利比亚。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出发,基达内搭一艘渔船,和其他350个难民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穿过公海,到达意大利属蓝佩杜萨岛。2008年10月,基达内到达富有拯救意义的意大利海岸,然而最初的喜悦很快变成一场噩梦。“我只想在安定中生活。”四年后他说,“如今我却坐在了苦难中。”
因为在自己的祖国有生命危险,基达内在意大利处在“附属保护”之下:他有三年的居留许可,可以工作,也可以找房子。根据法律规定,他在健康护理和社会援助方面和普通公民一样,实际上这张居留许可却毫无价值。因为意大利的难民系统如同一出装模作样的滑稽喜剧,难民获得住处后混乱就开始了。在基达内表明自己需要保护的申请获得通过后,他必须当天就离开西西里岛的临时住所,然而新的去处并没有安排好,他没有钱,语言也不通。
按原计划,基达内接下来应该在“政治避难者和难民国家保护体系SPRAR”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些住所强调融合,提供语言课和心理辅导。人权机构、意大利难民委员会会长克里斯多夫·海恩估计,在意大利生活着7.5万获得认证的难民和寻求保护者,“但是床位只有3000多个”。SPRAR顾问丹妮拉·迪·卡普亚坦言,“目前我们至少需要5000个床位,而这由于预算漏洞根本不可能实现。”
结果就是,几千获得认证的难民在意大利流离失所。海恩估计,仅仅在罗马就有6000人生活在大街和收容所里,基达内也是其中一员。像罗马地铁站附近那样的贫民窟也出现在都灵和米兰。失去家的人在野营地、老火车车厢和废弃房子中过夜,伸出援手的往往只有援助组织和教堂,而它们也力量有限。面对《明星》杂志的质问,意大利内务部没有回应。
每天中午,基达内都站在罗马中心的食品发放处,那里离意大利建国者维托里奥·艾玛努埃尔Ⅱ的宏伟白色纪念碑不远。“来的人太多了,食物根本不够分。”他说。因此,他从上午就开始排在长队中。“我们在意大利的生活内容就是等待,等待床位,等待食物,等待情况好转。”他说,“我想做一些事情,上大学,工作,提升自己。”但是,没有固定的住处,就不可能找到工作;没有工作他就不得不流浪街头。对他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往另一个国家。
在挪威的短暂美好
一个亲戚给了他票款。2009年5月13日,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他开始了到达欧洲之后最好的日子。他主动在官方报到,交出指纹,申请避难。到达几天之后,他就开始在一个书店工作。之后他在北方港口城市波多生活,免费住宿,每个月从国家获得2000克朗来购买食物和衣服,约合270欧元。他甚至在一个鳕鱼养殖场找到了一份时长八个月的工作,这位曾经的海洋学大学生在那里做水检。不久,他爱上一个同样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姑娘。说到这里,这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脸上有了光彩:“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抵达了欧洲。”
2010年7月,一份来自挪威难民局的公文传来。意大利接受了他的遣回,他被驱逐出境。一个律师翻译给他听,他在那儿获得了一个床位。指纹出卖了他。
自2003年起,这种驱逐在欧洲成为可能。当时《都柏林Ⅱ》协议已经生效,这29篇官方正式文献就是基达内流亡的原因。从那时起,只有最初抵达国对难民接收程序负责,禁止“难民购买”,即难民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以寻求最好的福利条件。实际上,北欧富国就此摆脱了对非洲难民的责任,例如德国和地中海不相邻,非洲难民要直接抵达德国避难简直不可能。90年代开始,德国难民数量持续下降,目前大部分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
数据显示,难民带来的压力分布得非常不平衡。去年,30多万人在欧盟国家申请避难,比前年增加了4万人。而德国难民数量和前年相比只增加了约5000人,达到约5.3万人,而意大利难民数量在同样的时间内翻了三倍,从1万人左右,增加到3.4万人。
欧盟委员将他们搜集到的难民指纹存入欧洲中心数据库Eurodac,和170.5万其他人一样,基达内指纹的电子图像也保存在这里,这些数据将在这里留存十年。只要基达内在一个欧盟国家寻求庇护,他的指纹就会和数据库中的匹配。几天内当局就会知道意大利该对他负责,随后准备遣回他。
重返意大利,苦难轮回
2010年10月22日,基达内搭乘一辆挪威空客抵达意大利。“好了,你可以走了。”在米兰机场,一个警察对他说,他不再提及当初承诺的住处。基达内逃票乘坐快车回到了罗马。
他回到罗马近郊的一所废弃房子里,他们称之为“客楼”。如果不是平屋顶上的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和外墙上几十条白色电线束,这个七层大楼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办公楼。金属栅栏中的一条缝隙为进入大楼开道。这里为基达内提供了多个月的睡处。人们挤在一起生活,巴掌大的地方中摆满了床垫、床架。一个戴着头巾的厄立特里亚人说:“《都柏林Ⅱ》协议就像艾滋,慢慢地会要了你的命。”
希望已死。这些远离家乡的非洲人坐在一个从来不会成为家的地方。年轻人昏睡在床垫上,从塑料瓶中喝烧酒。住在这里的约700人很少离开这栋大楼,有些人已经被遣回了5次,很多人已经完全放弃。
毁掉指纹,抵达德国
基达内不想这样,他宁愿毁掉自己的手指。
当他坐上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时,没有人注意到他毁掉的指尖。他用在挪威赚得的积蓄买了车票。2011年1月14日,这个厄立特里亚人在黑森递交了避难申请。他称自己为基达内玛雅木,把年龄少报了四岁。像所有抵达者一样,他被送去做“身份认证”。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的工作人员让基达内把刚洗过的手指一个一个放在扫描仪上,因为指尖烧毁,不可能和欧洲数据中心的指纹匹配,但是他们认为他很可疑。
黑森州奥伯乌尔泽尔市中一个米色的波纹板集装箱成为基达内的住所。他不知道的是:多特蒙德BAMF的都柏林委员会已经准备遣回他了。他非常无奈:“不仅仅是意大利,整个欧洲都需要一个能够更好地规范难民保护和保证人权的体系。”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遣回意大利的人在回去之后会得到一张车票,能顺利到达住的地方。”BAMF主席曼弗瑞德·施密特坚信一个罗马员工的报告,“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根本不想在国家提供的住所过夜,宁愿去大城市的朋友那里。”
基达内也再次被迫回到他所谓的“大城市罗马的朋友们”那里。由于强降雪,他2011年12月20日的遣回之行滞留在米兰机场。“到达时,我没有拿到车票也没有睡的地方。”他说。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机场大厅的银色金属椅子上度过的。
《明星》杂志来到施密特位于纽伦堡的办公室。这位当局领导若有所思地透过无框眼镜看着罗马的窝棚和废弃大楼照片。这符合施密特所说的“欧洲最低标准”吗?这位当局领导会让他自己的只比基达内略小的两个孩子在那里生活吗?“当然不会。”施密特称会将罗马的情况上报,“《都柏林Ⅱ》协议很好,虽然它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有些问题。”
指纹之咒,流亡何日终结
回到罗马后,基达内再次提交了住宿申请。“至少要等两到三周。”有人用圆珠笔在白色的纸片上潦草写道。又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几个月的等待之后,这个夏天基达内又一次来到德国,火车票是他的德国朋友们出的。
这些天,基达内再次提交他的避难申请。援助组织的员工帮助他,BAMF暂时仍让他在奥伯乌尔泽尔市的波纹板集装箱中过夜。尽管法院诉讼程序再次启动,当局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他遣送回意大利。
历时四年的欧洲流亡之路仍然没有结束。基达内不会放弃,他试图成功地逃离指纹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