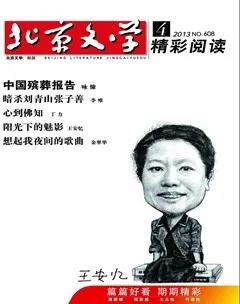从里往外写:李唯小说的叙事路径(评论)

十几年前,读《腐败分子潘长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此前我没有读过李唯的小说,此后我记住了“潘长水”的名字,也记住了李唯的名字。李唯的小说,写得曲折、深透,而又平实、亲切,有自己的腔调和情调,有自己的气质和性格。初看上去,他写小说,似乎大大咧咧,有点嘻嘻哈哈地闹一闹的意思;他的幽默也是有感染力的,时不时地会惹人笑出声来。但是,读着读着,你脸上的表情和内里的心情,就起了变化,就笑不出来了。在那幽默的背后,是含着深深的感喟的,是有着下坠的心绪的。你因此便沉重了起来,甚至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写小说的通病,是停留在表面的浮泛化与率尔操觚的简单化。有的小说家,得着一点素材,便不加深思,不事开掘,以近乎随便的方式敷衍成篇。这就造成了叙事的无意义和普遍雷同,术语谓之“同质化”。这样的小说,读时便觉无趣,读罢一如没读,——既没有阅读的美感和欣快,也没有人生经验的增加和丰富,只觉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被戏弄的沮丧感和懊恼感。
好的小说,是从里往外写的小说。它写人物,必深入其内心,设身处地,悬拟揣想,直至将每个人物的个性气质、言行举止,都了然于心;将他的所喜所恶、所爱所恨等种种心思,都了然于心;将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他们的环境因素,都了然于心,这才下笔来写。这是一种充满怀疑精神和反讽精神的写作态度,是一种与消费时代的娱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反道而行的叙事路径。它感兴趣的,是人物以及生活的复杂性。这样的小说意味着发现,具有解蔽的性质,——它要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表象下面,发现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和本质。
李唯的小说,就属于这种从里往外写的好小说。他对人性和权力的主题极感兴趣。他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探索人性异化和权力腐败的秘密。严肃而重大的主题,要求一种既有思想深度又富有人性内容的写作路径。仅仅满足于渲染人性的阴暗和权力的丑恶,仅仅满足于嘲笑和挖苦,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李唯无疑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在写《腐败分子潘长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一个“另是一种”的“腐败分子”。他从人物的“自尊心”入手展开叙事。这是一个极高明的角度。因为,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尊严感——它的延伸物是“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等——不仅是人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而且也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动力。然而,异化的生活却极大地压缩了人物获得尊严感的空间。像李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样,潘长水本质上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很讲道理的人。当国军连长以“副班长”诱他入伙的时候,“老潘抹了泪”说:“大哥,这不行,我已经参加了八路军。我参加八路走的时候,村里还特地拿出白面来让我吃顿面条。大哥你知道俺们那地界,弄点白面不易,这是人家的个意思。我不能让人家说我没意思。村里还有俺娘,在人前还要活人哩。”但是,现实却“很没意思”,生活也没他这么厚道。就因为做过俘虏,他被当作另类。他的档案里,被写入了这样一句话:“此人可利用但不能重用!”作者说道:“老潘的一生前途都被这句话压住了。”他因此活得很窝囊,很不体面。为了体面,他做了许多别人都不做的事情,“一壶开水嘛,都提了十好几年”。在权力斗争的游戏中,他先是被利用,最后被羞辱。他终于“变坏了”,终于成了“腐败分子”。因为没有腐败的“资格”和“资本”,他被抓了出来,被“开除党籍”。然而,太阳却照常升起,生活也一如既往。潘长水的命运令人感叹唏嘘,也发人深思。他其实是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的写作,依循的仍然是从里往外写的路径。这是一篇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的佳作。能从几十年前的一个已经有定论的大案中,发现新的叙事空间和主题内容,这足见李唯独到的眼光和独具的才华。在《艺概》中,刘熙载曾这样评论苏东坡的诗艺:“东坡诗推到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李唯这部新作的优点,也正在“能透过一层”来观察生活,来展开叙事。
李唯选择从特务的角度、以暗杀为线索来展开叙事。他消解了这类叙事的煞有介事的虚假和狭隘。他排弃了一切伪饰,紧紧地贴住像泥土一样真实的生活和人性来写,或者,就像李唯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在“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生活流程”中来写。在这里,敌人不再是异类,而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官员也不再是怪物,而是同样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的内心有属于人的欲望,也有战争留下的伤害记忆。在这部小说的叙事语境里,无论“敌”还是“我”,本质上都是气质相似、血脉相通的人,都一样有农民的厚道和愚钝、狡黠与粗野。刘婉香觉得自己跟刘青山“有了一种农民弟兄之间的亲近感”,“国民党特务刘婉香和中共地委书记刘青山在共同的农民阶级情感中融合在了一起”。阶级的差异性被文化上的相似性消解掉了。刘青山的爆粗口和讲义气,反映的正是原始形态的小农根性。李唯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中国式的权力腐败和人性败坏,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属于混杂着虚荣心、欲望化、江湖义气、山头主义、目光短浅、俗不可耐等特点的腐败模式。无论在刘婉香身上,还是在刘青山和张子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乡土中国的文化习惯特殊性和文化心理的顽固性。正是这种小农文化和人情文化,造成了腐败的普遍滋生和蔓延。在脆弱的制约机制面前,这种弄虚作假、贪得无厌、狂妄自大、恣意妄为的权力腐败,势不可当,为害甚烈;除非建构起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和惩戒体系,否则,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温情脉脉、皆大欢喜的腐败,将很难被有效地遏制和彻底地克服。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的结构非常巧妙。刘婉香,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农民,偏就被选中当了特务。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角度展开叙事,不仅有助于强化叙事的真实效果,而且还有助于营造出喜剧效果和反讽效果。这是一种闹剧与悲剧、荒诞与庄严、暗杀与明杀、他杀与自杀,彼此纠缠、相向互动的叙事结构。明面上的暗杀,紧张而热闹,却总是被潜在的不易察觉的“自杀”闹剧阻滞和瓦解。“敌我双方”融为一体,“特务”也跟着一起腐败。到最后,特务“暗杀”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却实现了——他们的猎杀对象被“明杀”了;这些暗杀对象自己把自己杀死了,而且死得那么快,那么惨,那么突然,那么必然,那么出人意外,那么在人意中。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被自己的人性弱点杀死的,是被自己身上的小农根性杀掉的,是被那些曾经受惠于他们而又把“报告和请愿书像雪片般地不断送往中央”的人杀死的,更是被自己手中的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杀死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与“潘长水”一样命运的人。在《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的主题结构里,隐含着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它是一个标本和原型,是一个值得深度解读的复杂文本。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