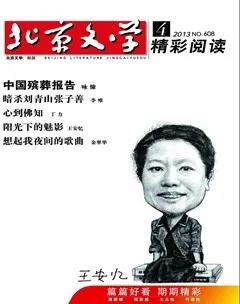文学是闲来无事
关于文学,我想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说几句。
文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学是闲来无事。这是我的定义。
不管谁从什么方面来批驳我的定义。我只认定,文学的内核就是两个人的事,那就是作者与读者的事。有作者写了,就是文本;有读者看了,就是文学。至于传播或传世,那是文学以外更大范畴之文化的事。
饥肠辘辘的声音不是文学,劳动的号子不是文学,爱的眼神、爱的呻吟也不是文学。文学是一个人把自己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对另一个人说。别把生死追问、忧国忧民看作文学本身,那只是文学对人生与社会的一种承担,是任务。文学是读者作者两个人完成比这任务更壮丽的神交。
不知这神交有哪个不是在闲来无事中发生,不知谁可从煌煌几千年的历史中举出这样一个人来!
文学永远是一种发生。存在是它的历史,或者说是过去式。存在就是历史,这逻辑无须争辩。在此想说的是,这历史都是一次次发生留下的,尽管有大量的文本失传,但谁也否认不了其曾经的发生,对今天这个文学基因的染色。
从价值观来说,文学的发生必须是一种新意,不具备新意的发生不构成文学的价值。不论创作还是阅读,没有新意的发生都是文学的附庸。
不知道谁在为文学要尊严。
司马迁被阉,苏东坡流放海南,老舍自沉湖底,没见文学尊严有失。
文学阐释人类。脸上的光彩,内心的龌龊,它都得阐释。它是人类命运中的东西,它只需要诚实,不需要尊严,它在人类命运中充当不了尊严的角色。因为,人类命运,都还不知将终结在宇宙的茅圊里,还是宇宙的宴席上。
说到生活与人生,当然是必须要有文学的。不管他们懂不懂、够不够文学,他们的生活、地位、人生都是踩着文学这两个字而辉煌的。
而另一方面,也绝对有不需要文学的。不要以为这仅是一般愤青的言辞。应该由此考量的是,在此矛盾尖锐的现实中,并不真正呈现谁需不需要文学的问题。事实上,不需要,或没能力从文学挣钱活命的,也拒绝不了文学。
孔雀开屏引诱性伴的审美,是动物的文学。傻子也会说娶个好看媳妇,是“君子好逑”的审美普及。如果说这举例不够严肃,那我还有个小故事:
1937年10月,晋北忻口战役。国军独立第五旅坚守的主阵地安如磐石。11月8日太原失守。不幸的是,该部从编制归属到战场投入,都不在战役军力投入的计划序列,得不到序列部队撤离的具体计划,只能沿太行山西侧绕太原孤军南撤。旅参谋长誓言,要像三国演义诸葛六出祁山赵云断后撤退那样,不让一兵一卒惨落敌手。多少天的艰难苦绝,这位崇尚赵云的参谋长,亲背图囊,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前后策应,眼都不眨地昼夜督军潜行。誓言得以实现,整旅全员撤到晋南。
我父亲当时是该旅的一员兵士。在他活着时,几次泪光闪闪地给我讲述他们的参谋长,在那次撤退中累伤了脑仁儿,到达晋南后,头一发疼,会立时倒地滚作一团。参谋长退役,把对赵云的崇尚留给了当年的兵士。二十多年后,我,也便在学龄前就熟知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没有谁觉得不需要就能拒绝了文学。
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全日制高中毕业,尽管是在乡下。莫言不也是在乡下么?那时当然还不知道莫言,是高尔基三部曲将我拐骗了。
不知道高尔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现在知道莫言是当了兵,提了干,才有更多闲来无事机会的。
而我,1973年底毕业,就一个月便是春节了,我也就从这一个月,便开始每年冬天上水库当民夫了。直到1977年高考,我没有任何机会。
高考的头一天晚上,我看到村小学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息。与我差不多年龄的教员,都在准备,而我在村北的寒风中,给生产队的麦子浇了一夜冻水。我是个农民,同当时许多人一样,耻于放弃当下的劳动,去拼命许是龙门跌翻的羞恨。没什么复习准备,我还在那次答完五张卷子的背面,随时记录了考堂的所有作弊。
一屋子的人都完了,包括我自己。
我不想再高考。不敢说是为了文学,我1982年底才结婚。1983年一个,1984年一个,1986年一个,1987年一个,四个孩子,让我的文学一步步崩溃。
更多的东西在历史转折中休弃。
我用20年拒绝读书。但是,文学一直在捉弄我。
文学是作者与读者的事,刊物却只是作者与帮闲评论家的菜地。
文学是一种精神的诱惑。对我,意味着甘心受骗。
文学是用来阐释人性的。鼓吹与标榜没有意义,暴露主义也是种无能的表现。闲来无事的人,必须得首先认定现实。
在地球村的人类意识聚拢中,中国当下的文学,基本还龟缩在农耕文化的阈限内。而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点,则一直没人拎得清。
中国农耕文化,在国家意义的范畴上,以天子、诸侯、平民、奴隶各自生命权利的血统组织形式家庭,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形态,完成奴隶、平民、贵族各自生命权利在社会层次中的伦常秩序。一切奴隶制的伦常、道德、崇尚,也才从这种社会基本形态上发展起来。《诗经》各篇以及被孔丘芟除更多的,也就是文学在这个基点上最初的璀璨。
而今,最初获得保障生命的物质,已从血缘继承有限的田产财帛,演变成无时无地不在金融泡沫里追求个人“财务自由”的竞存方式。人性的自私直接对应社会中核心而又全部唯一的金融力矩,生命的繁殖及其权利的承袭,都将不再延续农耕经济的文化价值,导致人性的呈现,在普遍意义上突破了田产与硬通货自然存限所载天理人道的阈值。
从现代意识上说,生命权利的基本意义,从法理价值上已趋同于个体人权的社会化平等;家庭这种从地权意义上确立几千年的血统组织,正在被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与政治进程上的法理价值所否定;而人性的自私,决难就此与个人的血统意识一刀两断,却会从实现自我、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下向所有的传统挑战。所有伦理、道德、情理、法理的价值,都需有新的社会定义,来结构人类未来生活的崭新形态。
文学要在呈现社会这一无情嬗变的过程中,展示人性向美求善的再度辉光,探寻生命自我在现实的本能诉求。展示这种诉求在生命于社会组织层次上完成一种新的伦理秩序的可能,文学才有可能从金融社会的文化基点,跨入一个新时代。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