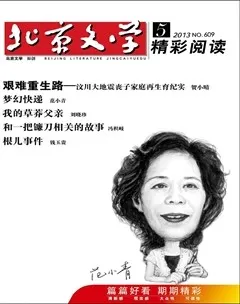乎乎成长录
乎乎:五岁半,语言能力发达的巨蟹座小男生
决定命运的两样
昨晚和朋友Z,还有多年前认识的一位作者郁平晚饭。
饭后与郁平同路。车上她说到她的公司(她办了所教日本人说汉语的语言学校)有不少漂亮姑娘,但都没找对象。姑娘们反映,如今男人(80后独生子女)多自私,没责任感。郁平说,她不要儿子成为自私男人。
郁平儿子十岁,她说带他去吃“肯德基”。有个和她儿子差不多大的胖男孩点了堆东西后掉屁股走了,留她妈在后头替他端盘子。郁平儿子买了东西,把自己的和妈妈的放托盘里端着,问,我们坐楼上还是楼下?
你是男人你决定!郁平答。
我觉得楼上比较好。儿子说。
吃完,郁平要求儿子收拾好桌面(其他桌一桌狼藉,等服务生来收拾)。
很小的一件事,折射出若干东西:孩子的责任感,自信,教养。郁平和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儿子现英、日文都学,但郁平说,成绩不重要,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只有性格和习惯!再没有第三样!她还说,一个妈妈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是,给他阳光的世界观。
天赋
幼儿园开设的美术兴趣班上了若干次,仿佛,你没显示出多少美术天赋,只是能快速完成作业——毛毛虫、彩虹、水果之类,依葫芦画瓢。老实说,我怀疑这些课对你身体中“美术”种子的启蒙作用。但,抱着上比不上好的心态,像所有给孩子报了兴趣班的家长一样,“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有次老师教画小鱼,我见一摞依样画瓢的作业中有一张特别的,它的特别在于那些小鱼的排列。其他小朋友大抵把鱼塞满画纸,你也是。而那张画,一群小鱼在纸的中腰朝一个方向游弋,画纸上下有留白——这使得画面有种流动的诗意。
画这幅画的孩子是有天分的。尽管每个孩子画下的线条都是“凭空而来,凭空而走”,但这凭空中有种与生俱来的对美的天然感应。这个把一群小鱼画在纸中腰的孩子,他对美有种天赋的灵感与把握。
在画画上,麦姐(大你一岁的表姐)应有天分,用麦妈的话说,“随便一个小人,辫子朝天,可爱极了,不知为什么她画的一切都像有神的,冒热气的。”这热气就是那点灵性——西方音乐史上有句俏皮话:“贝多芬走了一辈子才到达的那个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
而乎,你对音乐、跳舞似有比绘画更好的感受力。四月的一晚我放《中国功夫》给你听,你很喜欢。那股子铿锵十分投合你心意!凭着小身体对音乐本能的冲动,在雄赳赳的音乐里,你在床上如痴如醉地武起来!
歌曲豪气冲天,力拔山兮,旋律从缓到急,由疏到密。你随音乐节奏比画招式,小脸严肃,全情投入。慢时如推太极,当说唱到“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身轻好似云中燕豪气冲云天……”时,你陡然一振,快速地腾挪闪移,你的小身子有种奋不顾身的劲儿!谈不上什么套路,但也绝不是胡乱,以一个3岁9个月孩子的对招式的理解与律动,你将中国功夫演绎得形神兼备!
我看呆了!在床边,望你。这是你一人的舞台,我是唯一观众。歌放了一遍又一遍,你要我一直放,每一遍,从缓到急,推陈出新,你的激情每一次都崭新!在你的小身体中蕴蓄着多么蓬勃的能量啊!
(然而一年后,在学校学了此首歌的早操后,你丢失了这种即兴原创的灵感!每当音乐响,你努力回忆着学校教的套路……)
音乐感受(3岁10个月)
下午你画画,我看电脑,边放舒伯特的《小夜曲》。你听了一会儿,点评:这个音乐,好像妈妈死了一样。
我晕!不过我知道你听出了其中的宁静悲伤。
只怕心碎
最近,你在歌唱方面的代表曲目是《虫儿飞》,很美的一首歌!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只要有你陪……”你唱得很完整。有次你在电话里唱给舅婆听,她好一番赞扬,觉得你吐字清楚,音调分明,对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已不易。我赞同她的听后感,并相信这其中没有“人情分”。尤其你唱到“虫儿飞”三字的高声部时,最是好玩,音调陡然升高,像虫儿陡然振翅一飞,而后又低下,“一双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心碎这个词从小胖的你嘴里吐出,真有种奇异反差!好玩的同时还有一点……什么呢,你一定还不能理解成人的“心碎”。你的心碎最多为一个未买的玩具,一袋零食。像昨晚在外面吃饭,瑞瑞哥把饮料喝完,你很沮丧,半躺在地板,叹息“好倒霉啊”!最后你把明明已空了的橙汁瓶再次举到嘴边,努力举高,瓶子里仍然没一滴落下,我想这是你心碎的时候!
睡前谈话
“请你不要打扰妈妈好吗?妈妈现在有点事。请你配合好吗?谢谢!”
“不用谢。”你在床上礼貌地说,同时坚持让我陪你上床玩。我不肯,你哭起来。
睡前,与你同学许可证(这名字真牛!)的妈妈网聊了几句。她说起许可证近期一人睡,不要爹妈陪,我想到你每晚必要妈妈陪你上床,有时甚至晚上九点,我就得应你之邀上床,像在坐第二次月子。
我打算严肃认真地和你谈谈。
我说起你一两岁在上海时,妈妈晚上在电脑做事,你睡在大床看着妈妈,一会儿就睡着了,现在怎么天天要妈妈陪呢?我知道你爱妈妈,可爱不一定要这样黏着啊……
我还在唐僧般碎碎念,你气呼呼地说,“你不要说我小时候的事好吧,”又说,“这些事没意思!”
天哪!妈妈真的很想笑,可竭力忍住,不破坏谈话的严肃气氛。
“好,那我们说说现在。”我努力说服你要学会独处,别让妈妈当你的连体人。
你最后终于带着哭音答应自己睡,妈妈做完事来陪你。你的脸一直朝向我,刚剪完头愈显憨圆的小脸渐有睡意,睡去。睡前你费力睁下眼皮,确认我在,在你几步远的地方,守护你。
窗外变天下起雨,风声在北面一路奔跑过去。许多个夜晚中的一个——是有了多少个夜晚,才有了今夜的这一个?
“四季很好,你若在场”,以前你不在场时,世界对我也是完整的,没什么不同。你来之后,才发现以前的完整原来并非真的完整,有了你之后,世界才真的圆满。
昨天整理相册,有一本放了些你出生以来的照片。从最初那个五斤四两的瘦弱小生命,到如今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真让我讶异于生命的神奇。
有一张是一双臂弯抱着你的照片。你爸,他一手托奶瓶,另只手托着你的头,姿势稳定而牢固。茸茸黑发的你吮着奶瓶,那时你三个月左右吧,我只顾着给你的脸一个特写,拍下你爸的一双胳膊——也许这本来就是种喻示:每对父母之于孩子,最重要的都是一双可倚靠的臂弯,他们的相貌无关紧要。像我读过的一个句子,“……长春的爸妈家对我来说,就像世界的终点,后背终于可以倚到墙。”
照片上这姿势永不可能在你和爸爸间重演了,你过了吮奶瓶的年纪,小胳膊的气力正一天天增长,直至有天超过爸爸。
我知道等待我们的不会尽是欢乐,伴随你成长的必然有我们的衰颓、烦恼甚至苦痛。我仍要深深感谢!我的脾性,我的日月,全在与你的点滴相处中有了潜滋暗长的变化。我不知道它是否朝着更好变去,我只知道在我多出的这个称谓“妈妈”里,实在有太重太重造化的恩馈!
男女混洗才有意思
昨天挺晚了,你还要下楼散步。因晚饭后我允诺了的,一直拖到近十点,你仍要我履行。好吧,下楼,你欢蹦在前,我就像遛只小狗。
街道行人已少,不少店铺已打烊,却不影响你的高兴劲儿。
上楼时,我说让爸爸给你洗澡。你不肯,要妈妈洗。
你是男孩啊,宝宝大了,男孩当然和男人一起洗。我说。
“男的和男的洗澡没有意思,”你急了,“男的和女的洗才有意思!”
@#¥%# ……
还有一个月,你四岁了。
比春风更美的笑
“一个幸福的人就是有幸福感的人。”电视里,高晓松晃着长发蓬松的大脑袋,一语中的!
谁不想追寻幸福呢,哪怕苦难令我们伟大,令我们心智深邃,我们宁肯做个平庸的有福之人,而不愿做一个深刻痛苦的智者。
幸福,在一千个人那儿,有一千种注解。在你这儿,幸福就是——吃喝玩乐!
你一岁多时,外婆有次感喟你一点没表现出像某些天才小家伙那样敏而好学,背诗百篇,遂感叹,“就知道成天吃喝玩乐!”我诧异,这会子不吃喝玩乐,更待何时?难道要一岁多的你早读唐诗,晚诵新概念么?一位猛妈说得好,“童年不就是拿来浪费的吗?能浪费的时候不浪费,才是更大的浪费!”
直到四岁多,目不识丁的你仍延续了以吃喝玩乐为主旨的生活,我也随你,并替自己的“不作为”找了不少依据,如台湾作家侯文咏所言:
“常听人家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我想说的却是:别让孩子的快乐输在起跑线上……成绩或才艺就算输在起跑线上,将来如果有需要,要追补都为时不晚,但快乐这样的气质却是从小就必须养成……”
的确,任何专业技术都可弥补,都可大器晚成,性格养成却基本是种童年范儿——它像名媛气质一样得从娃娃抓起,后头修炼虽有效,毕竟不如童子功。
我宁肯你庸常地快乐,也不愿你阴郁而优秀。
我太爱听你笑了!你常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为些鸡毛蒜皮。前阵子在沪,晚上你看一部动画片,乐不可支。夜里你在梦中大笑有声,把外婆吓一跳。她讲给我听,我听着,心里温暖。一个做梦笑出声的孩子,充满了对人世多大的信赖与满意!真愿你把这快乐延伸下去,延伸在你人生每个角落。
我想玩简单点的
你觉得自己幸福不?我问。
不觉得。
为什么?
你和爸爸老是做事!
我无言以对。我所指的“幸福”实在很狭隘!我问你是否幸福时,多是给你好吃好喝或又给你买了新玩具时。然而,对你,那也许的确不是幸福,至少不是最幸福。你最高兴的是我们陪你玩,和你一起疯!
像此刻,你让外婆用毛巾被把你做馅,包饺子,你的小脚丫伸出来,外婆说,饺子皮破了呀!你笑得乐不可支。你假装找醋给外婆蘸饺子,外婆问你什么馅。
“恐龙和鳄鱼馅的!”你说。
“啊?好吃么?”
“放点糖,还要把外婆放进去就好吃了。”你哈哈大笑。
你把几床毛巾被包来包去,说要把山包起来,你乐此不疲,其乐无穷。
外婆说,“好了,玩拼图。”外婆惦记着你的益智工作。
“外婆,我想玩简单点的。”你说。
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编《女友》杂志的情感问答栏时,每期都收到不少女性要求转给主持人的邮件。这些邮件来自各地,主题却一致,基本可归纳为“被伤害”——与丈夫糟糕的婚姻关系,背叛、欺骗、伤害、争吵……她们中许多人是妈妈,不愿离的原因都是“因为孩子”。
教育专家孙瑞雪曾说,“爸爸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爱妈妈,因为妈妈是孩子的皮肤。”那当爸爸不再爱妈妈时,怎么办?
当爸爸不爱妈妈时,妈妈至少应当爱自己!可在不少邮件里看不到这点,只有妈妈的自艾自怨,只有妈妈的痛苦沮丧,只有妈妈对孩子的内疚无奈……
妈妈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当爸爸不再爱她时,她仍爱自己。爱自己的妈妈才有能力爱孩子。
六画的字
昨晚带你去看外婆,外婆一见你,脸上神情真年轻!是种打心底的焕发,是由衷喜欢才有的发亮。
饭后你诚恳地问外婆,“外婆,你怎么这么老,你怎么还不死呢?”
@#¥#%……&*
好在外婆很淡定。
还有次,早上,你问,“妈,骷髅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有关死亡标本的问题,还真有点复杂。
“嗯,是人死后,埋在土里,然后肉身腐烂,就剩骨骼了……”
另次你问我,是瑞瑞哥先死还是麦姐先死?瑞哥比麦姐大六岁,不等我答,你说,一定是瑞瑞哥先死,因为他大。在你如今的意识里,死按年龄先后排序。
周国平先生说了,不能轻率对待孩子提出的死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是孩子灵魂中有价值的困惑,不应被随便打发掉!成人切忌用一个平庸答案来把问题取消。
如何的回答才算合格?死亡,它涉及生物、医学、信仰等等。每个人,每一天都在面临这问题,也正是在追问过程中,获取着“生”的点滴启示。
“生命是一种聚合,死亡是一种发散”。有一天,接受死是种必然的人类宿命甚至休憩时,死就没那么可怖了。死的面目是会转化的,像光在不同角度会折射不同影像。
死,这个在词库中最被忌讳的字,说出它或写下它就觉得陷入阴暗的字,也许有一天,它会消解这些禁忌,回复到一个寻常汉字,和“吃”“米”,和“光”“年”这些同为六画的字一样。
灯为何而熄
年初二,从外婆家回,家门口路灯全熄,估计是电路坏,过年无人修。
“平时好好的,过年反倒坏了,真是的!”我说。
“因为要放焰火啊,黑了放焰火才好看。”你说。
啊,多美的理由!街道的黑似乎一下有了含义,原来是为了成全焰火的璀璨!
地下河
多年前,一位北方女作家对我说,也许有一天她会写写她母亲,不过,她还没准备好……她语气十分复杂,让人觉得这个“准备”需要数年乃至一生。或许到最后,这位本来相当擅长修辞与表述的女作家也不会写到母亲。
我理解。世上,我用最不耐烦的声调与之说话的是我的母亲。有很长一阵子,我们几乎不能说超过三句的话,超过三句即吵,双方声音都变得极不好听,心里窝火。然而,并无隔夜仇,次日或一个恰当时候,很自然地又说起来。怨与惦念等同。
我在医院频繁出入的那几年,常做些小手术。每一次,母亲都在手术室门口候着,直到我出来,奔赴上来,握住我的手,脸上那样一种忧愁、焦急与心疼,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毫无遮掩,骨头连着筋的情感!“我若为她流一泪,她必为我如泉涌”,可这并不能抵消我成长中母亲对我刻薄、粗疏、急躁时刻带给我的伤害。我们常有矛盾,我有时觉得我每一次不耐烦,每一次突然尖刻或狂怒起来,是潜意识中把往昔的“账”全都一并计入!
在我突然狂怒起来的时刻背后,潜伏着一个原因——妈妈,我和你多么肖似与雷同!我恼怒你的那一部分,也常是我厌弃自己的那部分。当我痛数你身上那些不堪时,恰因为知道,它们同样深植于我,难以移除!
“互为依赖、彼此制约、协同进化”,这在生态学中诠释“相克相生”现象的话同样适合我们。这些年,我们正是这样过来,刺猬般反复摸索最适宜的距离,近了痛,远了冷,我不知道我们最终会否寻找到一个黄金距离,既能相温又不致彼此伤害。
衡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足够丰富、多向度。然而,最理想的亲人关系当数明朗、单纯。宝,希望爸妈与你之间尽量靠近一种直接与简单——这世间诸种关系几乎都有纠葛在其中,夫妻、同事、朋友……然而,血缘,这是人类最后的机会,最后让彼此关系纯化的机会。
仅有爱是不够的,比爱更重要的是,良性的爱的方式——在许多家里,爱比不爱更糟糕:因为爱,遂有了要求、期待、胁持……有不少亲缘关系在这当中不停磨损,直到彻底疏离。
乎,我希望爸妈永远是你最可信赖的人,任何时候,你不会因找不到可沟通的“门”而无法启齿。当然,在你如今四岁时,这一切看上去不难实现。可我知道,再过十年,难度会增加十倍!许多父母,并非伊始就想与儿女成为宿敌,但在经过一个个节点后,他们却往最不希望的方向去了。
这世上,最让人悲观的是糟糕的亲缘关系。有次春节前,邮局,一位老妪在交费,边抱怨水电煤的涨价。邮局的人开玩笑,涨点价算啥嘛!马上过年,儿女不得孝敬你个红包?老妇说,“指望他们孝敬?他们别来沾我的就行了……”她神色寒凉,有苦难言,她整个人的神态让我觉得,她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意义被一笔勾销了!
她靠着柜台,说不出的荒芜。
伴侣不睦可分,朋友不合则淡。可亲人,它是条无法断绝源头的地下河的上游,承载着我们对人世的信心和最坏境地时的慰藉。
惩罚,如果不是为了爱
美术兴趣班。这学期最后一节课,家长可陪同。这节课老师教画的是蝴蝶,色彩和图案有点小复杂。只听后排传来一男人粗鲁呵斥,一位父亲在骂儿子不好好画。那孩子,大约是大班的,五岁左右吧,低头不吭气。再一会儿,那父亲又开骂,夹杂连串脏字。骂着骂着,他动手搧了孩子一耳光。我气愤地叫了声,怎么这样对孩子!他大约看到周围投射来的眼光,索性让孩子收拾书包,“不上了,给老子滚回家去!”
孩子呜咽着收拾东西。透过窗玻璃,走廊上,男子斥骂着,在孩子身后踹了一脚——几乎可以想象那孩子的未来,多半阴霾笼罩。据说,在暴君制下长大的孩子,或者屈从、萎靡,或者怨毒、冷酷。
一个不给孩子尊严的人,一个以粗暴欺压孩子的人,一个让孩子内心充满恐惧羞辱的人,配做父亲吗?J3njg9W4OoLiCjtNpRwqWQ==不配!也许他父亲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所以他理直气壮地沿袭。这类人,他们不会想一想,在他们五岁时,能否麻利地画好一只彩色蝴蝶?
孩子让人生气愤怒的时刻在所难免,惩罚也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惩罚。
一位叫陈洁的妈妈曾谈到与儿子的矛盾,“不管用什么惩罚方式,让孩子明白其中有爱,是最重要的。爱显然是比任何手段都有效的教育方式,或者说,它是任何教育的基础。离开了爱,惩罚就成了敌我矛盾,除了滋生敌意、仇恨、屈服、对暴力的信仰,没有其他作用。”
极是!在许多对孩子的惩罚中,放纵着成人的自私与乖戾,在以“惩罚”为名号的行为下,实施的是成人以大欺小的霸道——别以为孩子无力反抗便是惩罚“成功”,譬如那位美术课上的父亲。请记住,孩子遭遇的一切不公,他必会以另种方式“回报”——你根本不能想象这对父子今后会相处和睦。那孩子,在父亲老了后,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回敬父亲因老而带来的衰迈。
惩罚假如偏离了爱,就会成为一己的情绪宣泄,成为成人张扬强悍、滥用权力的“理由”。而往往,错误的教育方法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很有效。
别急着惩罚孩子!惩罚前请想想,从孩子的年龄与心理出发,这事儿真值得惩罚吗?哪一种方式会更有效——而不是更利于快速地出气!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电脑出故障,之前你动过我电脑,我因此把责任归咎于你。我沉下脸,叹口气。你靠在我旁边说:“你心里肯定是想这个,‘我生这个儿子有什么用!’”说罢,你黯然趴在一旁藤椅上自己玩,百无聊赖。
你的“读心术”让我惭愧。
一位广州的IT工程师父亲说:“先别为你教训孩子的次数忏悔,因为教育同其他事情一样,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比责骂一次更糟糕的是带一个‘总’字。‘你总是不按时睡觉’,‘你总让我担心’或者‘你总是哭哭闹闹’。这样的话不仅打击孩子的这一次冒失,更彻底地摧毁孩子的自信,让他明白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取得成功。”
要承认,这个“总”字也是我的常用字,有时你淘,我很自然地批评你,“你每次都这样是吧……”“你又气妈妈是吧”,诸如此类。把单数错误膨胀成复数的旧账,似乎这样,能加大你犯错的严重性、一贯性,更利于我批评你的力度。
然而,像那位父亲说的,这实在是比“最糟糕”更糟糕的一种方式!
灵魂像云一样
我在睡,你在一边画画。迷糊醒来,你拿来一幅画,指点给我看,“这是大鲨鱼,这是轮船……”画面右上方,轮船上塔楼旁画了个不规则形状,有点像海马,你说:“这是灵魂!”,我吃一惊,“灵魂就像云一样。”你接着说。
再补充说明,“灵魂在云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