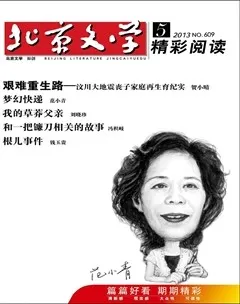惶恐滩头(外一篇)
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更是吉安的母亲河。从秦至清的两千多年里,赣江一直是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于是可以说,沿途的赣州、吉安等地都是水带来的城市,它们因水而发达。多少年前,在铁路和公路没有开通之时,赣江,它就是一条北方通往岭南唯一的航路。它是官道,也是维系着民生民情的生命道,可以说帆樯竞发、舟楫穿行的景象是名不虚传的。
然而,赣江又是一条天险之路,尤其是吉安的万安至赣州这段90公里的航道,竟有着艰难险阻十八滩。“赣江之险天下闻,险中之险十八滩,船过十有九艘翻”,此说虽然邪乎,但也说明这段河道的非同一般。
十八滩的最后一滩即是惶恐滩。
我站在惶恐滩头向上看,两岸是高山绝壁,硬是把一条江挤在了怪石嶙峋的险狭之处,汹涌而来的江水无路可走,就在这一地段挤成破浪碎涛。由于水下暗礁林立,那水声就更显得惶恐争鸣,有诗说“赣石三百里,春流十八滩;路从青壁绝,船到半江寒”。惶恐滩是赣江上游的最后一个锁口,之所以叫锁口,其险可想而知。过了这道锁口,两岸豁然开朗,江水一决而过,像松一口气一样,变得舒缓平阔。
因而赣江行船的人听到惶恐滩,没有不感到惶恐的。然而要上行和下行又必得走这惶恐滩。“涛声嘈杂怒雷轰,顽石参差拨不开。行客尽言滩路险,谁叫君自险中来?”那时的人们,行船到这里,就等于把脑袋别在了腰间,拼过就活了,拼不过就会葬身在这万顷波涛之中。
我在岸边遇到一位撑筏的老者,老者说:他的爷爷就是死在这惶恐滩头的,那是他亲眼所见。爷爷和几名船工把着一条运粮船,行到水急浪高之处,那船就再也把持不住,由着水性被甩在了礁石上,船立时就翻了,人落在水里,冒了几冒,连叫的声音都没有,就再无了踪影。他后来只在岸边捡到了一些船的碎片,家人把那些碎片埋在了岸边,权当是爷爷的坟墓。
老者说,这片滩头那时多有拉纤人,也有胆大的撑船人。为了挣钱,总有些胆大的人要拿着自己的性命与这艰险搏上一搏。所以很多的船只到这一带也会把命运交到这些人手里。
这个惶恐滩头,水小了险恶,怪石更加峥嵘,撑船人受到更大的限制;水大了也惶恐,因为水流湍急,礁石隐在了水底,水流不定旋转到那里,就会划散船底。
当年的苏轼被贬广东惠州,而后又奉诏回京,必也经了这个赣江天险。他在《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中写道:“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多少年过去,又一个人物辛弃疾路经万安县南的造口壁,也写有“郁孤台下清江(赣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想这两位大才子也经历过惶恐滩头波涛的洗礼,算得是有惊无险。
吉安人文天祥对这一带赣江应该是十分熟悉的。1277年,他在永丰兵败,从这里退往福建。两年后,在广东海丰被俘,因而有诗一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他或与这赣江太有缘分,被捕后,誓死不降,元兵无计,将他押解,乘船顺江而下,押至京城。文天祥绝食数日,计算好行程,决心船到家乡时魂归故里。然而船顺风而下,没有达到他的预想。假如船在这惶恐滩激流触礁,文天祥也便与这赣江组成一曲千古绝唱,不至于首刃菜市口。
一阵风从上游的山口踅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我猛然缓过神来,身边的老者也已撑筏远去。
实际上,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惶恐滩的争鸣景象,这个锁口之地,现在已变成了一座一公里长的大坝,大坝的下面就是在江西数第一的万安水电站。这个小电站1958年上马,后又在1961年下马,经过多少周折,前些年,才形成了现今的样子。
我走向大坝的中间,那是一个船闸,可供上下游的船只经过,而就在这船闸的下面,就是赫赫有名的惶恐滩的最险处。脚踏其上,心内还真的有种异样的感觉自脚底涌起。顺着大坝向前望去,赣江在这一段已经形成了一个高高的平湖,是大坝和两岸的山峰共同抬高了水面,同昔日的十八滩真的是两个景象了。
正看着,叽叽喳喳来了几个女孩子,问起她们可知这个地名,她们竟然不知道惶恐滩而只知道水电站了。
走下大坝,当地的一个朋友递给我一本书,我在书里看到一幅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惶恐滩头的画,一时又让我陷入思古之幽。
归来打开博客,看到一个熟悉的网名的留言:听说你去了万安,也去看了惶恐滩头的水电站,而我就在那个水电站里上班。我倒想起来了,她曾经跟我说过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我的眼前,一个女孩子天天守着这古老的赣江水,面对着惶恐滩头写诗的形象顿时鲜明起来。
张翰回家
《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有人以为张翰辞官是逃避政治险恶,早预见好了的,未免就高看这个才子了,他的身上,还是文人的气质多一些。说他逃避,还不如说他是厌烦。西晋时期很多的文士多是如此。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不是追求农转非,而是相反。
张翰的走回周庄,是进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完成了对周庄自然的美丽构建。600年后,一个叫周迪公郎的人来到了周庄,并且确立了周庄的名称,季鹰的回归处终于明确了下来。在此之前,周庄的前身只是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而他离开的洛阳却早已是个大都市了。繁华锦绣,灯红酒绿比不上莼菜和鲈鱼,那个时候不知有没有牡丹花,在张翰眼里,却不比家乡的油菜花。张翰还是归去了,说实在的,“季鹰归处”原来只是个含糊的概念,顶多说是指“苏地”,季鹰带给周庄的意义,远比沈万三要强得多。严格说起来,周庄的文化意味比商业意味要历久而弥香。
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神秘得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很多。《晋书》说他“有清才,善属文,而放纵不拘”。尽管他的诗今仅存《首丘赋》《秋风歌》等六首,却是大名远播。
张翰回家后,常垂钓于南湖,诵读于陋室。在野花芬芳的田埂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在碧水蓝天的旷野间留下舒展的啸吟:
忽有一飞鸟,
五色杂英华。
一鸣众鸟至,
再鸣众鸟罗。
长鸣摇羽翼,
百鸟互相和。
历史记载张翰的生卒年均不详。按说像他这样超脱的文学家、书法家应该活一个大岁数。还有他喜欢的故乡的乡野,莼菜和鲈鱼。但是在57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有时候,悲伤就是这么突然降临,降临得让人猝不及防。
张翰的母亲去世了。
这在张翰的生命中是巨大的重创。张翰悲伤极了,谁也没有想到,张翰竟然因过度悲伤而失去了生命。“悲伤过度”是个什么词语呢?动员所有的想象细胞也难于解说清楚。这就显现了张翰的又一个特性。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比故土、母亲更重的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有着同样性格的人阮籍。阮籍正在同别人下棋的时候,传来了母亲的死讯,阮籍听了坚持同人把棋下完,然后拿起酒杯,大口地饮酒,直喝下两斗,才大放悲声,并口吐鲜血。这些血性男儿,遇到什么事都没有在乎的,对自己的母亲却格外上心。母亲没了,就等于塌了天。世界一下子变得一片昏暗。
张翰就这样死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前飘满了他的诗:
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禁兮仰天悲。
张翰还是没有了家啊!张翰旺年而逝,且只给我们留下了不多的文字。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修曾写道:
清词不逊江东名,
怆楚归隐言难明。
思乡忽从秋风起,
白蚬莼菜脍鲈羹。
他诗中的名句“黄花如散金”,在唐代曾以此命题举士。李白说:“张翰黄金句,风流五百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一行楷书《张翰思鲈帖》,是欧阳询为张翰写的小传。笔力刚劲挺拔、险峻逼人。那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将张翰的形象也勾进了史册。这也是欧阳询把张翰的莼鲈之思看作一种崇高之举,笔墨记之,以述胸怀。每一笔都浸淫了书家的内心情感。后来这幅字帖被广为流传,每一个得到它的人都是爱不释手,有的还加盖了名印,以示珍藏。不知怎的就传到了宫里,宋徽宗看到,欣喜异常,觉是至宝,遂加盖私章,并附言语。
此帖后转到了清乾隆手中,这位在书法上也卓有成就的大清皇帝也是一样如获至宝,喜爱有加。
虽然这是冲着欧阳询的书法,但书中的内容也同时让人入心了。
周庄的南湖因了张翰的典故又称“张矢鱼湖”。
最早知道张翰,是读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时候感觉这个季鹰是个怪老头,不关心政治,只在意鲈鱼。其实张翰年岁并不老,但那时就知道有一种鱼很好吃,可惜我们吃不到。直到十几年后才见到鲈鱼的模样,但那早不是张翰时期的鱼种了。细想起来,那时的物资流通也不畅,要不怎么官宴上没有东曹掾这样的大官想吃的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