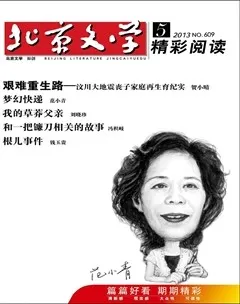网络诗歌三问:困顿与迷茫中探寻未来
网络诗歌正向这个时代展示出它复杂的脸孔: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全民诗歌写作的“时间开始了”,它曾代表着新的写作、新的传播,重新挑起众多爱诗者的写作热情,搅动着日益沉闷与沉默的中国诗歌的一池春水。但另一方面,从出生时起,它就面对着来自传统审美的猛烈批判与打击,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青春。近20年热闹喧嚣后,开放、便捷、互动、开放之外,它正展露出娱乐化、江湖化、浮躁化和粗鄙化的面孔。
它是谁:不是救世主也非罪人
观察一个正在行进路上的艺术门类,以事件观察,或比理论分析更直接。由广大网友和诗歌票友自发评选的“2011中国十大诗歌新闻”中,诗人海啸一首《可爱的中国》在微博发布引发“海啸体”和2011年“首届微博中国诗歌节”推出的“微诗体”在流行事件中分列第一和第四位。它们不仅印证着网络之于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更生动诠释了网络诗歌的界定:前者是广义的网络诗歌,即涵盖所有以诗歌形式出现并借助网络媒体进行传播的文字;后者为狭义的网络诗歌,仅为直接在网络上创作并主要或者率先以网络为渠道传播的诗歌。
简单而言,独立于主流诗歌之外的网络诗歌,在两条道路上开始了诗歌探索的未来之旅。一条是希望之路,一条是混乱之路。一方面是突破固有体制的卡拉ok式写作,最大程度激发了民间写作的热情;平等写作与对话的诗歌圆桌现象全面消解了所有的霸权、经典和权威;“写、评、读、编一条龙”彻底颠覆了传统诗歌传播路径,重构了一个至今已有4.85亿网民和数千万计的论坛、博客、微博空间的互动平台。
另一方面,游戏性为主要价值的文本观;低贱化为表征的美学风格;口水化的言说语系,加以网络特有的拼贴、复制、粘连等技术手段,吸引大批缺乏文学修养和语言基础的业余写手入场,几乎无可避免地制造了网络诗歌写作沙泥俱下的局面。大量的“口水诗歌”“随机诗歌”“快餐诗歌”“泡沫诗歌”直接将汉语诗歌整体品质带到了谷底。而在功利性的刺激下,网络诗歌不仅制造出一批“网络诗歌流氓”,也一度炮制了“梨花体”“羊羔体”等一幕幕网络诗歌肥皂剧。
如此情势下,网络、网络诗歌之于汉语诗歌,究竟是救世主还是罪人?没有答案。因为艺术的演进,从来不是两分法可以划定,而是各种变量的博弈与冲突下融合推进。曾经很多人预言,网络将成为纯文学的墓地,古典诗词在人们的网络想象中,似乎将更无空间,但写作门槛降低之下,网络诗歌带动了古典诗歌的复兴;也曾有论者认为,网络诗歌令诗歌分裂成两个江湖,传统主流的和网络的。但网络诗歌的兴盛,反过来又吸引了很多已有的诗人、诗论家的加入,从而有效提升了网络诗歌的专业化水平,也模糊了两个江湖的划界,并在网络上发表。然而随着网络诗歌的发展,新的山头主义又在网络诗歌江湖生成。
无论开始,还是现在,网络诗歌是如此难以清晰地描述。要看清楚它,我们必须明晰另一个问题——网络诗歌从何而来,即这个神话何以被创造,又怎样被扭曲?
从哪里来:成也网络败也网络?
似乎从一开始,网络诗歌兴衰成败的命运密码,就深深地写进了网络传播时代的命运里。
也只有在互联网新传播时代,诗歌写作才彻底摆脱编审、发行等繁琐的环节,告别媒介制约,而网络载体的不断更新亦不断拓展着网络诗歌的生存空间。从凡有文学BBS处有古典诗词栏目,到博客写作令诗歌更加个人化,再到微诗体以其草根即时性受到网络追捧,并吸引众多名家参与,网络的确为诗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与传播空间。
另一个背景是,变化的时代为网络诗歌贴近现实打开了一扇窗。作为过去二十多年来文学“向内转”的一个反叛和回归,网络写作无疑大大降低了诗歌关注现实的潜在风险。当类似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社会事件出现时,网民们迅速捕捉了社会情绪中的痛感,在与时代形成的共鸣中,再次令诗歌站立在现实的大地上。
网络诗歌之特殊性在于,它的全新生存与表达方式,史无前例的试验和探索,皆来源于互联网给予的自由、开放与包容的环境。只是硬币总有两面,网络代价之昂贵在于,网络诗歌所有的乱象也许都源于此。
社会媒体专家温伯格指出,网络时代没有边界,没有边界意味着没有形状,没有形状又意味着网络化的知识缺少知识的核心要素:基础。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网络诗歌,当网络给予阅读和创作群体前所未有的空间时,也颠覆了传统诗歌所有的基础。这令网络诗歌成为一座沙上之塔,当一切都建基于大众后现代氛围中的狂欢意识和消费立场之上,它创造着繁荣,也创造着虚无。
传播媒介与社会环境,当然是理解网络诗歌得失的关键,但更需考量的是,此环境下社会集体心理的“利导”。社会心理学里,个人因团体压力的影响,在知觉、态度、判断与行为上表现出与团体内大多数人一致的现象叫作从众。准确地说,网络诗歌低贱化写作的泛滥,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传播媒介、社会环境、娱乐功能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相互传导,相互影响,最终在模范与传染中形成了集体的从众心理。
也就是说,网络诗歌写作必然服从于这一原理。对于娱乐功能巨大,跟风、媚俗、浅薄最容易吸引眼球的网络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从众提供相应的内容,这就实际上形成了某种逆向淘汰——在缺乏明确共识和评价标准的写作环境里,无论是新诗还是古典诗写作,下里巴人大获成功,阳春白雪无人问津成为必然。如此循环反复,诗歌品质伊于胡底。
失却品质,一切繁荣沦为表象,更回避了诗歌根本的挑战——在文化全球化与中国诗歌文化语境的重塑中,告别精英化写作与口语化写作以邻为壑的旧格局,汉语诗歌如何找到重新对接时代、对应现实的大门。
诗歌失去理想,就成为无主的孤魂,在一个没有边界也缺乏共识的网络诗歌环境里,创作上的随意性和投机性必然无限膨胀。网络诗歌由此加速堕落为一个“热而乱”、“文字卡拉OK”、低贱化写作泛滥的江湖。
到哪里去:未来还待“下回分解”
网络诗歌到了十字路口——无论创作者还是读者都能感受到这种杂乱、令人焦虑的状态,各方也充满了突破的紧迫感。但如何突破、怎样变革的新路径,却在争论中愈发错乱。而如果我们耳边依然只有私语、游戏与争吵,未来从何而来?
网络诗歌的无处容身源自诗歌整体命运的漂泊,网络诗歌的繁荣与虚火成为当下诗歌命运的无双写照,它的探索与迷茫是汉语诗歌写作在现代化十字路口迷惑中的一部分,而对它的难以评价又源于当下诗歌混乱评价体系下整体的无法评价。
冲突与迷茫背后,是各界对于网络诗歌的身份认同忧虑。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诗歌是继承了中国诗歌争论绝对化的倾向——不是认为网络诗歌代表着未来,可以一揽子解决当代诗歌发展中的困境,就是根据网络诗歌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一竿子打翻,认为网络诗歌就是当代诗歌庸俗粗鄙化的罪魁,却很少把网络诗歌问题理性化。没有考虑到在汉语诗歌整体历史演进的框架下,诗歌从来就呈现出包容多元的样态,从来在吸收与融合中前进,不会在封闭与山头中发展。
当网络诗歌和诗坛的混乱无序已经纤毫毕现,最初的判断却依然成立——网络诗歌就是汉语诗歌的未来。
经过种种纷扰,新传播时代的未来正日益清晰,而网络诗歌正是新传播时代下的蛋。当诗歌写作的舞台开放给普通网民,当诗歌不再仅仅是权力、精英和商业恃宠撒娇的宠物,而是让所有人开口也面向所有人说话,诗歌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诗歌价值体系的重建,其“超文本”形式的新发展,尤其是借助多媒体技术,网络诗歌融合音乐、动画、色彩于一身,终将带来新的革命。
网络诗歌为汉语诗歌的未来打开一种可能性。如果不改变网络诗歌当下的发展模式,不建立网络诗歌与主流诗歌更加协调平衡的发展格局,等待我们的,只会是网络诗歌一次次山寨狂欢和劣质化,可能将停留于可能。由此判断,便需要切实的推进,诗歌习惯“仰望星空”,但如今更需要脚踏实地,而通过解决问题,或可以逐步找到新路。
倘若我们确认变化的迫切性,而且意识到不可阻遏的新媒体浪潮的到来,那么首要挑战就是如何使诗歌的现实性再度生长起来,无论选择任何载体,诗歌的本质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映照,记录并反映现实生活,才是抵制网络信息沙尘暴的最佳方式。我们还需亟盼的是冷静的力量,如果说初生的岁月里网络诗歌展现着它炽热狂放的一面,那么现在它需要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季节,需要将泡沫挤出,在多元理性中转向提升网络诗歌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和思想内涵的下一段旅程。
而真正的悖论与挑战在于:网络诗歌成于网络,但今天它在文本创作、交流论辩、创作心态、文本阅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却是网络化写作和网络诗歌文化异化的结果。而语言探索的停滞与江湖格局的固化,又进一步导致了网络诗歌的低俗化与污名化。因此网络诗歌突破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抵制网络写作负面效应,不仅要告别回车键文字和快餐诗运动,同时也要求以新的价值动向和价值系统修补低贱化写作裂痕。一句话,网络诗歌必须超越网络化写作的禁锢。
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现实中去求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公民写作的大路上,网络诗歌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我们并不指望种种的问题和矛盾瞬间解决,乃至拿出路线图。当下最重要的,是搭建传统诗歌和网络诗歌对话的平台,有了理性的争论,才会有真正的共识;有共识,才有未来。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网络诗歌不可避免地仍将经受质疑与考验。但对未来的信心也正源于此——希望总藏在对过去和未来的困惑之中。虽然前路忐忑,道路艰辛,但网络诗歌已是这个时代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时间给出答案。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