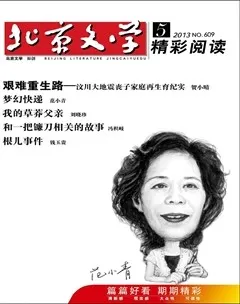放牛小子
人这辈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哪儿等得了三十年呀!
早年,我们村那帮放牛小子,都在八、九、十来岁的年龄,齐刷儿的,身背结实,虎头虎脑。除了睡觉,他们从不在家里呆上一会儿,跟上了弦似的,一个比一个淘,一个赛一个野。生吃蝎子,活吞蚂蚱,山梁追狍子,岩洞逗狼崽儿,上天入地无所不做。几年过去,他们晃成了半大小子,心急的老家儿,开始给他们张罗婆娘了。突然一个惊雷,山村变了,香果树竟开出了秋花儿,乡亲们惊讶。紧接着,这些放牛小子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折。如今,他们都混得人五人六儿的,在都市里度过的时光,早已超出在黄土地上走过的年轮。
别看这群放牛小子个个儿邋邋遢遢,没上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七扭八歪,缺胳膊短腿儿,但他们的后半生都很体面,很荣光,很不得了。他们着实混得不错,彻底脱了胎,换了骨。要是看那时的他们,谁也不会把他们往大出息里想。其实他们从骨子里就没想有大出息,按当时农村的追求,能娶上个媳妇,哪怕是口外的,生他几个带把儿的小崽儿,给祖宗将烟火旺盛地延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了不起的事了。也许这些放牛小子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累,遭了无数罪,于是,老天爷突然改变了对他们的待遇,开始偏爱他们,疼爱他们,眷顾他们。但让人不理解的是,还有很多和他们年龄一样大的孩子也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同样也是放过牛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他们那样的好命运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郊农村,农事的运营基本维系着原始的生产状态,田野里那些拉车、耕地、播种的活茬儿,主要依靠生产队里的那些大牲畜。架子硕大的黄牛首当第一生产力,因为它们的力气恒久、性格憨耐,按庄家人的说法,它们出活儿。牛们通常是白天耕作,夜间吃草。不是它们非想要夜间吃草,这样做是为了腾出白天的时间,好最大限度地多耕地,提高耕作效能。于是,必须调整黄牛们的进食时间和进食习惯,还必须在夜里有放养它们和伺候它们的人,以确保它们在静谧的夜晚吃好、吃饱,休息好、调整好,以便第二天耕地或是播种时有足够的劲头儿去撞套拉犁。
夜间放牛,顾名思义,我们那个村子称为“放夜牛”。起初,这项活茬儿通常是大人们的事,因为在夜晚牛群很兴奋,很拗犟,它们比白天更善于游走,不时蹿到阴森深冷的地方或是走进坟圈子里吃草。也许那些地方的草长得高深茂密、味道鲜美。但那些沟沟坎坎,旮旮旯旯,毕竟是让人感到特别不舒服和不自在的地方。再遇上忽隐忽现、明明暗暗的磷火,或是撩起个奔跑的旋风,那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漆黑的夜间,野地里各种大小精灵你来我往,异常兴奋,它们倾巢出动,嬉戏打闹,寻欢觅食。它们的眼睛闪着红光或绿光,让人心里不免惊惊诧诧的。这时被蝎子蜇一下,蛇咬一口,也是常遇到的事。所以,放夜牛这活儿女人们显然不可以胜任,当家的老爷们儿谁舍得呀!哪有这么不疼女人的人!因此也只有那些大男人包了这项艰巨而又有点恐惧的活茬儿。
说来男人们的胆子相对还是大的,甭说坟圈里的老坟了,就是刚下葬的,周围尚存着歪扭的花圈还没几天的新坟,居然也敢在坟头上坐一坐、靠一靠,困急了,还兴许睡上个觉。男人们遇到任何情况都能泰然处之,又富于经验,知道哪座山哪道梁哪条沟的草好。后来有的大人因白天下地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儿,夜晚瞪着俩眼放夜牛,身体慢慢就有些吃不消了。这时有的人就把家里的孩子带出来,让他们跟着夜晚看看牛,轰轰牛,自己也好趁机找个地方能多睡上一会儿。大人们渐渐发现小孩子放夜牛还真行,在他们睡觉的情况下,照样能胜任放牛的行当,每头牛的肚子都吃得滚圆,这让大人们很欣慰。别看是小孩子,但胆子可比女人大多了,看来小子就是小子。实践证明,这些孩子放夜牛是合格的,称职的。为了寻找草好的地方,他们居然能从容地穿越坟地,甚至敢在坟头上撒尿,拍着胸脯向大人炫耀:“我什么也不怕!”这些孩子为了省电,手中的“电棒”从不轻易开一下,除了眼前蹿出来一只野物,才照一下它们到底是什么精灵。“人家的孩子能放夜牛,咱家的孩子怎么就不能?”又有男人在动员老婆。于是,经过各家的“妈”的同意,就有了更多家庭的孩子肩负起了放夜牛的使命。他们夜间不睡觉也照样精神,更重要的是能让牲畜们吃得饱饱的。就这样,经过一季的见习,夜间放牛的任务后来就慢慢交给小孩子们了。那时他们虽然都缺嘴,个头精瘦,但精神头却十足,可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他们表现得似乎很富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手持皮鞭,但很少抽打牲畜们,对牛群里的每一头牛都悉心照顾,也很上心、很关心,发现不爱吃草的牛,就赶紧报告大人,以及时采取措施。
这些放牛娃在那个艰苦的岁月,能够超常地适应各种生存环境。他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用大人逼着,愿意为家里或生产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小孩子也非常不容易。他们在放牛的过程中,经常被蚊虫叮咬,马蜂蜇,风吹雨淋,日晒寒袭,还总饿着肚子和牲畜们在原野一同撒欢儿。他们乐观向上,不愁不怨,是一群憨厚朴实的非常踏实的地地道道的大山的儿子。
他们从十几岁起就放牛,一直放到他们的身体隆起了结实的肌肉,浑身疙疙瘩瘩的。他们习惯称身上的肌肉为“小鸡蛋”或“腱子肉”,他们真的就像牛群里一头头健壮的牛犊子,好像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这些半大小子,别看胡子还没长全,可时常和大人过招比试摔跤,在他们眼里他们早已经是庄稼汉了,所有的农活,都不在话下。
后来,正值城里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也面临着一场命运的大转折。这样的转折,来得突然,来得意外,来得惊喜。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一项特殊的政策,如同春风一样拂面而至,这项让他们激动得折跟头、打把式、放鞭炮的政策,着实改变了他们的一切。他们开始不是他们了。这些放牛小子扔下鞭子,离开农村,奔赴城市,这种鲜明的对流,就好像是城乡青年大换防。城里的知青一夜间变成了农民,农村的放牛小子转眼间就变成了城里户口的居民,端上了被所有人羡慕的“铁饭碗”。这是梦寐以求的喜事,他们端详着手中的“铁饭碗”,乐由心生,无限喜悦。因为它不怕磕,不怕碰,甚至不怕摔,里边总盛着香喷喷的取之不竭的美食。
他们从此离开了大山,离开了滋养他们的那块土地;他们从此拥有了城市主人的资格,彻底摘掉了农民的帽子。这带给他们的一系列的变化,完全是得益于当时在农村盛行好几年的“招工”政策。这个政策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和赞许,因为招工对象只是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孩子,中农出身都沾不到边。不管这些孩子干什么,上没上学,念没念书,识不识字,只要胳膊腿健全,身体强壮,就可享受到这样的政策。于是,在原野奔跑打闹了好多年的放牛小子,便个个都赶上了机会。他们第一次走进理发馆和洗澡堂,理了发,洗过澡,脱去草鞋,换上皮鞋,风光地来到城市里的国营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上班,从此告别了黄土,吃上了皇粮。
“招工”是早年国家针对农村青年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了划时代的福音。他们适龄的儿孙,只要符合“根红苗正”这一铁定的标准,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成为被“招工”的对象。这批没有,下批可以轮到;这拨没赶上,下拨还有希望。只要政策在,心就踏实。这项积德的政策持续了好多年,可以说,所有够招工条件的贫下中农的孩子,在政策有效期的那些年,几乎全都赶上了。那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也渴望被招去当工人。他们心想,出身不好,这没法和贫下中农的孩子比,可好单位轮不到,次单位也可以呀。只要能出去,能当一名城里的职工,能端上“铁饭碗”,哪怕是看大门儿的、打扫卫生的、掏厕所背大粪的,甚至扛包卖苦力,也愿意去。可他们根本没弄明白,他们从祖宗那儿,就不在政策享受的范围,学习再好,身体再好,一切都好,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那也不行。这是原则、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为这,村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一度苦恼过、苦闷过、压抑过,想不开。每次看到一批又一批被招走的出身好的青年,他们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他们祈盼着,招工的政策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头上啊!同样的年龄,怎么家庭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相差这么大呢!为此,他们埋怨过他们的父母。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们的父母,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就因为出身,把孩子的后半生都耽误了,甭说招工了,媳妇都不容易娶到,一身的臭味儿,谁跟呀!
数了数,我们那个村就有十几个放牛小子被招走。至于全公社、全县就更多了。这些曾经的放牛小子所去的地方,按当时的说法,都是天堂般的好单位,有领导关心,有师傅爱护,有同事们的关照。这应该说也是他们所在村庄的骄傲,是祖辈上的骄傲,是农民的骄傲,归根到底他们要感谢“根红苗正”,就是这一条,使这些孩子,获得了一个超级圆满的归宿。
命运让这些农村的放牛小子端上了“铁饭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利益。他们所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国家和首都北京的大机关、大企业、大厂矿,有的还被招进科研院所,并享受着丰厚的福利和劳保。
当他们得知就要离开家乡,就要去那么好的地方,由土小子变成城市职工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认为是天上掉下了大馅饼,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是在梦里。因为他们初中都没毕业,甚至小学也没上完,只是拿着鞭子放了若干年牛的农民后代,写自己的名字有时都要想一想,不是大白字就是笔画残缺,怎么就突然轮到了如此的好事美事乐事呢?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被招工的人也多了,他们突然醒悟了,认为这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呀,根红苗正,不优先考虑我们考虑谁?我们是有绝对的资格和条件享受这样政策的,这政策就是为我们定的。他们的确是太幸运了,他们应该感谢那个年代,他们更应感谢他们的父母,不早不晚偏偏把他们生在了那个多福的时刻,那个多福的年代,让他们碰上了那么好的运气,让他们永远结束了放牛小子的生涯,走上了即体面又荣光的、被人羡慕得五体投地的工作岗位。
这些放牛小子大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村,年龄相仿,上下差个一两岁、两三岁。我想他们也渴望出人头地,想做有大出息有大作为有大才华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赶上用知识造就他们的年代。也不要说他们不学习,不好好学习,是那时不太讲学习。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小字报,他们不想背上反动的名声,所以就没拿学习太当回事。假如要是眼下,这些放牛娃说不定都是科学种田的能手,或是农业科技的带头人,至少能让自家的菜园、果园通过科技管理,科技投入,增加家庭收入。在大搞运动的那些年里,学校经常停课,学生在课堂上也经UyhRrfWwKPYEt4hUDyIwPjb7dWYp08ITTNAJeijESHk=常打闹,淘气的学生还在教室甚至课桌上板凳上大便小便。记得升班好像都用不着考试。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索性就不在学校耽误工夫了,不同程度地肩负起了各种农活或生产队放牛的行当。其实,说他们是放牛小子,可不光放牛,还放马、放驴、放猪、放羊、放鸭……还去做所有能做的一切农活。
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民的孩子也一样早早当起了家。他们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打草、割柴、担水、劈柴,这样的活计都要去做,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尽全力为他们的父母分担家务。在做家务和农活上,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区别,他们都很能干,都很勤劳。但是他们中间有个东西在鲜明地隔着他们,区别着他们,就是他们对出身的解读和感受有着强烈反差。
应该说这是一群本质非常好的孩子,是非常勇敢和勤劳的孩子,他们敢于吃苦,敢于挑战艰难的环境,有很强的韧劲。他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十几岁的孩子,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家里,都能当一个劳动力使。在大人们的熏陶和影响下,他们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农活儿,特别是放牲口这活儿,很适合他们的天性,孩子们都格外喜欢。也许当时没有什么玩儿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舞弄鞭子,自己做,自己拧。他们走进空旷的原野,抡圆了,甩几下,啪、啪,听着清脆的鞭声,特开心,特惬意。由于长期在农村磨炼,他们每个人都能轻松驾驭几十头大牲畜或上百头小牲畜,整天游荡在七沟八梁。他们不管多烈、多暴、多难调教的牛马驴骡,都能降服它们。他们是牛仔,是中国农村的牛仔。他们放什么牲口,就骑什么牲口,绝不轻易放过它们。调教牲口是他们认为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因为男子汉的勇猛很多都体现在与刚烈任性的牲畜的较量上。他们有的还模仿马背民族的勇士的样子,在长长的榆木杆儿上,拴个绳套,当作“套马杆”,不过不光套马,也去套牛、套驴。这些孩子在往返放牧的崎岖山路上,总是骑在牲畜的背上挥着鞭子驱赶着它们奔跑,他们仿佛真的成了马背民族的后代,透着果敢和刚毅,表现得异常勇敢。有时候,他们骑着驴或牛从山顶上往山下冲,这确实需要一种超常的勇气和技艺。那些牲畜在他们的呵斥下,个个都变得老实服帖。孩子们骑在牲畜的背上,让它们跑就跑起来,让它们走就慢下来,让它们站住就会停下来。这些放牛小子有了多年艰苦的摔打和历练,进城后表现得也异常突出,别看字认得不多,但他们也具有很多长处,他们勤快、低调、卑微、老实、本分、仗义、尊重师傅,这些都是他们身上的优点,这为今后更好地融入他们所在的集体,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
由于他们具备的优点,不管是车间主任,还是单位领导,都很喜欢他们的实在劲。经过长期考验,有很多人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重视,从事着单位很重要的工作岗位。特别是他们善于助人的精神,使那些城里人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心存好感。更可喜的是,由于他们所具备的优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得到了城里女孩子的赏识和喜欢。几年过后,我们村那些曾经的放牛娃,都在城里处了对象,有的是纯正的京城姑娘,有的是家在农村但本人是在城里工作的。他们相继将在城里搞的对象带回了家。当他们走进村庄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极希望乡亲们都站在街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他们心仪的人被带回家了。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和乡亲们多搭一会儿讪,故意延长心上人在街头停留的时间。这些“放牛娃”心里很美,更是自豪,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一个曾经放牛的孩子,今天居然能带回来一位城里的姑娘,这是多么风光、让人心花怒放的事情。
真是“人挪活”,这些曾经的放牛小子,离开了小天地,见到了大世面,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奋起直追。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很多人居然读完了中专,又上大专。可想,就那样一个可怜的基础,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不知他们牺牲了多少时间才换来这样一个说得过去学历。经过在大城市多年多方面的熏染,后来他们个个都仪表堂堂,穿着入时,行为讲究,甚至还有几件名牌穿戴。他们变得谈吐高雅,大部分人已是京腔十足,举止颇为入时。但他们骨子里依然是农民,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十分自信,回到村里那个样子似乎很难拿。还像原来在村里时的样子吧,显然不行,怕街坊四邻笑话。如果学城里人的样子,不到位不说,怕乡亲们接受不了。总之很难把握,这是让他们回村感到非常为难的事情。所以村里人说他们有些不土不洋,甚至有的人表现得还很酸,这是乡亲们最看不惯的地方。他们中的有的人,好像记不起乡音,说不好老家的土话了,也许怕给大城市丢脸,也许怕城里的老婆笑话,也许怕他们的孩子听了会反感。在家和父母唠嗑也拿腔拿调,老爸老妈不习惯也得听着,还要装得爱听,不然一旦让他们感觉出来,他们就会很长时间不回来,任性的春节都不回来看老爹老妈一眼。这些曾经的放牛娃,他们似乎对生养他们的村庄有些淡忘,更从来不提及放牛时的那段记忆。
其实,那段放牛的记忆,才是真正的原生态的记忆,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多数人都希望他们这样想,包括他们的父母。但对那段记忆,他们每个人的感受也许不同,他们毕竟离开故土的时间太长太远了。由于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了他们一生中很多地方的改变,他们和他们在老家的兄弟姐妹们已没有了更多的交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很高贵,可谓居高临下,和他们交流相当于和农民交流,所以小时候兄弟姐妹们之间的那种默契,已经很淡很淡了。如果要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里,这种情况恐怕不会那么不自信。所以,当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后,与在家的兄弟姐妹的接触,只是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态度来掩饰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的虚伪。
眼下,那些曾经的放牛小子都已是近60岁的人了,自然多数都做了爷爷或姥爷。几十年过去了,想想他们孩子的身上,已经完全找不见一点农民的影子了,他们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学在城里。这些放牛小子的后代或隔辈人就更不知道农村和农民了,至于放牛小子的故事听也没听过,其实这些故事就在他们身边。而这些爷爷或姥爷只得把那段经历作为秘密,埋藏在心底,对谁也不会透露,这也许有他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