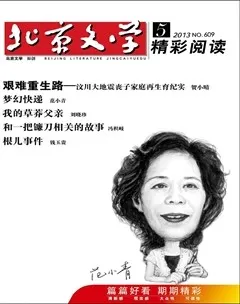透过家庭铁幕看一个母亲的逆性归途(点评)
这是一个被“现实”的“寒冷”合围窒息而死的故事。这里的“现实”只有清算,只有永无归期的沉沦,没有灵魂的接纳、宽容和抚慰。所谓的“现实”,主要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并已成为我们当下处境的历史与文化。主人公孙美英即死于一种历史一种文化,死于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当然这里也有人的自私、贪婪、阴暗和个性上的冷漠与麻木。
问题是年轻的主人公孙美英实在无法忍受。她不甘就此“湮灭”。她不能忍受历史文化中的这种“原始范例”对她的日夜制造。于是她选择了逃匿和流浪。“迫于生计”她做了一只“流浪鸡”——一做就是16年。“她把做‘鸡’挣来的钱大把大把地寄给两个儿子”,让他们读书、成长、成材。自己“手里也积攒了一笔积蓄”,然后就打算“洗手”,回家,帮助两个儿子建房结婚生子,巩固后方,建立安乐窝,“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她的一个梦。然而,破灭了。梦的破灭在金钱破灭之后。文化的破灭便露出了它内里的牙齿和残酷性。
当孙美英帮儿子建房结婚生子几部曲按计划完成后,她的爱也从遥远的梦乡回到了当下,从16年的时距回到了儿子们的生活现场,她零距离地接触、观摩、关爱、抚慰、抚摸、吮吸,她极尽所能洗涤历史的“污垢”,洗涤自己的“罪孽”,她试图缝合生活的破碎,她竭尽全力重建梦乡里企及的生活和家园。甚至将自己用来养老的最后的钱(4万现金)从“小姨”那里一分不留地“提取”、拿出,给了两个不肖儿子的家庭输“血”。
然而,她儿子说:“我恨你……我们习惯了没有妈的日子……”
无疑,这是一声惊雷。因为孙美英当场就“惊呆了”。这是小说最精彩最深刻最核心的一笔,有如文眼,朗照全篇。
试问,在这个现实,她有救赎自己的上苍,有可以告慰的诸神,有魂灵最后的归处吗?
这个小说虽系处女作,但起点是高的。它具有一般初涉小说这一虚构文本所没有的纵深感。我之肯定,也正是它的深刻性所在。首先,它指出孙美英纵然做了妓女,但毕竟是母亲。所以她具有一种天下母亲同样敢为儿女下地狱,甘愿遁入黑暗或沉入腐朽的、超功利而毋庸回报的母爱,甚而有过之无不及。其次,它昭明孙美英是强烈地渴望忏悔渴望赎罪(如果做“鸡”也算是一种“罪”的话)的。因为在她的体内也有文化的积沉,有“整体居民”必须遵从的贞洁观。虽然逃离,但并没有逃脱。一种“不知其所在又无处不在……充斥于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原型政治”(福柯语)统摄着她。她希望“化”掉那些脏钱来雪洗自己,构筑一个母亲的新形象,从而使自己从16年的“空旷”中回来,但是“现实”不让不允许不接纳不宽容。第三,小说批判了文化的伪善和劣根性。在中国的文化中存在着某种先天的钙质匮乏(和奴性综合征)的不足基因,并不够博大和宽容,从它的紧口“瓶”中“蒸馏”的那些所谓“精华”来看,存在着某种最不人道的原罪的东西。
小说十分悲凉地揭示了一个家庭的铁幕:儿子伏击并“强奸”了自己的母亲,同时,儿子还是尾随母亲的潜在的屠手,正是这个做儿子的代为吹灭了一个离世之人心中的那盏灯,而不是点亮。从而使一个被现实“粉碎”的亡灵,带着遗恨、带着周身的寒冷,踏上了黑暗旅途,永无归期,没有“故乡”,只有永远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