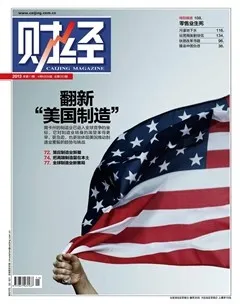“人民外交”的虚像与真实
2001年8月13日,竞选时承诺参拜靖国神社的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警告,断然践约。从此,中日关系进入长达六年的“靖国冰川期”:一方不厌其烦地提出严正交涉,一方在众目睽睽之下每年冲锋参拜。直到2006年10月“小泉后”的安倍晋三首相以“参拜与否就是不说”为妥协展开“破冰之旅”,中日关系才从“抗议疲劳症”解脱出来。
如何理解安倍带来的“柳暗花明”?中国学者强调:“体现了日本主流民意”,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这反映了中国对日外交传统的“人民”意识形态想象。
早在“靖国冰川期”初始, 2002年就有学术刊物发表回顾历史的文章《民间外交功德无量》,肯定民间外交仍旧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和保障”。此后,《人民日报》也不断刊文倡导“民间友好”,认为:中日关系有着“以民促官”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优良传统,小泉的倒行逆施要靠“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来“突破”,并“形成世代友好的形势”。终于,中国方面于2006年3月特邀日本民间友好团体访华,强调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而在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相信民间团体“将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与半年之后的“破冰之旅”联系起来,似乎真的上演了“以民促官”的“友好大团圆”。
但同样的逻辑在当今安倍二次政权下遭受重创。他接过前任留下的“钓鱼岛危机”,却打掉了期待他再次“破冰”的幻想,把对华政策推到日美制定“共同作战计划”的军事化悬崖。而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有80%嫌恶中国,安倍的支持率则高达70%。中国的“人民”日本论哑然失语。
“人民外交”曾经“以民促官”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吗?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了“人民外交决定论”的虚构性。没有解构这种历史神话的知识努力,就不能重建对日外交。
“这一条路是走不通了”
“你和蒋介石、美国站在一起,很好,就按你的办法,你还不同意吗?!”1959年3月18日下午,一路南下调查处理“大跃进”混乱的毛泽东,在武汉抽空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起僵持一年的中日“经济绝交”,又斥责起来。
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急忙迎合道:“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就是远交近攻。”他最后又表示,两国关系中断了,只能依靠国民外交来往,回国后自己要促使政府改变政策。
这里所谓两国关系,是指“人民间”的交流。美国控制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与台湾蒋介石政府议和,但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同情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开来”的原则指导对日工作,通过签订贸易协议、协助日侨回国、宽大处理战犯建立起“人民外交”关系,并冀此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发展到“半官方外交”,再实现邦交正常化。
然而,上述日本利益以民间形式解决以后,日本政府便不再释放可能谈判邦交的空气,中国政府仍争取互设商务代表机构。1958年3月5日,双方贸易团体签署新协定,其中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商务代表机构可以悬挂国旗、使用密码电报、入境不按指纹,等于承认半官方地位。
但日本政府在美国、台湾的压力下公开否认悬挂国旗,中国方面表示严词抗议。僵持之中,5月2日,一名日本“暴徒”在长崎的展览会场扯下悬挂的五星红旗,日本政府未追究“罪犯”。这是继两个月前拒绝向强掳劳工刘连仁谢罪和赔偿的侮辱性事件之后再起风波。5月9日,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政府“侮辱”“敌视”中国人民,预言其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随后,中国切断与日本的交流。这导致一些日本企业失去原料和市场,社会党便于1959年3月访华,试探重开贸易。但毛泽东答以不会断绝“一万年”,客主无欢可叙而散。
与毛泽东谴责日本相对照,周恩来更多作自我反省。他在3月15日会见浅沼时表示:我们已经得到教训,“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是走不通了。”“应该在两国政府之间做的事情,还是需要政府与政府之间来做。”这是拒绝客人,也提出了重建外交的新思路。
牵强附会的“半官半民”
周恩来反省“以民促官”之路“走不通”是符合实际的。
日本主张中日友好的在野党、民间团体居于少数,不能决定外交政策。但他们与中国交往,促成了日本政府也希望的贸易利益和日侨、战犯回国;日本政府因此不必付出对华友好而招致美国压力的政治代价,其侮辱、敌视中国的言行有增无减。
至于“日本人民”,他们担心中日贸易、日侨和战犯归国受阻才对政府施压,而既然中国予以解决,也就不必急切地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所以,中国切断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关系,以促使日本政府反省和“日本人民”向政府施压。
不幸的是时机错了。
如果在日本方面提出利益要求之初,中国断然主张政府间谈判,日本也就难以回避。在“日本人民”与中国交涉解决了最为揪心的日侨、战犯回国问题之后,日本政府就有足够的耐心“静观”中国暴怒,并唱起“政经分离”的高调。
尤其失去体面的是中国恰在此时陷入“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且既被美国封锁又开始与苏联对抗。普通百姓饥寒交迫,国家急需从日本进口化肥、农药、机械以恢复发展生产,与日本的“经济绝交”难以持续。因此,随着“日本人民”要求重开贸易,中国不仅恢复了“友好贸易”,而且与大资本、垄断资本也签订了长期综合贸易协议,甚至在约定不享受外交特权、不挂国旗、不使用密码电报的条件下,互设贸易联络机构。
上世纪60年代初确立的这种对日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经济急需,但在外交意义上则捉襟见肘:切断贸易之初,中国一再驳斥“政经分离”是“欺人太甚”的“侮辱”,不能容忍日本既敌视中国又“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岂料遇到经济危机,便不顾日本政府继续敌视中国的态度而恢复贸易,全盘接受曾经拒绝的互设商务代表机构条件,难免被视为自食前言、唾面自干。
当时,前来交涉的日方代表察觉到中国“渴望着”与日本通商,就坚决贯彻“政经分离”。这样,种族主义“落后中国观”和殖民主义“市场中国观”必然复活。
不根据周恩来“此路不通”的自省精神反思内政失败累及外交失态的教训,而把上世纪60年代的中日贸易牵强附会为“半官半民”体制,虚构一套“人民外交”成功“以民促官”建立“半官方”关系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历史神话,这种夸大“人民外交”作用、捏造“以民促官”规律的思想,在“靖国冰川期”再次陷中国外交于被动。而在最近的“钓鱼岛危机”初起时,仍有“一小撮右翼分子的闹剧”“亟须扶正压邪”之类的“区别论”大行其道,受此迷惑的中国外交当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头绪。
“中国人民”缺位的对日外交
事实上,正如来华谈判建交的田中角荣首相当时所说:“尼克松访华的结果,我国已经处于不和中国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就不能维持政权的形势了。”即日本政府的决断并非缘于“以民促官”,而是因为美国转变了对华政策。而且从1970年3月的日本舆论调查来看,主张与中国建交者给出的理由,47%是担心“错过巨大市场”,31%是担心“落后于世界大势”,只有15%担心“战争不得结束”,经济主义动机压倒战争责任意识。这意味着对中国的蔑视。
为什么“人民外交”会造成日本的“蔑视中国观”?在“刘连仁事件”“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不久,著名学者南原繁就批评“我们日本人内心还残留着陈旧的中国观”。一些中日友好人士也发表反省声明,强调不应该“满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而应该在战争责任自觉的基础上“改造民族道德”。
所谓“满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是指中国的“人民外交”一味地迎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欲望,导致日本社会没有反省战争责任的机会而把“陈旧”的“蔑视中国观”延续下来。不了解国家间政治原理而一厢情愿地搞“友好”运动,这种国际关系的人情化想象在战后和解的意义上可谓适得其反。
尤其沉痛的是,历史上曾经有过避免这种“友好”偏向、唤醒日本战争责任意识的机会。
1950年,苏联把其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当时作为党外人士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认识到:斯大林此举可以提高中国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得到国际承认。
然而,后来实际的战犯侦讯、审判受制于中共中央的对日外交“人民友好”原则,目的在于宽大释放,其间不仅要求“思想不通”的工作干部“提高认识”,连起诉书、新闻报道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比如,新华社报道稿中被害人“控诉日本战犯的滔天罪行”、旁听者“流着眼泪在听被害人哭诉”等描述均被删去,而加上被告人的悔罪表现和辩护人“请求法庭从宽处理”之类的说明。可见,“人民外交”的政治性、党政包办性造成了中日关系利益、尊严的不平等,“中国人民”其实是缺席或不在场的。
“中国人民”缺位的对日外交既没有达到平等“友好”的目的,也不是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决定性动力。但对日外交话语受到“人民外交”之“以民促官”“区别论”等虚构的主宰,在今天仍然造成混乱,即政府外交不能有效地实现尊严、利益,则“人民”必愤然出场。比如,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僵局,政府外交无能为力,就诱发了抗议游行。而最近“钓鱼岛危机”所诱发的抗议更呈现新的特点,出现大规模的无政府暴力。
作者供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