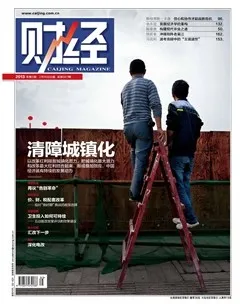府院动向
中央“一号文”新提法
最近几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九连增”,但同时,“谁来种地”的担忧日益渐起。因承接农产品供给、城镇化进程等相关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并没令人感到意外。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与此份文件制定相关的人士均指出,虽然一号文件每年提及的内容都差不多,但今年提及的“家庭农场”,有些新意。
按照相关文件起草者的思路,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单位,将成为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商品化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单位,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的受体。
为什么选择以这种形式作为经营主体创新的基础?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农忙季节缺人手、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的现象。
今后谁来种地?过去各地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大资本下乡租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但这一过程至今有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大资本下乡后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是个未知数;其次,在一些劳动力虽然出现短缺但基数仍大的地区,快速推进这种模式,将与仍在务农的农民产生矛盾。
这正是中农办陈锡文主任大力提倡家庭农场这一新概念的主要原因。“今后中国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到底是公司企业大规模经营、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场,还是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农民合作?我的看法是,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提高组织化行为,变得更强,一定能够种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期表示。
事实上,在中央层面将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由地方自发推进的家庭农场试验早已开展多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松江模式和吉林延边模式。
“松江模式”从2007年起开始实验,其主要特点是由当地区政府推动,采取以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的方式,将农民手中的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年底,全区耕地流转面积已占全区耕地面积的99.4%。其中,近一半的耕地流向家庭农场。到2012年6月底,总面积为604平方公里的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1173户。
这种模式对家庭农场的生产有一系列严格规定:农场主必须是本村组织中的成员;农场耕地必须用于粮食生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包;综合考虑吸纳当地劳动力、收入等相关因素后,当地政府将每个农场的基本规模定为80亩-150亩。
而为了保证家庭农场高效经营,松江区政府专门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其提供全程机械化订单作业服务。除此之外,松江区还成立了一系列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农资供应、农机、种子繁育基地、烘干设施等四大类。
曾对该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告诉《财经》记者:“以目前的经营水平来看,一个家庭农场可由夫妇两人经营,他们的年收入水平可达10万元左右。”
但需要指出,这种模式因地处上海,不少相关人士怀疑,上海雄厚的财力能做成的,其他地区不一定能做成。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根据。
据《财经》记者掌握的权威信息:2011年,松江区所有家庭农场获得的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约为2607万元,其中来自中央财政的占14%,来自上海市的占40%,来自松江区的占46%。财政补贴已经占到了家庭农场净收入的五分之三。
好在相对落后地区也有进行实验并取得成功的案例,延边模式即是其中之一。政府在这种模式中起到的作用依然不小,但主要和资金无关,因此其适用性可能相对较强。
延边模式的主要做法包括:允许在册的家庭农场获得由政府担保的土地他项权利担保贷款、信用担保贷款,农场获得的全部涉农贷款均由政府贴息60%,政府还补贴其投保土地承租费附加险等。
总之,当地政府出台上述这些做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的两大瓶颈性问题:其一,在农民家庭普遍既缺乏资本积累、又欠缺有效抵押物的前提下,如何找到稳定持续的融资模式及渠道,是家庭农场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及生产的基本前提;其二,家庭农场因为实力仍然较弱,相关农业保险应该及时开展并起到积极作用。
现在来看,支持家庭农场建设虽然已成为政策公司,但其能否快速得到推广,除了上述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之外,还有一些具体政策需要调整。比如,家庭农场目前无法在工商局注册,试点地区均为地方政府“特事特办”。此外,这个新组织是否可以享受免税、补贴、贷款抵押物种类放宽等一系列扶持。
2013年这一概念可能仍将处于继续试点状态,不会也无法大规模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