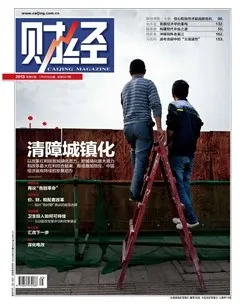构造综合通胀指标
在国民经济宏观运行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但从过去60年中央银行盯住CPI实施货币政策的成败经验看,单纯盯住CPI似乎有缺陷。由此,世界主要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有些“变革”:货币政策既要盯住物价,又要盯住资产价格。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也主要以CPI衡量。
然而,通胀不仅仅是狭义的CPI,而应该是广义的价格指数变化。如果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劳动力价格(工资)、CPI、房地产价格等综合成一个广义的通胀指数,或许货币政策更能够有的放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必须用强力措施去治理房地产价格了。西方货币政策的实践也是一边在应对以CPI为主要内容的通胀,一边兼顾资产价格。在技术层面,我们是否也可以与“国际接轨”?
CPI本身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它不完全代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笼统地说,就是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物价的普遍上升。经过实践中无数次的检验,CPI可以反映通货膨胀的统计学含义,其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过程中。
通货膨胀除了CPI所反映的还有很多其他内容,但绝不是要否决它,而是在关注它的同时,还要结合资产价格和要素价格。于是,让我们在解构CPI的基础上,也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PPIRM)等生产资料价格纳入视野,同时观察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代表资产价格的房价,争取从多个维度来描绘通货膨胀。
首先,分析一下CPI。国家统计局把CPI定义为反映城乡居民家庭购买并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
CPI具体分为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CPI构成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食品所占的权重。美国CPI的篮子里食品约占5%,中国是31.79%。近两年网络和主流媒体上有一系列很火的流行词,从“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糖高宗”,用不着图表,都知道食品价格对CPI的“贡献”有多大。
CPI的非食品类分为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七大项,合计权重约占三分之二。整体看,非食品类的同比变化是较为平稳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正负2%的区间内波动。
在CPI的非食品类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其一是非食品类中的许多分项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行政化定价因素,比如烟草、医疗、交通、教育等,粗略测算这些细项的合计权重很可能不低于三分之一,所以非食品类能表现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行政化定价的影响;其二是非食品类的居住只统计租金、水电费、装修材料、房贷利率等指标,且权重不高,所以通过CPI来了解住宅价格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偏差。
其次,看看PPI和PPIRM的通货膨胀含义。PPI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PPIRM反映工业企业为生产投入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
简单讲,对于一个企业或行业,PPI是收入,PPIRM是成本,利润就是两者的差值。从产业链角度出发,存在PPIRM向PPI传递,PPI向CPI传递的关系,即资源品通过上、中、下游行业一层层向个人消费品传导。但把这三项指标放在一起对比后可以看到,虽然趋势上方向一致,但三者之间传递效率却存在差异。PPIRM向PPI传递效果明显,但PPI向CPI传导效果相对较弱。
以2007年-2008年国际输入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明显压力为例,该时期内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能源类商品持续飙升。根据上面提到的传递关系,石油价格上涨会顺着油气开采业、化工制造业、纺织业一路传导至CPI非食品类中的衣着项目,但实际情况是这段时间的衣着项目同比始终为负值。
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下游企业成本转嫁的能力不一样,像主力石化企业多为垄断国企,议价能力毋庸置疑,于是资源价格的上涨可以非常通畅地传递下去。但到了纺织业,由于产能过剩和高度强化的竞争环境,成本转嫁的能力大幅弱化,于是价格传导被阻挡于末端之前。影响价格传递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定价。
因此,发源于原材料、燃料及动力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受到的买、卖方市场特点以及行政化管制的影响是无法由CPI完全反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构造综合通货膨胀指标时应把PPI和PPIRM收纳进来的原因。
再次,探究一下工资水平。2011年珠三角工人工资实际上涨幅逾30%,普通工人工资达到近3000元,比该区域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深圳要高出1倍以上。
原材料、物价、房价的上涨,劳动力供给趋紧和农民工对生活品质的提升,都是推高工资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在工资水平和通胀水平双双走高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关注 “工资通胀”说,对工资和通胀螺旋式上涨的担忧渐起。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增长率和产品价格增长率之和。若是工资上涨的速度与人均名义GDP基本同步,工资增长并不会对通胀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工资和物价之间存在的螺旋式互动,着眼点在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是事实,可这正反映了市场对产品实打实的需求,而成本正是需求的表达形式。若是不存在超额的需求,何必提高成本来满足需求呢?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对生产成本的攀升叫苦不迭,深层次的原因是其中的部分企业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计可施。
所以,不必纠结于名义工资上涨是否直接导致了通胀的加剧,而是应把它作为一项能够更全面考量通胀增长率的一个因子,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无法适应人工成本上涨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被淘汰,企业将通过技术升级提升生产和管理效率,企业并购的步伐也会被推动,这符合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因此,把工资水平纳入通胀综合指标是适当的。
最后,看看住宅价格。国家统计局在计算CPI时,并没有把住宅价格纳入其中。住宅可以算做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品。住宅价格虽然没有直接计入CPI,但是它的上升会从需求压力和成本推动两个方面影响CPI。
房价的上涨激发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热情,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大概在四分之一。从需求上看,在我国城市化推进且仍存在一定人口红利因素的大环境下,存在大量的住宅刚性需求,房价上涨会迫使需要买房的家庭增加储蓄,本可用于消费的收入被挤压,造成了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于是投资和消费间的不平衡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成本角度看,房价上涨带动房租提高,给企业经营成本增加负担,激发了职工加薪的要求,方方面面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剧。
通过对比新建住宅价格和CPI中的居住类项目,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月同比始终高于CPI居住类项目;第二点是新建住宅价格的变化相对CPI居住类项目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领先性。
2007年7月到2008年8月,在这段非食品类同比出现趋势性上行的时期里,居住类项目与其基本同步,但新建住宅价格的行情在2007年3月已告确立,而同比涨幅下行的通道则开启于2008年2月,比CPI的反应提前了半年左右。因此,把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纳入通货膨胀综合指标内,不但可以揭示CPI无法反映的波动幅度,也可以改进CPI同比数据滞后的缺点。
以上通过分析与实体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四大价格指数,可以看到通货膨胀、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是互动的,也是轮动的。由此,通货膨胀不能仅仅指狭义的CPI指数,还应该有广义的概念。进一步也可推论,货币政策针对的通货膨胀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
对于“狭义通货膨胀”的CPI,仅凭它不足以掌握通货膨胀的程度,如生产资料价格向下传导时受到的阻塞、我国特殊的行政化定价机制、工资水平的长期结构性效应以及资产价格变化的剧烈程度。而将生产资料 (PPI及 PPIRM)、生产要素 (工资)、资产价格 (住宅)等数据与CPI相结合从而构造出一个广义的“综合通货膨胀指标”,应该具备一定的实际意义。
2006年到2010年,综合通胀指标与CPI的变化趋势大体上相同,但整体水平明显偏高。较为明显的偏差发生在2010年,该期间生产资料、住宅价格和工资水平的涨幅要明显超出CPI的上涨幅度。这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货币超发的结果,而狭义CPI不好衡量,但广义通货膨胀却能很好地显现。
货币主义的“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的论断仍在绕梁,以上分析仅提供了一个注脚:货币渗透到了广义价格中,货币政策具有广义中的兼顾属性。
作者为光大银行副行长,本文节选自其新著《金融论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