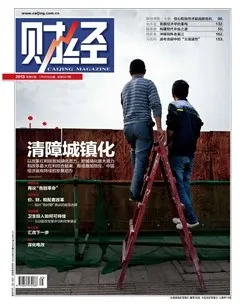波考克眼中的“王道盛世”
波考克(J.G.A.Pocock,1924-)这个人近年来在政治学界名头很大,但在中国读者并不多,除了几篇文章之外,他的著作多年未见译成中文,这与同属“剑桥学派”、已有五种著作汉译本的斯金纳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的东西一向以难读著称。过去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研讨班授课时,不少年轻学子便抱怨他的东西让人看不太懂,不久前与李强和刘北成两位教授小聚时,席间也曾说起,很多学子都感叹波氏那本《马基雅维里时刻》实在难啃。
钟情波考克
我近年所译的东西中,便有两本波考克,一本是“难啃”的《马基雅维里时刻》,目前仍在出版社的编辑过程中,估计不久就会面市,另一本便是下面要讲的《德行、商业和历史》,去年秋天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波考克为何难读?用斯金纳的话说,他虽然治史,却是史家中理论思维最严重的。
麻烦在于,他的理论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各种主义或思想体系,而是另有所宗;他用来贯穿海量史料的手段,不是自由和权利一类寻常的现代政治概念,而是搞政治学的人十分陌生的一些语汇,你不事先搞清楚它们的含义,读他的书会觉得满纸不知所云。
但是波考克的价值也许正系于此。他要绕开后人归纳出的那些理论概念,带我们返回历史语境的细节之中。平常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常会有一种体验,特定环境下的语气眼神,往往能比语言传递出更多的信息,政治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政治固然离不开观念,便它们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得到阐述的,与人们当时的利害思考、愿望和困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或扭曲着它们在使用中的含义。
为波考克奠定政治思想史大师地位的煌煌巨著《马基雅维里时刻》有一个副标题:“佛罗伦萨政治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所以他也常被人误解为共和主义者。诚然,他在书中构筑了一个以英美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将洛克等人的权利学说边缘化,这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演进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引来论者蜂拥,但也易于让人忽略他研究的另一面。
其实波考克有更大的野心。他要揭示的是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这一复杂的过程。共和主义当然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但其中不仅包括它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还有它的变形与没落。这后一个过程,涉及到英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话语的演变,值得思考强盛帝国命运的人再三玩味。
在克伦威尔清教徒的革命狂热过后,英国人又两次选择了君主制,以政体复辟方式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英国也因此有了所谓“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之称。
我们从《德行、商业和历史》一书中可以看到,共和主义为何在英国人中间时运不济,他们披着一层外衣做了些什么;他们分明踏上了一条新路,为何还是觉得旧鞋子舒服。
“王道盛世”的政治演化
这本文集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大体限于所谓“王道盛世”(the deep peace of Augustans)时期,即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迅速嬗变为一个商业化社会的过程。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至今犹存,对同样生活在“盛世”中的我们可能并不陌生。
在这个“王道盛世”时期,辉格党寡头集团推动着英国的商业繁荣,它自身也完成了守旧贵族原则与资本原则的联姻。
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便是贸易的扩张和帝国的形成,而信用的扩张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大量的社会资金投资于政府股票,同时促进了“商业繁荣、政治稳定和帝国的实力”。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话说,英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作为“内生货币”的信用。与受稀缺性限制的黄金白银不同,这种货币的扩张,更多地依赖一个能够维护信用可靠性的体制,其政治作用意味深长。
这是一个“金钱利益”和“投机社会”崛起的时代。它的典型人物不是传统的工商业者,而是政治冒险家和股票公债的持有人,他们的主要财产不再是土地、货物和金银这类传统形式的财富,而是“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票据”。“财产乃政治人格的社会基础”这种传统观念也因此发生动摇,它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财产维系独立人格和参政能力这类古典思想,日益失去了对精英阶层的感召力。
与土地这种传统的财产形式不同,股票和债券一类财产并不能为政治自由提供保障,反而会强化资本与权力的合作关系。公债持有人对政府信用进行投机,便把自己同辉格党寡头政府的稳定绑在了一起,从而丧失了公民身份最重要的独立性。
在保守派和共和主义者看来,这会给政治秩序的健康带来“史无前例的危险”。当年休谟和斯威夫特(就是写《格列弗游记》的那位)等人对此都有忧心忡忡的论述。这一类人物在当时的漫画中也多被刻画成一副“生硬、卑鄙、刻薄的嘴脸”。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是这种有着极大危险性的因素,却给政治带来了奇妙的变化。为了使预期收益的兑现变得具有确定性,政府和投资人都要创造出一些使其看上去更可靠的条件。于是在政府一方面,守信成了一种制度要求,它必须维护宪政体制,“规规矩矩地做事”;而在社会一方面,基于长远利益的精明算计逐渐战胜单纯的欲望,为驯化和约束贪婪,使之变得“可以管理”提供了手段。英国商业繁荣的秘密便隐藏其中,它是使英国“光荣革命”的经济效果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财政原因之一:在辉格党的不懈努力之下,英国的公债有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作为其后盾,而法国发行的“革命公债”或“指券”(assignats)除了靠没收教会财产之外,并无任何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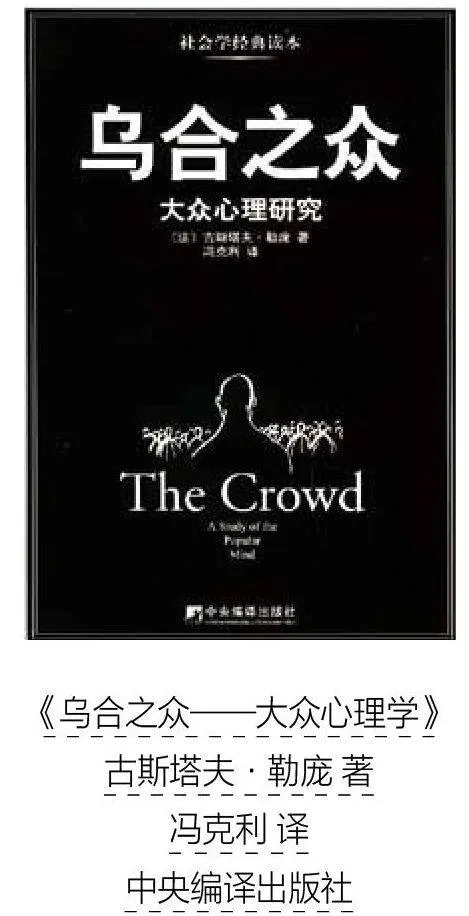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论述使欲望变得合理,自私可以开明,从而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和哲学著作。在公平法律制度的保障之下,私利的追求可以成为一种推动政治稳定、促进道德风尚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力量。当然我们也不难想象,在这种语境中,共和主义的“美德”无法有效转化为“利益”和“权利”的法学语言,其衰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亚当·斯密等人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便是这种新秩序的思想成果。它既是观察商业社会运行原理而产生的科学,也为辉格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有效的意识形态辩护。
教养VS美德
与此同时,“辉格主义话语”还形成了一种广为传播的“教养”与“礼仪”文化。它以“社会性宗教精神”取代“先知宗教信仰”,试图用更能反映文明演进过程的“风尚”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通过这种教化,可使人趋于儒雅温和,让政治变得行止有度,以往的宗教狂热则成了“有失体面”的表现。
波考克在书中不断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世界,从此类叙述中也最可体味他所谓“深入语境”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那个疯狂扩张的伦敦”,而是一个悠闲的城市环境,绅士商人在这里相互交往,学习斯文礼仪。“粗俗的托利党土财主和猎狐者被授之以生意经和新教徒的成功之道。”它喜欢安定闲适的生活,对托利党或共和派的“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武装公民”极不友好。认为“教养”和“自然演进的风尚”远远优于斯巴达和罗马人的“粗野美德”。
在这种环境里,辉格党的精英们知道必须让清教徒和乡村党学会“教养”,不然他们很可能不得体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权。
这种状况带来的结果是,财产、空闲和参政,变成了经商、悠闲和教养,此即当时“风尚”语言的基本内容。风气所至,商业繁荣基础上的社交礼仪和精致优雅的个人举止,便成了完善人格的主要方式。受其引导的活动,主要是社会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也不宜称为古典意义上的“美德”。
然而,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观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悠久传统,而且至今仍是社会批判最基本的话语资源之一,我们从阿伦特和桑德尔的语言中便能时常听到它的回响。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英国统治阶层,就像一切得益于“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人一样,却日益丧失了“美德”的优势,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必须放弃这种优势,另寻自我辩解的思想资源。他们与之对抗的故事,我们可以视为“古今之争”这场贯穿于整个欧陆启蒙运动的辩论,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自然延伸。
一方面,他们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美德”,例如经常从西塞罗的“生意”与“职责”之分中寻找辩词,这使得他们看起来像是“西塞罗风格的辉格党”。但他们所处的环境毕竟已大不同于古罗马。
古典时代“公民战士”的崇高与伟大,在于他“自足自立,清心寡欲,不忘公益,心系农耕”,而议会及其治下的纳税人和“经济人”既疏于参政,更乐意把政治也变成生意,他们管住了国王之后,便花钱请代理人(大臣和议员)去治理国家,把舞刀弄剑之事交给职业军队。建立现代“利维坦”的必要性,并不是来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而是商业文明的需要,而这显然不能用罗马的语言为之辩护。
更多商界中的人则纷纷加入“脱离美德、崇尚教养”的运动,为了替自己正名,他们将古代世界描述得“严酷而质朴”,“因专业化低下而十分贫乏”。用教养所确立的标准来衡量,古代公民甚至没什么道德优势可言。他们没有“随时可以兑付的信用和现金用来支付工资劳动者,只好盘剥不必支付报酬的奴隶和农奴的劳动”。在不存在频繁而多样化的商业社会环境中,他的人格也缺少多姿多彩和优雅精致,只好把闲暇用于积极参与治理国家的活动和征战,或是用于沉思的形而上学和迷信,而这些都是易于导致狂热的因素。就像孟德斯鸠所言,只有商业才能使欲望变得优雅、使礼俗变得温和。
从英国光荣革命到法国革命之间这段时期,辉格党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便是被这些有着不同表述方式的概念——礼仪、教养、斯文或品位——占据着。在他们看来,这个由“社交与情感、商业与教养”培育出的欣欣向荣的新世界,足以取代古人的“美德”和“积极自由”。法学在这方面尤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产权”的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它成了具有高度实践功能的“新美德”。
成功酿成的苦果
这种新美德,加上辉格党寡头集团通过限制王权取得的政治成功,它对英国史的保守主义解释,对礼仪教化的提倡与践行,逐渐变成了得到普遍接受的现实。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到美洲殖民地危机爆发时,英国已被国王与议会共治的体制牢牢占据,没有为其他任何政治选择留下空间,甚至连潘恩也承认“完全无法想象它会被推翻”。但是正如波考克所说,即使在寡头性质最严重时,这个体制也有着法国旧制度所缺少的自由主义灵活性。它所培养的政治平衡与中庸意识,它用“礼仪教养”构建的社会文化,它对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的有效维护,使18世纪的英国成了一个对“公民美德”这种古典价值越来越不友好的社会ZGCZGp1TBQXnaZ8zEhi+DjQHRIdCXjEtGXqZQUMRHb8=。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这个“王道盛世”虽然有效克服了国内的共和主义激进思想,却压不住它在美洲殖民地的发酵。当美洲人开始以税收为由向那个体制发起挑战时,它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了。
由此也再一次印证,无论多么合理的信念,若失去对变化中的政治现实的关照,往往会变得跟幻觉一样不靠谱。美洲的独立,便是这个很成功的体制所吞下的苦果。
正如波考克在书中着墨颇多的大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说,罗马人的美德使他们大获成功,但也为帝国的衰亡埋下了祸根。它衰败的原因,是它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强大所包含的危险,“它消亡的故事一目了然……是没有中庸精神的辉煌大业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样,辉格党寡头所主导的议会体制的成功,也使英国无法对18世纪70年代美洲殖民地的危机做出合理的回应。一路走来都很舒服的旧鞋子,终于让它栽了一个大跟头。
北美殖民地的精英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自己也是议会中的绅士,他们却日益感到西敏士并不买他们的账,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但推动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仍是英国的,尽管它与辉格党的议会体制是对立的。这便是“共和主义和乡村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它一直就存在于英格兰的政治传统中,“可以被用来否定议会主权的正当性,暗示着选择另一种政体的可能”,这为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家提供了他们不想再做不列颠人的激进解释。所以波考克说,美国人的政治性格固然是在美洲环境中塑造的,但你必须从“不列颠的背景”加以考察,将它看作这个大共同体发生的一次历史性危机,因为它始终与英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王权在议会中”(King-in-Parliament)——难分难解。美洲的独立,便是这种体制“内部发生危机”的结果。
波考克的这一番叙述,为我们认识这个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个大帝国,无论它多么稳固和持久,也无法完全消除其政治传统中可以为演化提供不同选择的复杂成分。如果其中一种适应得十分成功,它会倾向于排斥其他选择,使自身陷入僵化。这将让它在面对危机时拙于应付,为自己的成功付出剧痛的代价。
正是这种体制性偏执所导致的失败,使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大英帝国,变成了至今仍然健在的“大西洋文化综合体”。我们今天还能不时听到这个综合体中传出对“古典美德”的赞颂,说明“古今之争”也并没有结束。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译有《民主新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致命的自负》《立宪经济学》《邓小平时代》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