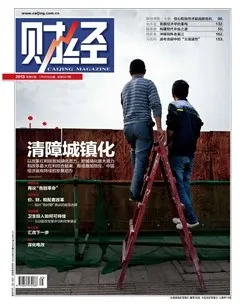多面印度
因参加“亚欧青年领袖论坛”,我到印度实地考察了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前曾阅读过关于印度的书籍,了解了一些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但多是较抽象和理性的认知,真正来到印度并目睹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境况后,感受还是相当震撼的。
新德里与旧德里
这次青年领袖论坛除了会议讨论与互动外,还给参会者提供半天的实地考察机会,参会者可以在城镇化与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三个领域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城镇化与基础设施这一主题,主要是乘坐地铁参观新德里和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
新德里的地铁是印度人很引以为豪的项目。2002年,印度首条地铁线路正式通车,这被印度人看作“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随着地铁系统日臻完善,那些一直为缺乏一套干净、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而深感窘迫的居民们认为新德里终于与国际接轨了。相较拥挤凌乱的公交系统,地铁里与街道是两个世界。
我们从地铁出来,来到旧德里大街的时候,着实感到吃惊。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不堪,到处是人力车、小三轮车、摩托车等,狭窄、拥挤而嘈杂。街道两旁的建筑异常陈旧,黑漆漆的,大量电线与光缆无序地裸露在街道两旁,斜挂在木杆上和树上,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如果就基础设施情况做个对比,我觉得作为印度的首都,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远赶不上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小县城。
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印度,几乎所有人都感叹,旧德里的基础设施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也参观了几个市场,同样非常拥挤、嘈杂和破败。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具有深远的国民福利含义。如果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建设,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两国起步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也比较相似,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丰裕。
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印度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落后?同印度的朋友交流了解后,我认为主要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思路。
印度选择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把发展服务外包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中国则选择主要发展制造业。应该说两国的选择都有道理,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都符合两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发展结果却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也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在一国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
我个人认为,印度以发展服务外包业为主的战略导向,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也不太鼓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服务外包业比如呼叫中心(Call Center)等,只需要固定的场所以及一定的数据通信系统就可以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
而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不仅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战略还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运送商品物资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也要求基础设施等硬件不断更新换代,以提高效率,维持竞争优势。
从大的视角来看,正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国经济绩效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结果,也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在印度,甚至在其具有很大优势的IT产业里,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足的。我们入住的宾馆是印度新德里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宾馆环境非常优美,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个著名的IT国度里,这样的五星级宾馆竟然不能免费上网,上网要付相当高昂的网费,30分钟近3美元,而且网络也非常不稳定,这种基础设施水平无疑会对印度的发展构成制约。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在资源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我看到,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污染。
我于10月30日凌晨3点到达新德里国际机场,一出机场就闻到了空气中刺鼻的化学品污染味道,本以为是当天凌晨有雾的原因,但在印度的六天时间里,新德里的空气一直如此,让人感到窒息。
在分组实地考察中,我们论坛的一些代表选择了环境保护主题,去了恒河支流的亚穆纳河(Yamuna River)。他们回来讲,这条作为新德里主要水源的河流,已经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污染,水面漆黑、黏稠,散发浓重的臭气,而河两岸的百姓则主要饮用此水,造成了大量的健康问题。
自由在民主之前
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
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
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
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
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
经济上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优质民主,反而降低了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因为要参加本次青年领袖论坛,我早早地把签证递交到印度使馆,提前了将近4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而这也是在德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实现的。
从印度回到北京,在新德里机场,我们过海关安检,真正见识了印度“民主”体制下傲慢、低效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个人要花20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海关,以至于我们几乎赶不上飞机,只好跟前面的人商量,让我们先进行过关安检。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活力印度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
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
这次在新德里召开的青年领袖论坛正好与第十三届德国-印度亚太会议时间相连,作为青年领袖论坛代表,我们获邀参加了德国-印度亚太会议的一些内容。
该会议上,德国政界、工商界的代表将近千人,规模之大让我感到震惊。资本是逐利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敏锐的嗅觉。德国大批企业家到印度来,应该是嗅到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目前,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制约,印度在制造业上还不能与中国竞争,但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未来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这次青年领袖论坛上,我们在最后的讨论环节,还是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发展思路和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组中40岁以下的欧洲年轻人,普遍坚持应该抛弃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幸福。但是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经济可持续增长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