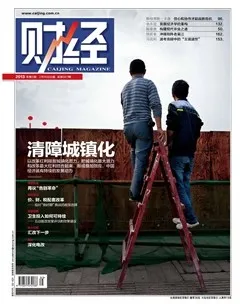重塑中美经贸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美双方贸易投资快速发展。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连续11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按中方统计口径,2012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846.8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204倍,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约达1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值约为3517.9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超过17%。
经贸投资的三个不平衡
总体上,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实现了利益互补、互利共赢,但是,也积累了一些不平衡因素。近年来中美经贸投资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
其一,贸易不平衡。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美贸易顺差更是出现大幅上涨,200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9%。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比2008年下降了16.1%,但仍达1433.8亿美元,2010年至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恢复增长,201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为2189.1亿美元。
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第一来源地,中美贸易长期的不平衡使得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其二,中美投资不平衡。投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投资规模上,还体现在投资结构上。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远小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规模,目前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约为707.3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77.85亿美元。
而中国对美国间接投资规模远大于美国对中国间接投资规模,2012年中国对美国间接投资中,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约为1.17万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间接投资规模仅为千亿美元。但是在总体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大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
其三,贸易与投资比例不平衡。中美间不断增加的巨额贸易总额,并没有带来相对应的中美双方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中美两国间的投资总额和增长率明显不足,与中美两国巨额的商品贸易和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符。
不平衡的成因
中美经贸投资不平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两国产业结构和分工不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产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为中国所取代,低端制造业被转移到中国,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也因而转移为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其次,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统计因素。
中国出口的货物经第三地转运是导致双方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交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按照原产地规则,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大陆地区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样货物在途经香港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附加值也成为大陆地区出口的一部分。
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计入香港而非大陆,无形之中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逆差额。
实质上,中美经贸不平衡,是在美国单边主义和美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美经济利益的不平等,美国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中国。
一般而言,中美经贸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同时中国又将出口获得的美元,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借回给美国,维持美国高负债运行。在这种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掩盖着双方利益的不平等。
美国是中国发展“外溢效应”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质优价廉的商品为美国消费者创造了经济福利,对美国稳定市场、降低通膨起了主要作用。中国用所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巨额国债,这对其平衡预算、稳定金融市场至关重要。但这种投资收益率很低。
研究显示,2002年-2012年间中国外储投资的平均名义收益率为3%左右,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还将进一步大幅缩水。
反过来,美国拿着从中国获得的价格低廉的资金,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和高收益的股权证券投资,获得了高额投资利润。
有研究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平均年收益率在20%左右。以苹果(Apple)产品为例,中国生产的苹果iPad出口到美国,中国表面上增加了出口额,但在150美元的生产成本中,只有约4美元是中国创造的附加值,绝大部分附加值和利润被美国投资者及其他国家拿走了。
除经济因素,中美经贸不平衡还来源于美国将经贸关系政治化。
纵观现代国际经贸关系,从没有像中美经贸关系这样具有强烈、浓厚的政治色彩。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采取双重标准,干预、限制中美贸易、投资的结构与范围,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投下了泛政治化的阴影。
其一,美国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WTO),坚持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但是,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要在入关15年后才能完成这一进程。在国内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动用反倾销、反补贴手段,对中国出口、投资设置障碍。
其二,美国自身并未遵守自由贸易原则。
按照自由贸易理论,一国出口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占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应该在出口中占主体。但是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出口额相对较少,且其行业生产率超出中国越多,该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则越低,这一现象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三,美国在两国经贸往来中采用双重标准。在对自己有利时,便拿自由贸易标准说事,时而祭起“双反”大旗,时而以所谓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当无法用自由贸易标准阻止中国时,它又拿起“国家安全”等非贸易的武器。
就深层次的根源而言,中美经贸之间的不平衡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即“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也就是说,只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存在,美国就必须保持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以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但是,作为国际货币国,美国又要保持贸易顺差以维持币值的稳定。二者不可兼得。
美元流出美国的途径不仅包括贸易逆差,还有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逆差”。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务也在持续攀升。2013年初,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1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90%。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美国的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根本无力支撑美元坚挺。长远而言,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自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国采取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美国凭借美元国际垄断货币地位向全球转嫁危机,将挽救美国经济的负担和成本让全世界买单。
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家,目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17万亿美元。每一轮美元量化宽松的溢出效应都对我国债权造成稀释与摊薄,不可避免对我国债权利益造成损失。
再平衡的策略
2011年以来,美国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战略,旨在巩固21世纪美国在亚太主导地位,扮演亚洲地区“世纪领袖”角色。
其目标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国家“遵守规则”,核心是要用国际规则和规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并联合地区其他国家在“规则制定、规则适用”的范畴共同对付中国。
美国在2011年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极力推出自己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以中国目前不具备协定所要求的条件为由,明确拒绝邀请中国参与其中。
此举旨在架空中国已经参与或正在谈判加入的各种贸易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甚至APEC本身,迫使中国顺从于美国的条件,使整个亚洲经贸合作都纳入美国主导的轨道上。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合作甚至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潜在对抗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关系将更加复杂。
面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与美国经贸关系的定位、战略,在强调互利共赢、增进中美战略互信、扩大经贸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扭转中美经贸投资的失衡,在坚持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中美经贸合作地位。
根本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归根结底需要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内需、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 才能从本质上减少中美经贸失衡,真正提高我国国民福祉, 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
转变外贸发展战略。按照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对美经贸合作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促进中美贸易平衡。我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产业结构处于价值链低端。中国应尽快调整产业结构, 实施科技创新,发展具有技术资本优势的产业,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实施市场多元战略,改善中国外贸市场过于不平衡与集中状况。应加大力气开拓新市场,努力提高对拉美、非洲、中东、独联体、东欧、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为应对美国外贸投资政策变化和市场波动提供充分的回旋余地,增加我方在中美竞争和博弈中的筹码。
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扭转中美经贸不平衡、不平等的局面,摆脱中国经济受制于美元的不利局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必由之路。美国持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备受国际社会诟病,欧元前景莫测,日元地位明显削弱,世界各国迫切期望一个新的主要货币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了发展的新契机。
要继续做大做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与主要贸易对手国家货币互换安排,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同时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随着这些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自然过程。
作者为中国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