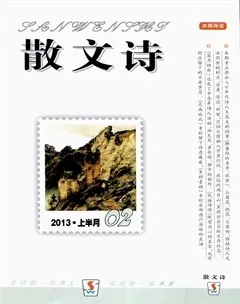黄恩鹏《过故人庄》选读
“自然才是真正的王者”。黄恩鹏以“自然中心主义”作为他散文诗创作的核心理念,这使他取得了一个崭新的视点,观察、认识和处理他的题材。他的“自然中心主义”不同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也不同于梭罗的“瓦尔登湖”。时代不同了,他在“现代化”的时空背景下,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物质挤压精神,科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以至于威胁到生活的基本安全的现实相对应、相联系,这就极大地提升了他散文诗的现实针对性。读了他的《过故人庄》这本新集子,首先的感觉便是他强化了一个新的散文诗的题材关注面。这是很重要的。然而,散文诗是精品性的文学新品种,在详论其成就时,不仅要关注她写的是什么,而且要关注她怎样写,只作“意义”的表述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我试图从他的几篇作品中,剖析一下她们的“艺术魅力”。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长久以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和精神追求的一个“标本”,也被许多诗人反复歌吟过。恩鹏的《种菊南山》赋予了一种清新、淡泊和简约的美的意境。“一脉浅水,足够一生饮了”,这样的语言,毫不做作,却饶富深意。“鸟鸣。月光。一声唱腔。都不会孤独。它们照在山坡上,如风,如雨,一遍遍浴洗心灵”,这样朴素的语言所表达的,早已超越了陶公那农耕社会的境界。完全可以涵盖当今时代人们所向往的那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界。恩鹏着墨不多,已将这种意境点染得十分诱人。然而,恰在此时,突然闪出了“他逍遥,人们饥馑”七个字,如一把匕首的切入,诗有了出人意料的升华。这便使他“自然中心主义”的美好向往,被现实的无情“匕首”所戳破,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惊醒”。诗人似乎也在“人间尘埃和车马的喧闹”前有所怀疑了:“能否”“何时”,均是在当下环境中对“自然中心主义”的一种拷问。
于是,诗人乃将他的目光转向“世外”,由人到鱼。“鱼,在河之侧听水”,真是出色的诗语言。还有:“在光的剖面看光”“或成为日月,阴阳互生”,他将鱼的世界,鱼在时间中的自由自在写得出神入化。完全与纷扰嘈杂的人间不同:“流浪的泪水洗濯着怆然的大地”,像这样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诗美语言,在朴实无华与简约节制中蕴含着很深的潜在美感,我以为是现代口语所创造的一种新型的诗美境界,恰是散文诗所应追求的。恩鹏在鱼的从不追问“今是何世”的“时间最深处”“过着苦难清贫的一生”中,寄托着他的理想:“在天地梵声里,圆满成佛”,这当然比“种菊南山”更上一层楼了。
然而,人既不能变鱼,也不能成佛,恩鹏只得求助于祖先了。“我开始猜想前世的样子。”在他的组诗《一粒盐的魂》中,有一章是《祖先与我》,他借助于“盐”,从幻觉中想象着过去时光中的人生。“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些自然景观“跌落深井”“古柏下谈玄论道的老者与天地对弈”,恩鹏在《易理》中开启了“须髯飘飘的仙人端坐虚静的堤岸,孤绝天地大谜的言说”的画面,极为概括而又形象地揭示了“祖先”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态,而又与现实生活中的“桌子、茶杯”这些“涌动的物象”,作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有了“我的绿蓑衣,我的舴艋舟,我的出征曲,我的渔歌子,都到哪里去了”的提问,他的对于已经走失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怀念之情,便惘然若失地得以呈现。
我还想提到一章《月光深处的雨》,是他的《北方不要南方的雨》组诗中的一章。她未曾采用大部分散文诗多节段的结构样式,而像散文似的连成一片。然而,她的语言与意境的美,却达到一种新的高度,我以为冠为“经典”之誉,是毫不过分的。“我在月光里伸出手,试图接住一粒雨或一粒鸟鸣,但我两手空空”,是一种对于雨的滋润的渴望,依然是现代人的大自然情结,是心灵干枯的哀鸣。全诗沉浸在极为细微的情感沉醉之中,语言之优美,情怀之缠绵,真似“涟漪旋转”“小溪蜿蜒”。您看:“窗子挡住梦想,天空在杯子里倾斜”“水寻找水,母亲寻找孩子”这是一种何其朴素却又意味深远的语言!“南方河流,血液已然干涸”“光的残渣被一些植物吸食”,到处是饥渴!“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灵魂无所归依”,这便是点睛之笔了吧。诗人将“月光”作为他的向往的一种依托:“我与月光融在了一起”,幻想“张开翅膀向月光深处飞翔”。这个美好的幻觉能带给我们多少慰藉呢?诗人与读者,似均有一种望梅止渴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