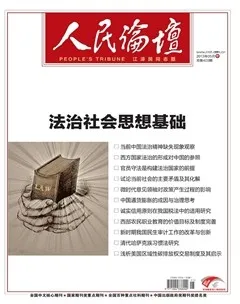论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艺思想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时代诉求: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聚焦点,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轨是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方式,而革命、农民和知识分子则是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汇。
【关键词】现代民族国家 文学革命 政治革命 农民 知识分子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诉求是建立一个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民族国家。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集中体现了这种时代诉求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放异彩: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聚焦点,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轨是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方式,而革命、农民和知识分子则是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汇。
聚焦点:创建现代民族国家
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毛泽东在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①这篇文章闪现着毛泽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进行革命的思想萌芽。历史事实证明,这两点确实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因此,考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必须将其置放于中华民族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的宏阔历史背景中,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所闪烁的现代性光芒。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被阐释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意义增值,最终凝结成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关于文艺问题深思熟虑的集体智慧之果。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一是20世纪40年代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标志的时期,该文与同一阶段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共同创立了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次高峰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发表为标志,该时期的亮点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任务。可以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两次高峰期聚焦着一个共同词—现代民族国家。如果说前一个繁荣期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如何用文艺促成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问题,那么后期他所关注的则是怎样借助文艺的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壮大。
方式: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轨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国人的百年梦想,在此过程中涌现的思想革命和政治斗争均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回应,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亦然。毛泽东以开创性的思维和行动力,以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文化生产力,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动力。
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观点。当全民抗战浪潮汹涌袭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起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联姻从理论层面走向了火热的现实,最终以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这个策略无可非议的合理性。
此外,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有一个创见:他把早期国人对新中国模糊的远景想象具化为有特定内涵的清晰目标,并为此目标制定了一套操作性极强的规程。从梁启超等人企盼的“少年中国”到李大钊呼唤的“青春中国”可知,国人对新中国的想象仍然停留在形象层面上,缺乏具体内涵。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新中国的航船才以清晰的面目扬帆出海。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这样定义知识分子倾心追求的理想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而与之配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式就是“民族的形式”。②
对参与创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艺所要承担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反对封建主义。对外反帝,意在取得民族主权独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对内反封,旨在清除封建积弊,实现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只有二者兼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巍然屹立。据此可知,新民主主义文化所提出的一套规范性文学话语,核心就是确立以现代性为鹄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
自《讲话》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所预设的新文化目标进入实际运作阶段。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考量的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怎样的配套文化,那么《讲话》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创造这样的文化来帮助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讲话》承继了五四“文学革命”和左翼“革命文学”所追求的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的目标,同时将前者生搬硬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汇入中国民族抗战的现实,自创了一套理论体系,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铺就了文化坦途。
关键词:革命·农民·知识分子
《讲话》浓缩了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文艺思想的精华,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标志,而革命、农民和知识分子则是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汇。如果说革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后两者则是革命的主体—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缔造者,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关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成败。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不仅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而且也离不开“文化的军队”。但自五四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支军队实际上各自为战。于是,延安座谈会召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两支军队的完全结合。在这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实质上分别指涉农民和知识分子。由此自然进入两支军队如何结合的话题,也就是座谈会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前者强调的是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后者关注的是文艺的服务手段和方式问题。
《讲话》将《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大众”具象化为“工农兵”,并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据了全国人口八九成之多的农业大国,工人阶级尚未成长起来,士兵基本来源于农民,因此,所谓的工农兵实际上指向了农民。
毛泽东始终相信农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发展与胜利的根本基础。他断然认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③这一思想,贯穿在他毕生的革命实践当中。正像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DNeDIiT0PT1cnqJ7Ur9zpQ==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④因此,在处理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述中,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民众一边,这确实让知识分子望尘莫及。
天然亲和农民的价值观使政治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其矛盾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在许多场合表达了“革命”统一战线对知识分子的热切呼唤:一支文人的纤笔甚至可以当得过3000枝毛瑟枪;“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却执拗地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队伍中,只能是被团结的对象,而不可能是领导者。因此他把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和转移立足点等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强硬规定知识分子只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文学革命”和左翼“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追求从文艺本体蔓延到创作主体,曾经的启蒙领袖变成了被启蒙的对象,救世的精英成了被拯救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改造和立场转变成为《讲话》中一个高亢的音符。
不可否认,这种凝聚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理想的战时文艺策略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事实上它也从政治和革命角度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而言也不无裨益。然而,时过境迁,这种带有特殊时代实用色彩的权宜文化策略被移植到政治经济形势迥然相异的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被教条化和绝对化,并最终被制度化为衡量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圭臬,极大地戕害了文艺的生命力。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知识分子的贬抑灼伤了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因此显得滞重迟疑
【作者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注释】
①[美]司徒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④[澳]王衮吾:《历史的天平》,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