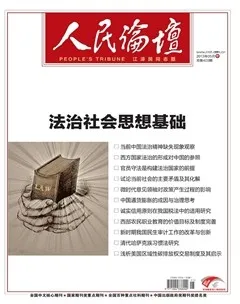略论保障性社区居住者的体育权利保障
【摘要】弱势群体保护是社会存在的核心构成,政府应该将弱势群体作为体育权利保障的重心,进而防止“现代贫民窟”的出现,这是对社会健康、公共健康维护的必须举措;政府无偿为保障性社区提供体育用地,是均等化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保障性社区 居民 体育权利 保障
保障性住房是民生工程,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其建设的工程中始终伴随着质量控制与功能性不足两方面的问题。对于质量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加大投入、施工方责任终身制等方式来进行监督与控制。而对于其社区包含健身康乐在内的功能—即应当规划的社区体育用地及其配套,却选择了忽视。无家的弱势群体对于居住问题得到解决表示满意,然而,一旦拥有了住所,真正成为“居民”之后,对于社区现状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届时,功能性短缺的问题将会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因此,解决公共服务问题较为重要。针对保障性住房的健康保障功能是否能够“被忽略”,本文拟通过社会学的相关视角进行阐释,表达对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构成的保障性住房居住者体育权利维护的诉求。
保障性社区及其居住者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存在、政府行为与弱势群体保护。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其他现存的拥有生命力的文明,保护弱势阶层的理念和行动一直贯穿历史。保护弱者,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群体的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维持社会框架的稳固。渴望延续的文明不会惧怕动乱、战争或者其他,但却重视社会的相对公平公正,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一直按照社会存在的基础法则予以执行。
对于社会系统具体化的生活世界而言,信用和社会共同体系统、政治行政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是四个具有间接性联系的图式,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繁荣萧条的必然)产生于经济系统之内且逐渐积重,必然会造成上述四个系统之一难以保证资源流通性,如果盲目以计划手段来进行调控、保护和提供基础设施以及负责公共部门的生产活动,将会导致国家承担了过多的公共抑或是私体的责任。国家不可以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服务人民,执拗地采取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伤害国家与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十分容易曲解民众的真正意愿。国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而这个仲裁者,应当在过程中偏重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无论是从公利或私利的角度出发—这也恰恰是保证近代西方社会“三权分立”思想没有被意义解构的重要因素之一。①
保障性社区居民构成及其需求的渐进性。瓦尔德(Walder)和V·舒依(Shue)认为基层社区与国家体制、政党相互联系,既可以把社区视为国家在基层的控制组织,也可以把社区视为社会控制的一个系结(conterminous with the party branch),国家以及政党通过它将权利渗入社会底层—这种新传统主义的关系模式,内质依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类似蜂窝状的共同体(celllike communities)的普遍结构。②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资条件的丰富,作为社会构成的个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得以提高。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来讲,只是在生存底线上进行了浮动,并未发生根本的形态转换,弱势群体依旧处于被权力集团漠视的境况。作为保障房居住者来讲,刚刚获得了社会保障—政府给予的优先低价购买或者低价租赁房屋的特权,个人的需求暂时得到满足,然而,物质文化追求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中国房屋的昂贵性、不易变迁等基本属性决定了社区居住环境必须依照发展的眼光,进行功能性配套与拓展。
“现代贫民窟”之忧。保障性社区,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者构成的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建设标准、限定购买价格或租房租金的房屋组团,即由政策性租赁住房、廉租性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构成的居住社区。然而,据调查,96%以上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都没有建设应许配套的文化用地、体育用地等,楼距拥挤、楼层高耸、休闲空间狭小以及居住密度大构成这些社区建设的共同特点,甚至绿地都能被变向侵占。保障房如果仅以满足人的居住需求为目标,那保障型社区不过是大量“蜂巢”、“蚁窝”式的建筑集合群体。再加之保障房建设多被安置在城市周边的郊区—这两项恰恰符合“现代贫民窟”的基本特征,现代城市弱势群体集中地依然成型。
保障性社区居住者的体育权利保障
社会健康与公共健康。维护社会健康,必然需要公共健康理念的贯彻。1948年执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中明确“享受最高标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毋庸置疑体育运动在公民个体生命健康中的作用,这从联合国颁布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中的第一章可以看出:人权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每个人应能自由地发展和保持它的身体、心智和道德的力量,因而任何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均应得到保障。
伦理学视域下的公共健康理念保障,通常涵盖医疗保健资源分配工作、气候维护及环境下被保护的公正以及全球化之下的国家区域公共健康公正等研究内容。③满足当代人权斗争的需要之后,应通过实质意义的理念宣扬,把体育运动对个体健康保障的预防功用引入到公共健康正义的理念之内。毕竟,个体的健康是构成公共健康的必须;而公共健康保障的基础,是需要对个体的健康权利进行维护。运动对于公共健康的保障有着先天优势,即预防功能。坚持进行体育活动的个体人,将会拥有更加富有疾病免疫力、抵抗力的身体。这对于重视外部环境的当代公共健康理念是一个完美的补充。
体育权利保障、以中下阶层权利为核心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体育权利保障不仅涉及广大群众,而且对于稳定社会状况,培养与恢复生产力方面作用明显。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处在权力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出生、入学、就业、医疗以及养老等整个社会存在的过程都称得上是“二等公民”,④体育权利的保障是一个“抽肥补瘦”的过程,因为利益绩效是持续递增的,财力富裕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不会终止,如果以绝对平等为原则,反而会损害传统的和合伦理与理念,引发仇视情节与独立意识。⑤因此,权利的保障,不仅是一种“救援”,更需要发挥其对初次分配后的利益进行必要调整,这是一种“发展型”的补偿。⑥这种补偿对提供者而言,出自个体获利的边际效应曲线上端;而对于急需救助的中下层阶级,则是个体获利的边际效应曲线的始端,是一种维护基本生存、基本需要的获得—这种获得是通过非自觉地牺牲个人权利得到的。
以上是近年来广大学者呼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原因。建设体育用地及其配套设施,正是维护保障性社区居民体育权利的具体体现,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的有形的服务过程。
保障性社区的最优路径选择
无偿划拨与免费供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无偿划拨注重的是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仅对于保障性社区居民来讲是无偿得到并进行使用的。通过明确“无偿”这个概念,可以把体育用地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或中央政府)。这样一来,保障性社区内除了私人购买或租赁的房屋之外,还有了一块“服务居民、提供其参与体育机会、满足其运动需求”的土地存在形式,这样从属性上明确了所有权与使用权,避免了后续纠纷,有利于使用的有效性。从长远来讲,即便是土地增殖须拆迁或者其他问题出现,在拥有所有权的情况下,这块体育用地相当于国家资产可以进行收回,自然又拥有“土地储备”的性质。此外,提供体育锻炼用地这一基础性保障,发展性的保障可以依靠社区自助等其他形式进行提供。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政府可以从“事事劳心劳力”的状况中脱离出来,也符合现今行政体制改革、职能转变的要求。
在社会中个体体育运动权利的保障上,通行的规则即:把中上阶层的关注重心放在“对健康意识的宣扬与培养”之上,把弱势群体构成的下层阶级的公共健康问题的关注eOoLxUldKTqP6wrRRC/loQ==方式选择为资金、设备等具体物质的支持。具体到我国的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建议政府释放国家集体资源配置的“制度红利”,通过对相关建筑规划体系及其标准的修改核定,高标准地完善包含体育用地及其设施的公建配套,不但可以将“社会公平”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充实到和谐社区建设之中,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公民人权保障行动来讲,也是走出了非常具体、坚实的一步。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注释】
①张旅平,赵立玮:“自由与秩序: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②张静:“旧传统与新取向—从法团主义看‘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模式”,《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03~407页。
③王喜文,张肖阳,肖巍:“社会公正:公共健康伦理的时代课题”,《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④程汉大:“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价值分析—兼论当前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的特点与对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⑤项中新:《均等化:基础、理念与制度安排》,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⑥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