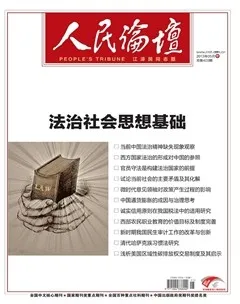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革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早在18世纪初,西方国家就有了内容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2008年6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迈入了战略主动的新阶段。它是我国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内在需要。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 历史发展 变革
回顾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11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由“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由被动移植转变为主动利用的巨大转变。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笔者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初体验:帝国主义殖民施压,法令条文形同虚设
清朝末年,清政府实施新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萌芽初现。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利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然而其后不久便成了政治运动的殉葬品。此后,清政府又制定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04年)和《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等法令。然而,作为帝国主义强力施压的结果,这些法令所保障的利益主体也就不言自明了,因此至民国初年这些法令也就被终止了。①
此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由于是直接照搬外国的法律,因此都没有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起步时间较晚,且大多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外力强加的影响,其法律建设与实施的物质基础及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并不相符,因此,基于这样的前提建立的法律很难符合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法律效用也很难体现。
萌芽:贸易合作陷僵局,知识产权显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制定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行政规章,比如,1950年政务院批准施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和《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1963年颁布了《商标管理条例》和《发明奖励条例》等,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1978年,中美贸易因知识产权问题陷入僵局,这引起了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知识产权建设奠定了基础。
《商标法》—纠正了商标的注册和专有权问题。1983年3月1日《商标法》开始施行。这部法律纠正了商标强制注册但注册商标人没有专有权的问题。它明确规定,商标采用资源注册制度,国家保护商标所有权。对于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则强制申请注册商标,未经核准注册,不得在市场上销售。
《专利法》—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色彩。与《商标法》的“水到渠成”不同的是,《专利法》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声中诞生的。虽然之前国家颁布过一系列相关的保障发明权的行政规章,但是专利所有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在反对私有制的时代大背景下,《专利法》的颁布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抵制。然而中美贸易谈判的僵局迫使《专利法》的起草步伐虽然步履维艰,但却更加坚定。1985年4月1日,《专利法》开始实施。
《著作权法》—对传统分享意识的最大挑战。《著作权法》这部法律是对传统分享意识的最大挑战。自1979年起草开始,反对“知识私有”的呼声就将这部法律的起草囿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草案起草历经8年才最终获得通过。紧接着又因为天价版权费而被紧急叫停,随后美国以“特殊301条款”向中国实施贸易报复,中美贸易再度陷入僵局,《著作权法》的出台则迫在眉睫。经过11年的激烈碰撞与交锋,《著作权法》最终得以实施。这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意味着我国思想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展示了知识产权制度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逐渐从被动抵制到主动接受的过程。
外源动力:对华贸易协商,知识产权要价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建设过程中,与国际接轨的客观要求、与来自国际上的贸易压力是推动其建设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外源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国际条约的约束—与条约不符的规定亟待更改。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我国开始积极加入各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这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奠定了良好基础。其中主要包括:1985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1989年,加入《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3年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器录音制品公约》;1994年加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协定》和《专利合作条约》;1995年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和《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条约》;1996年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协定》;1998年加入《专利国际分类协定》;1999年加入《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加入国际公约就意味着我们要面临各种条约的约束与监督,很多与国际条约不符的规定亟待修改完善。比如,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在专利权客体方面,对药品和化学的排除不符合《巴黎公约》的规定,因此,在之后的修订过程中加上了对药品和化学的保护。
除了修订现行法律之外,我国在这一时期还颁布了一些新兴领域的法规,比如,1997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1年6月4日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都逐步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国际贸易的压力—贸易协商更是知识产权要价。从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层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TRIPS协议)是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的代表。而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也一直以TRIPS协议作为其知识产权要价的标准,在与美国的复关谈判中,知识产权成了最大的障碍。
中国从知识产权建设萌芽到加入世贸组织也不过20年,其制度建设还有很多的不完备,然而与国际贸易接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与TRIPS协议接轨,我国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回顾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再到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动因都是外源性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制定与修订都小心保护着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作为最大推动力的始终是来自国际贸易上的压力。基于这样的前提,法律的变革方向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身的需求,而始终是沿着国际社会的要求制定的,这也是所有外源性法律制度的通病。只有当外源性动力转变为内在需求时,法律制度才能为我所用,真正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内在需求:经济发展促使知识产权引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产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规则进Xj/MXpn+CaCV9E6cvtdu4A==入世界贸易的范畴之中,进而将其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国际化,主导世界贸易游戏规则,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我们在国际贸易游戏中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加。2008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这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迈入了战略主动的崭新阶段。
纵观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欧洲发达国家最早确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中国家相对较晚,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较之落后200年左右,但即便如此,也比中国早了近100年。中国在知识产权建设的道路上起步较晚,虽然30年间取得的成就显著,然而回顾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值得我们思考的也很多。
正如吴汉东教授所说,西方国家作为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推行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经济学家在考察14世纪中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初年的中国,它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资本与教育积累的水平丝毫不亚于70年代的英国,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中国呢?②笔者认为:正如前文提到的,当一个法律制度不是在受外意强加的情况下,而是基于本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来制定的,便是有助于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一部法律的立法动因如果是积极而主动的,这部法律就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反之,如果是消极的、被动的,其法律效果不仅得不到充分体现,反而会抑制自身的发展,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吴汉东:“中国民商法律网:利弊之间: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②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建设30年的总结和反思”,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09-12/16/content_2006113.htm。
责编/丰家卫(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