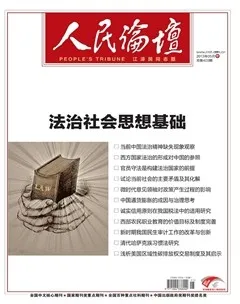论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成因
传统中国虽然有篇帙浩繁的成文法典,统治者也重视通过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但古代中国却缺乏西方传统中视法律为“至尊”、以法律来限制最高权力的信仰。这是与中国古代“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法律从属于权力以及儒家法“德主刑辅”的政治观密切相关的。构建现代法律信仰,需要以个人权利概念转变法律的工具性,赋予其独立价值;以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多元秩序来制约权力的专断性,使权力在法律约束下运行,从而实现法治秩序。
追求“民主”、“法治”以摆脱传统王朝更迭的治乱循环怪圈,走向现代化国家,是中国知识阶层自清末以来一直不懈追求的“中国梦”,这一梦想在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反复,至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特别强调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这对于构建法治社会,无疑是抓住了根本。
构建法治社会,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律信仰,以法律为“至尊”,尊重、敬畏并崇尚法律,改变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移法就情”的人情社会的“法律观”;而对于代民出治的各级权力机关,更要通晓、守护并遵从法律,从而改变以权代法、以权越法、以权压法的观念和行为。
传统中国虽有发达的成文法传统,统治者也重视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秩序,有的王朝甚至出现过崇尚法律的时期,但整体上远未形成将法律视为至尊的信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是传统中国对法律的主体认知,也可以说是主流观念。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统治者看来,法律虽不可或缺,但只是“治之具”,其价值相对于“德礼”而言,具有从属性,这种“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是传统中国缺乏法律信仰与法治秩序的思想认识根源。
构建现代法律信仰,需要以个人权利概念转变法律的工具性,赋予其独立价值;以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多元秩序来制约权力的专断性,使权力在法律约束下运行,从而实现法治秩序。
对法律的信仰即是对“法治”秩序的信仰,而“法治”秩序则意味着“法律的至尊性(supremacy)”或“法律的优势(predominance of Law)”。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阐述,在一个“法律主治”的国家,人民仅受法律的统治,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之外,人民有安排自己生活的绝对自由。只要未经普通法院的正当程序,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没有权力宣布某个公民有罪并因此限制其自由;并且,凡有权利受侵害的地方,便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救济。意思是,“法治”秩序的要义在于:一方面以法律限制权力的“专断性”,另一方面保障在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有制度化的救济途径。①
传统中国并非没有“法治”,事实上,如果仅就“法治”的字面意义—“依法裁判”而言,“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一样,中国的司法官吏也非常注重于依法判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②。但传统中国的“法治”,并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而是为着国家权力统治人民的需要提出来的。如果说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也是因为认识到任意性的权力反而不利于统治,而给掌权者设立一个权力限度对统治大有好处”,中国传统的“法治”具有两个基调,“一方面是把法律作为威吓民众的武器的一般预防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明确统治权限、控制官吏擅断的思想”。③
那么,传统中国为何未能产生西方文化传统中那种视法律为至尊、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律信仰呢?
“工具主义”法律观
在传统中国的法律语境中,“法治”与“德治”、“礼治”等概念都属于同一范畴,指的都是一种“治道”,即统治阶层管理社会与民众应当采取的策略问题。
儒家视法律的出现为社会危机的“救时”措施,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bAxKQXSFQ6PwXRDE/zDmEw==乱政,而作九刑”,“三代之法”,都是末世④。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社会治理的诸多工具的排序中,德、礼处于优先且主体地位,而法律则处于末端。受此观念影响,传统中国的政治家大都认为治理社会应当以德、礼为本,刑罚为末。作为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法典,《唐律疏议》制订的原则,突出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法家虽然崇尚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客观法律,反对国君对法律的恣意破坏,如《黄帝四经》强调“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⑤;汉代著名廷尉张释之强调“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律》中便出现了类似现代的“罪刑法定主义”主张。但法家对法律的态度也是工具主义的,在这点上与儒家并没有实质差别,正如近人萧公权先生指出的那样:“吾国古代法治思想,以近代之标准衡之,乃人治思想之一种。盖先秦诸子之重法,皆认为法为尊君之治具,而未尝认其本身具有制裁元首百官之权威。……于是法与术显然悉降为专制之治具,君主之权位遂超越臣民法度之上而绝无丝毫之限制。”⑥
由于法律只被视为“专制之治具”,所以,“中国的所谓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由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⑦传统的律典也不过是“皇帝告诫官吏如何准确运用刑罚的指示”⑧。《管子》明确记载说:“杀戮禁诛谓之法”、“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可以说,传统中国法律更多或主要表现为刑法或刑罚,因而,统治者崇尚法律往往意味着“尚刑主义”;民众遵从法律意味着甘愿成为被惩治或宰制的客体。“尚法”会加剧社会危机。汉初君臣在总结统一六国的强大的秦王朝何以“二世而亡”时,得出“尚法而亡”的结论。这使得“汉代之法”更多融入儒家的思想观念。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汉书刑法志》更是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以吏为师”。上述结论对后世影响甚大。因而我们的先民不论是从对法律的认知上,还是从法律的实践层面上,都印证了“尚法”不利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宋人杨万里论述法与刑的关系说:“法不用则为法,法用之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民犯之则为刑”,⑨也就是说,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之一,一旦外化为具体的运用,就成为刑罚的同义语。明代理学家丘浚引述吴澂说:“罚者一时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罚”,强调“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⑩
将法律定位为刑罚性的工具,这使法律不可能具有超越性的独立价值。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道→德→礼→法→刑是王道政治理念迫于现实向下的渐次展开,但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这种展开,最终能沿着刑→法→礼→德→道的上行路线,达到王道政治的实现,即出礼而入于刑,施刑而返于德,禁暴而归于道。”此观念与西方把法律视为信仰的精髓,相信“上帝即法律本身,故特别珍爱法律”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法律的工具性定位还使传统中国无法具备昂格尔所强调的法律的“自治性”:在实体内容上,传统法典因为“过分地吸收道德”而成为道德宣谕与行为规范相结合的混合体,从《唐律》制订的原则—“一准乎礼”即可看出法典更多融入道德理念,自身没有独立性;就司法机构的设置而言,中国古代地方衙署甚至没有或较少设有专门的审判机构,审判只被视为地方衙署多种行政职能中的一种。中央自唐宋以后虽设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但审判、复核、平反等职能仅是其诸多行政职能之一而已,更谈不上“专属性”与“独立性”;在方法上,传统律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并未产生自身独有的价值理念与研究方法;在法律职业上,只懂法律的官员被视为庸俗的“刀笔吏”,精通法律的讼师则被视为如盗贼般的“讼棍”,鲜有学者愿意把自己视为法律专家,这与古罗马法学家享有的那种尊崇地位,是大异其趣的。
故此,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法治”概念,而且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也有过“法治”实践,但由于法律在传统文化中只被视为刑罚性的工具,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与自治性,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从未形成过法律至上的信仰,也就无法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法律从属于权力
用法律约束权力的专断性,以使公民免受他人意志及行为的恣意奴役,这是法律信仰的核心。这种信仰的产生,既需要将权力视为“必要之恶”而加以警惕,也必须理顺并妥善处理好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限制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的恣意妄为和扩张,改变法律完全从属于权力、服务于权力的状态。
西周至春秋早期,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君与贵族共同分享,周天子虽是天下的共主,但其权力受先例及传统礼仪、习惯的限制,他对各地的诸侯及封臣并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王权还不是那么极端化,原始民主遗风尚有一定生存空间”,法律具有多元性的效力渊源。国君没有颁布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的权力。秦汉以后,君权虽得到加强,但君主仍不是唯一的法律渊源,臣僚拥有相对普遍的立法和议法权,郡县长官实际上掌握生杀大权。隋唐以后,私人注律受到严格限制,死刑权实现真正上收,立法和最高司法权完全从属于皇权。
回过来再看权、法关系。在传统中国的固有观念中,一直存在“有治人,无治法”的坚定信念,因为在先民看来,任何法律即便是“善法”,也需要人去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是人(主要是君主)制定的。“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的汉代杜周,他任廷尉时以“善候伺”著称,“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人们的不满,有人质问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的回答成为“法自君出”的依据之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在杜周看来,书于竹简上的法律效力远远不及皇帝的意旨和命令,或者说,法律无非是君主所肯定的内容。对于杜周的回答,我们可以做宽泛解释,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他们如同各级衙署的“小皇帝”,其权力可以超越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身就代表法律,是法律的象征。法律来源于权力,从属于权力,因而,也必须服务、服从于权力。
从法律内容来看,传统法典更多的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等级秩序和封建伦常,具有极强的“私属性”。因而,尽管内容、条款不断加增,但甚少或者说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对民众私权的保护。换言之,传统法典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禁止性、惩戒性规定,法律所展现出来的多属“恶法”;对于民众的权益,则视为“锥刀之末”的“细故”而不加规定,即便理直而“打官司”,也被视为不安本分的“刁民”。这样的法律哪里值得尊崇?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三代以后之法的制订,原因皆出于私,“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萧公权也认为:三代以下“其制度本于私天下之一念,大背贵民之旨,故不足以比三代之法耳。抑就另一方面观之,三代公天下而法因以疏,后世私天下而法因以密。疏者近于无法,密者适成非法”。法律属于专门知识,更多的民众当其蒙受冤屈时,他们无法也不会求助于法律,而是奢望“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说到底,“青天意识”不是社会对法律的呼唤,而恰恰是对“人治”的崇拜。法律的工具性特征以及从属于权力的位序,使得传统社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大政小法”的格局,法律被要求“服从并服务于政治”。
“刑罚时轻时重”
法律的工具性质以及从属于权力的位序,由此引申出传统中国法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法律的时轻时重,即非衡平性。学者们总是从积极方面解读中国法律的起源。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中国的先民将良好愿望寄托给“獬豸”这种独角神兽身上,据说,它能够辨别善恶,用独角触不直者。但这种法律的“平之如水”即衡平性,却甚少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而代之的更多是法律时轻时重,即非衡平性。
法律的工具性质决定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不同。当社会秩序稳定,四民乐业,家给人足时,法律被搁置起来,“备而不用”,即古人艳称的“刑措”,认为这恰是“盛世”的表现;而当一个王朝走过其鼎盛,步入衰落时期,法律的重刑化就成为一种必然。反映在同样一种犯罪行为上,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惩罚就有很大不同,甚至悬如天地。这时,“约法刑简”就受到破坏,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严刑酷法来强力维护社会秩序。清初沿袭明朝法律,死刑条款不足二百,到乾嘉以后,累积的社会矛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统治者遂用重法治官、治民,死刑条款达八百余条。以强盗罪而言,康雍时期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发遣之罪,咸丰以后,社会秩序被打乱,强盗罪不分首从皆斩;到了同治时期,不但首从皆斩,且地方官可以先斩后奏,乃至斩而不奏;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连把风、接赃之人,因属“同恶相济”,一并处斩。法律成为统治者试图纾解社会危机的筹码,重轻予夺,曲缩伸张,因而同罪异罚不但体现在法律身份不平等上,也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适用上。因而,法律更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人们侥幸以逃避法律为能事,何谈“尚法”?!桃应曾向他的老师孟子提出“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人,则如之何?”这样的问题。孟子最初的回答是“把他抓起来。”桃应又问孟子:“舜是天子,难道他不禁止皋陶吗?”孟子回答说:“舜怎么会禁止?他已经授权皋陶了。”桃应又问:“那舜怎么办?”孟子最后回答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连贵为天子的舜都会背着犯有死罪的父亲“窃负而逃”,逃避法律的惩罚,岂能要求普通民众遵从法律的裁决?可以说,儒家法的本质是维护“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是法律面前绝对意义的不平等。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则要求打破这种人为的从而也是用法律来保障的等级秩序,就此而言,挑战并质疑法律,对社会变革具有积极意义。
民众法律意识的缺失
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体制、制度性原因,是主要从“官”即法律实施的主体的视角来分析的,那么,从民众即法律实施的对象即客体而言,法律意识、法律知识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传统中国法律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法律至上的观念。从立法原则到具体内容,法律更多体现为保障以皇权为主的公权法特征,因而刑罚构成其主体或主要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这就意味着,民众一旦与法律接触,往往成为被宰制的对象。就此而言,法律为不祥之物,等同于污物。我们的先民在不祥之法上,要专门加上“祥刑”之字义,就是希望给法律赋予社会稳定器的功能。
同时,法律是专门知识,在农业社会里,知识本身是社会上层乃至进入上层社会的人所独享,而不能进入普通民众之中。因而,民众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甚至绝大多数处于无知的状态。因而人们一旦触犯法律,也不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统治者而言,他们更是垄断法律,拥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裁判权,希望民众长久处于法律的无知状态。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上,晋国贵族叔向明确表示反对,他写信指责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唐代大儒孔颖达在为这句经典作解时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矣。”统治者惧怕法律公开以后,为民众所知悉,并据此维护自身权益,那样的话,统治者就不能“议事以制”,随意解释法律。
使民众处于法律的无知状态,直到清末,即便是以洋务派、改革者著称的人,仍然如此认为。同光年间,有一江宁县令,为了在江苏州县官吏中“普法”,编写了七言律文,经按察使司呈请巡抚丁日昌颁行。而丁日昌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在乡塾中让生童“读律不读书”是错误的,因为一旦让人掌握律例奥妙,则不便于官员。他说:“悬书读法,要在各州县视民如伤,于律例中择其易犯各条,恺切讲解,或榜示通衢,未尝不可稍资警惕,若爱民初无实心,则良法仅成具文,不诚无物,其何感之能通?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中固有深意存焉。”在丁日昌的眼中,法律只有那些与民众容易触犯的条款有关,而即使是“生童”这样的知识阶层,也不便于让他们知晓法律。那么,他所说的“深意”究竟是指什么?他解释说:“律例一书,善读者以为仁之至、义至尽,至平至正,允协于中,不善读者凿破混沌,便生机械,老庄齐物之旨,其弊尚流为申韩,申韩刻薄之余,其弊将安所底止?童蒙不读书而读律,亦非当务之急也。”令其将已经颁发州县的七言律文,立即收回销毁。说到底,还是一个“怕”字,担心法律一旦为非官府的人所知晓、所掌握,那么,必将挑战公权力对法律所独有的解释权、裁决权。
从以上分析可知,传统中国并不存在视法律为至高无上的法律信仰,这种法律信仰的缺失,也是当代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种负担,或可以称之为消极因素。而如何超越缺乏法律信仰的文化传统,构建新的法律信仰与法治秩序,不但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更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跨过去的一道门槛。
【注释】
①[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②[美]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
③[日]仁井田陞:“唐律的通则性规定及其来源”,姚荣涛译,载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3页。
④《左传·昭公六年》。
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3页。
⑥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⑦[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王亚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⑧[美]钟威廉:“大清律例研究”,苏亦工译,载于《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9页。
⑨(宋)杨万里:《诚斋集·刑法论》。
⑩(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百,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53页。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506页。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徐祥民:“春秋时期法律形式的特点及其成文化趋势”,《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第142~148页。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96页。
林乾:《中国古代的法律与权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孟子》“尽心”。
《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7~1228页。
《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六年。
《抚吴公牍》下册,卷三十八。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