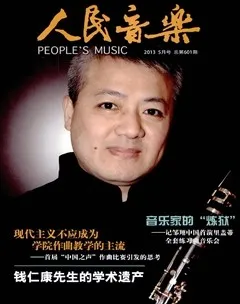推动中国当代艺术音乐发展的创意工程
首次见到《中国新音乐年鉴2009》(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钱仁平主编。本文中以下简称《年鉴》,其他年鉴则使用全称以示区别),是在2011年5月北京现代艺术节期间,那时该书刚刚出版,还带着油墨的清香。笔者立即被该书独到的学术眼光、“及时”的选题和精美的装帧强烈吸引,在北京的宾馆里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一气读完全书,受益匪浅。至2012年5月,《年鉴》2010卷如期出版,总页码竟达550页,比2009卷的第317页篇幅增加多达70%,信息量更大。笔者读来深有感触,觉得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实在值得颂扬,是以作此文,记叙自己对已出版的两本《年鉴》的感受及对后续出版的期待。
一
中国音乐的发展无疑应该以大量的音乐创作作品为根基。社会对中国音乐的关注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音乐、当代流行音乐以及少数已获得广泛认可的当代经典艺术音乐作品之上,而更多的新创作的艺术音乐作品,则一向甚少被关注。由于乐谱出版难,演出少(多在专业音乐院校内部或学术会议上,未推向社会市场),这类新作品往往只在专业“圈子”里流行,有关的活动报道也常常仅限于地方媒体及个别的报道综述,不能让人形成整体印象。因此可以说,除了少数知名作曲家及其作品,中国当代艺术音乐一直处于“默默”的发展之中。社会大众,甚至中国音乐界,可能不知道有关当代中国艺术音乐“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有什么”。《年鉴》的出版全面梳理中国各地乃至海外各年度有关中国新音乐的创作与活动,向全社会展示中国新音乐的整体状况并做出完整清晰的档案记录,可谓填补了“空白”,弥补了缺憾的创意之举。
例如,2009卷的“年度创作”与2010卷的“专业创作”栏目由各地的音乐学者撰写的各专业音乐院校及海外华人新音乐年度创作与活动述评,囊括了作品创作、演出、学术活动等信息,全面地展示各地的成果与特色,尤其是部分文章中以列表统计各项成果目录,一目了然;“专题项目”记录了当年度各地举行的有关中国新音乐的重大活动与项目,例如2009卷包括北京现代音乐节、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中央音乐学院的德国当代音乐周、上海音乐学院的当代音乐周、国际电子音乐周、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及历届中国交响音乐季纪事、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盛会、第四届“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系列活动》述评等内容;2010卷除上述北京、上海的音乐节活动外,还包括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文艺表演综述、“上海之春”创办50周年综述、徐振民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与研讨会、新加坡“赵季平作品专场音乐会”等各类活动的述评。仅此两项就让笔者读来不禁慨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中国各地还是有那么一群作曲家在坚持艺术音乐创作、原来中国新音乐领域还是很热闹、很精彩!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
《年鉴》的栏目设置可谓纲目清晰、完整全面。上述带来大量信息的两个栏目中,不仅包括中国各地专业音乐院校以及北京、上海两大中国音乐艺术中心的主要活动,还包括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的中国新音乐活动综述,让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新音乐”在不同地域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笔者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从《年鉴》2009卷读到台湾2009年提出《乐典计划》,记录台湾当代作曲家谱写的美丽乐音(146页),这与中国大陆从2006年即开始的《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计划异曲同工(2009卷,第251—255页)。两者在遴选标准、活动内容等方面是否可以相互借鉴参考而共襄盛举?“人物访谈”栏目收录访谈者与部分作曲家的对话,2009、2010卷就收入对高为杰、叶小纲、郭文景、张勇、何训田、金湘、王宁等当代中国作曲家的访谈,还包括与怀纳、拉赫曼等国际知名作曲家的专题对话。在采访者与受访者的精彩对话中,闪烁着作曲家的创作心得与音乐观念。这一栏目让笔者深受鼓舞的还有获悉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的“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研究”项目进展顺利,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认真学习与审慎借鉴国际先进数字化保存的学术理念与技术标准,积极研讨、制定既便于信息交流、科学管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保存标准(2009卷,第280—286页)。这一工程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必将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献综述”栏目则包括年度音乐创作评论综述、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状况综述、国际文献视野中的中国新音乐等内容。尤其是《国际文献视野中的中国新音乐》一文,从学位论文、期刊评论和出版三个方面对各年度中国新音乐在海外的发展状况进行文献梳理与总结。作者从众多的外文文献中梳理提炼的述评文字,让我们知道中国新音乐在国外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以及外国音乐学术界对中国新音乐的关注度与主要观点。作者在结语中提出的建议“重视作品出版;重视音乐会评论与学位论文;重视作品与人物的译介”以及文末“中国新音乐在海外,传播比研究更迫切!”(2010卷,第505—506页)的呼声,更深刻地引起笔者的共鸣——若干年前笔者在欧洲留学,就亲历了在图书馆找不到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乐谱与音响、中国音乐家尽管在国内大名鼎鼎但国际上很少有人知晓的尴尬,不能不说这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力的结果。
二
音乐界人士看到该《年鉴》,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编出版的《中国音乐年鉴》,这套已连续出版多年的丛书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大事述评的重要工具书。两者有何异同?《年鉴》能否有所超越或者说形成自己的特色?笔者认为,两相比较,各有千秋,而《年鉴》从一开始就以明确的定位,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
1.限定选题,大幅拓展了纪事的深度与广度。《中国音乐年鉴》兼顾了年度音乐事件的方方面面,可谓全面系统,但正因为此,对于音乐的某一领域或侧面的记述与评论可能缺乏深度与广度。《年鉴》与之相比,多了一个“新”字,就将选题范围明确地限定在当代中国艺术音乐,从而可以在这一领域纪事的深度与广度上大有作为。例如《年鉴》的“专业创作”栏目,不仅囊括九大专业音乐学院、还包括部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学院、香港、台湾、澳门、海外华人的新音乐年度创作,分别由当地相关音乐学者撰写,保证了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这种做法使得该栏目的文章所提供的信息是由一人撰写全国各地情况综述之类的年鉴文章根本无法企及的。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音乐年鉴》是一本有关年度音乐的“通用词典”,人们可从中查找到很多有关年度音乐的信息,包括“中国新音乐”词条,但其解释不可能全面与深入;而《年鉴》则是一本有关中国新音乐的“专业工具书”,人们可从中获得该领域尽可能多与深入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年鉴》的出版可作为《中国音乐年鉴》的有效补充与深入,成为各年度“中国新音乐”的专门工具书。
2.出版迅速及时,强调时效性。年鉴作为记录某一领域年度活动与成果、每年出版一次的书籍,也应该强调时效性,即能够迅速及时地出版会更好。这样,年鉴起到的作用将不仅仅是过去事件的资料档案汇编,更能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发展起到及时的借鉴参考作用。但由于年鉴内的文章常常是各方面的综述与评论,编辑组稿复杂、作者写作费时,如果再加上经费不足等问题,常常导致年鉴出版的严重滞后。在这一点上,《年鉴》在2012年5月就能出版2010卷,编辑部的工作可谓“雷厉风行”,而还能保证较高的稿件质量与精美的出版装帧,更是难能可贵。它与《中国音乐年鉴》在文章时限上还有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中国音乐年鉴》每年的卷本基本是记录上一年度的事情,例如2008卷记述的是2007年度的内容;《年鉴》则记录当年的事件,例如《年鉴2009》记录的正是发生在2009年的事件,以此类推。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喜欢《年鉴》的做法。在出版时间可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如果每年卷本记述的还是上一年度的内容,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时间的错觉,年鉴仅仅成为一种对“过去”的档案记录,失去了应该具有的对“现实”与“未来”的指导作用。
3.图文并茂,增加了阅读吸引力,能更好地保存史料。《年鉴》中对重大音乐活动和音乐人物,配合文字还使用了大量的图片,包括海报、证书、活动现场、人物照片、谱例、图示等。这些图片资料在很多同类音乐书籍中都是少见的。印制成本高昂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它们以形象生动、图文并茂的形式增加了阅读吸引力,对于更好地保存史料,也显得尤为珍贵。
三
《年鉴》的2010卷与2009卷相比,也充分显示了年鉴编辑部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精神。本文开头提到的篇幅上的大幅增加只是表面,更重要的在于内容编排与栏目设置的调整与完7Unjsn0RZOpVGeHGzxIjbKvLjCYqA0azv/6F+Oq5ajY=善上。例如,在2011年的北京现代音乐节期间,笔者向《年鉴》的主编钱仁平先生毫无保留地转达了我对该书的喜爱以及2009卷“年度创作”有大陆各地、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但独独缺少澳门篇章的少许遗憾。《年鉴》2010卷就有了一篇有关中国新音乐在澳门的综述,从而在体例上达到了完整。在栏目的设置上,2009卷的“年度创作”、“重大项目”、“专题访谈”在10卷分别改为“专业创作”、“专题项目”、“人物访谈”似乎体现了一种深思熟虑,在表述上更贴切适合一些;2010卷更增设“年度观察”,分“十大新闻”与“大事记”全面记录中国新音乐领域当年度的主要事件。
当然,《年鉴》的栏目调整也还存在空间。例如“专业创作”专栏似乎还是不能准确概括该栏目的特色,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涉及的不仅仅是创作,还有展演、学术研究等内容,或许改为“年度各地报告”更合适?2010卷增加的“年度观察”中有关中国新音乐的“十大新闻”与“大事记”,是以什么标准遴选上榜,需要有个交待。此外,《年鉴》的所有作者均未注明工作单位等信息,尽管“圈内人士”可能知道大部分作者的“来头”,但如果能加上相关信息——如果由于编排体例问题而不方便在每一篇文章中注明,至少可以在书末增加一项“本书作者简介”,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岂不更符合当前学术出版的惯例?
吹毛求疵,实乃爱之心切。《年鉴》的出版是当代中国艺术音乐的福祉,也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切盼《年鉴》办得一年更比一年强!
代百生 博士,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音乐课程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