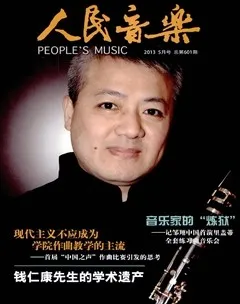从单一技术训练到综合素质培养
高等音乐院校无疑是培养“职业作曲家”的教育机构,其作曲专业的课程设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作曲专业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是“四大件”还是“五大件”?是“研讨课”(Seminar)、“学术报告会”(Sympoduim)还是“工作坊”(Workshop)?或干脆说,怎样才能锻造一个作曲家?在一个作曲家的成长过程中,高等音乐院校作曲系应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本科学段的课程设置,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既有“四大件”加“一对一”的课程体系,而且还需要完成从单一技术训练到综合素质培养的转型。
一
伴随着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建立,中国逐渐有了作曲专业。1930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黄自任教于国立音专,仿照欧美创立了“理论作曲”的教学模式。经过漫长的探索,终于形成了一个以“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对位法”(counterpoint)、“曲式学”(formenlehre)、“配器法”(orchestration)等基础作曲技术理论为主体的课程体系。这种“理论作曲”的教学模式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其他高等音乐院校的作曲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部分音乐学院(如武汉音乐学院)的作曲系还仍称“理论作曲系”。建国后,高等音乐院校的作曲专业,基于建国前的探索和实践,并接受和照搬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形成以“四大件”(和声、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配器)为专业基础课、外加“一对一”专业主课的课程体系。当然,作曲专业的学生除学习上述专业方向课程外,还要学习其他公共课程(如音乐基础课、音乐史论课、文化课、政治课等)。六十多年来,“四大件”加“一对一”的课程体系,一直支撑着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教学,至今仍是一个较为合理、有效的课程体系,但同时也是一个保守和具有缺陷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尽管这种课程体系在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并使得受教育者具有坚实的作曲技术基础和一定的音乐创作技能,但它仍值得反思且需进一步完善。
应当承认,“四大件”是欧洲“共性写作时代”的产物,可谓西方科学主义及其理性思维的结晶,无论是从哲学意义上说还是从实践层面看,都具有其完整性和科学性。但进入20世纪“个性化写作时代”,其完整性和科学性不仅在作曲家那里早已失去其有效性,而且还在音乐学院的讲堂上受到质疑。在新中国六十多年高等音乐院校教学改革进程中,“四大件”一方面受到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对其质疑的声音也不绝入耳,并提出“改良”。其中,改良的意见主要有二:
第一种意见是主张在“四大件”学科建设及其教学9f3febadbe616ecd8a6ed8b257c293f8中加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并试图建立一种“中西融合”的理论语境。早在1964年,陈应时在《对于改进作曲技术课教学的一点浅见》一文中就提出将“和声、复调等四门作曲技术基本课程拼成一门外来形式的作品分析课”、“另外再开设一门包括“五四”以来革命音乐在内的民族民间音乐分析课”的建议①,以改变一味学习那种基于欧洲音乐的“四大件”的局面,主张增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内容。这种建议无疑是合理的,其目的在于克服运用欧洲作曲技术创作具有中国民族民间风格音乐作品时那种“‘穿着马褂打领带’的不和谐不统一状态”②。这种“改良”的意识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不难发现,在全国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1979,武汉)及后来一系列关于“四大件”学科建设及其教学的学术研讨会③中,将中国传统音乐纳入“四大件”课程教学内容已成为共识。1995年,邹承瑞《关于作曲技术理论课教学的思考》一文集中讨论了“四大件”学科建设及其教学的民族化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批判“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语境中对长期以来中国作曲专业的“四大件”教学中的“西化”或“欧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第二种意见是,建议将“旋律学”或旋律写作技巧纳入作曲专业的技术理论教学体系,即将原来的“四大件”扩展为“五大件”。这种呼声在新中国作曲技术理论和作曲专业教学改革的语境中也未间断。1998年首届全国旋律学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次会议不仅为“旋律学”正名,而且使旋律学对于作曲专业教学的意义得以确立。薛艺兵《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一文中就提出“作为作曲技术理论的旋律学。”④此后十年间,将“四大件”扩展为“五大件”的建议也越来越强烈。
对于作曲专业“一对一”个别课教学,近年来作曲教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和改革的建议。如王飞《我国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之我见》一文就提出对作曲专业的“一对一”个别课教学的改革,并着重介绍了西方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专题讨论课和学术报告会”和“教学工作坊”的教学情况,认为“我国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个别课(专业主课)教学具有改革和发展的必要。⑤
可喜的是,建国后六十多年来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四大件”学科建设和教学的民族化、“四大件”向“五大件”的扩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对专业主课的“一对一”教学模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进。比如,五声化和声、民族曲式、民间音乐中的“支声”等内容,在不同程度被纳入作曲技术理论课的教学体系;“教学工作坊”在个别高等音乐学院作曲专业主课教学中也得到一定范围的尝试。尽管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总体上看,“四大件”的基础技术理论课程和“一对一”的专业主课仍是中国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构架。
二
毋庸置疑,中国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本科段的课程设置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坦率地说,过去几十年对作曲专业课程体系的反思和改革并不彻底,也不深入。这是因为,过去的反思和改革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具体而言是对“四大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的质疑,对“一对一”个别课教学效果的检讨。但应看到,在作曲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中还有一个问题长期被忽视。这个问题就是,即便“四大件”加“一对一”的课程体系是科学和完备的,或者说上述“四大件”学科建设及教学中的某些弊端已被克服,“一对一”的个别课经改革更体现出了其有效性且得到诸如“专题讨论课”、“学术报告会”、“教学工作坊”等多样化现代教学手段的补充,那么作曲专业的课程体系就是完备和科学的呢?本文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提出并得到答案。
毫无疑问,培养“职业作曲家”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真正的作曲家必须具备一种综合素质。这不仅是有关音乐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包括敏感的文化洞察力、良好的审美品味、高远的艺术眼界、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文化修养,等等。当然,这种综合素质不可能完全在课堂上获得,有些还需终生的修炼和习得。但高等音乐院校作为培养作曲家的专门机构,应尽可能地通过实施教学使学生逐渐具有这种综合素质。但长期以来,中国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教学却一直是以“四大件”和“一对一”为中心的,缺少综合素质的培训。本文认为,在“四大件”的作曲技术理论教学与“一对一”的专业主课教学之间需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即一种旨在探讨音乐创作一般规律并将作曲技术理论与艺术或美学理论相结合的“音乐创作理论”教学。其教学内容就在于让学生知道怎样创作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包括音乐作品的创意设计、音乐风格的设定、体裁与题材的选择,还有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何运用特定的音乐形式与手段塑造音乐形象、表现现实生活、表达文化观念等。显然,在既有的“四大件”教学中,虽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音乐创作”一般规律及相关艺术和美学问题,一个优秀的技术理论课教师也会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声形态、曲式结构、复调织体、音响、音色进行艺术表现和形象塑造,但总体而言,“四大件”仍是一个较纯粹的作曲技术理论课程,而不是真正的“音乐创作”课程。在“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学中,教师虽然是以“音乐创作”及具体作品(学生习作)为教学内容的,但它仍不是真正的“音乐创作”课程。众所周知,一个作曲专业学生在五年的学习中一直没有脱离“音乐创作”。一般说来,一年级写带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二年级写钢琴曲或其他器乐独奏曲,三年级写弦乐四重奏或其他形式的室内乐作品,四五年级则要写管弦乐作品并作为“毕业创作”。但不难发现,这些写作主要是以技术训练为目的的。如果说艺术歌曲和器乐独奏曲的写作是培养学生的旋律写作技巧、音乐材料运用和音乐主题发展能力、音乐结构布局能力,室内乐写作是培养学生运用和声语言和对位法的能力,那么管弦乐写作则是让学生掌握配器法并具有更高一级的综合运用能力。故在“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学中,教师主要任务是修改学生的这些习作,甚至是单纯地帮助学生解决习作中的技术问题。无可否认,“一对一”的教学,无疑也会涉及艺术表现或形象塑造等问题,但这一方面的内容却主要是就学生的习作而言的,所传授的更多是一种口传心授的创作经验,而非理论化、共性化的“音乐创作理论”。这就意味着,一个五年制本科作曲学生,五年中所学习的主要是“作曲”,或干脆说是“作曲技术”——如何运用“四大件”作曲技术使一部音乐作品具有自身结构的完整性(一种基于“自律论”的完整性)。至于说,如何进行“音乐创作”在五年的学习中并未得到系统的学习。这就意味着,“四大件”加“一对一”的课程体系,旨在解决“作曲技术”问题,而不是“音乐创作”问题。在这种境遇下,一个学生要想获得一位作曲家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并对“音乐创作”及其相关的艺术和美学问题有所把握,主要靠课外的习得或感悟,而不能依赖相应课程的教学。纵观新中国六十多年作曲专业的教学就不难发现,那些在学生时代就能写出成功作品、熟练进行“音乐创作”的学生,如20世纪6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何占豪、陈钢、王西麟,8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郭文景、周龙、叶小纲、谭盾、瞿小松等,他们在读期间的写作都不是机械的“作曲”或单纯的“作曲技术”训练,而对“音乐创作”及其相关艺术和美学问题已有了一定的理论思考,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同样,所有成功作曲家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上的娴熟,而更取决于他们对“音乐创作”及其相关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在本科学段作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增添一些探讨音乐创作一般规律并将作曲技术理论与艺术或美学理论相结合的“音乐创作理论”课程呢?也许有人会说,现今高等音乐院校不是已都开设了“艺术概论”、“音乐美学”及“音乐欣赏”、“音乐史”等与音乐创作相关的课程吗?不必重复设置。但应看到的是,一些公共课程大多只讲一般原理,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具体教授如何运用音乐形式和手段进行艺术表现、塑造音乐形象,更不可能探讨作曲技术理论与艺术或美学理论的链接。故本文认为,在作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增设这种“音乐创作理论”课程是完全必要的。这样一来,作曲专业的课程体系就是一个立体化的课程体系,它不仅保留了既有“四大件”加“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而且增设了一些旨在探讨音乐创作一般规律、力图实现作曲技术理论与艺术或美学理论相结合的“音乐创作理论”课程,进而实现从单一技术训练到综合素质培养的转型。
三
那么,这种着眼于作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音乐创作理论”课程应是怎样的呢?本文认为,“音乐创作理论”课程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音乐创作与创意设计”、“音乐形式与音乐风格”、“音乐表现与音乐形象”。这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至于说“音乐创作”中那些更高层次的文化与美学问题则只能让学生在课堂之外进行探讨。
显然,这种“音乐创作理论”课程,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课程,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其中的“理论”就是与“音乐创作”相关的音乐基础理论、音乐美学理论、艺术哲学理论;其中的“实践”则是古今中外“音乐创作”的实例(尤其是当代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总体而言,“音乐创作理论”课程应以“实践”为主。这就意味着,通过对“音乐创作”实例(主要是具体的音乐作品)分析,讲述“音乐创作与创意设计”、“音乐形式与音乐风格”、“音乐形式与音乐形象”等“音乐创作理论”问题。具体地说,“音乐创作与创意设计”主要讲述“音乐创作构思”或称之为“创意”,其主要内容是音乐创作构思过程中有关“题材与内容”、“形式与体裁”、“风格与技术”、“受众与传播”的设定与选择。这主要是一个基于艺术理论及美学的教学层次,旨在使学生在创作一部音乐作品之前,对这部音乐作品选择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思想内容、选择何种音乐体裁、运用什么表现形式、所呈现出的音乐风格、所运用的音乐技术及音乐作品的受众定位及作品的传播渠道、传播方式等具有一种较为深入的考虑。这种“创意设计”的教学,完全可通过对具体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的分析来进行,即所谓“案例式教学”。“音乐形式与音乐风格”的教学,则是一个基于音乐及作曲技术层面的教学,旨在使学生在完成一部音乐作品的“创意设计”后,学会如何把握这部音乐作品的结构形式和音乐风格。这就在于根据“创意设计”选择作品的结构形式,把握作品的音乐风格。其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一般包括“音高组织”(pitch organization)及其原则、和声结构及形态、调性结构及布局、复调结构及其形态、音响结构及其配器、曲式结构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力因素”)等,还包括一部音乐作品最主要、最突出的技术特征。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则较为复杂。所谓“音乐风格”,一般包括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对于音乐而言,还存在一个“技法风格”。无疑,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必须充分考虑这部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即根据其题材内容,找到适合表达这种题材思想的风格性因素,或是某个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音调特征,或是某个特定时代、特征流派的音乐语言,或是某个特定的技术特征,等等。不难发现,无论是选择结构形式,还是把握音乐风格,均可依赖对具体音乐作品的分析。“音乐表现与音乐形象”的教学,则又要回到艺术理论及美学的层面。这主要是探讨一部音乐作品如何通过具体可感的“音乐形式与音乐风格”,完成音乐的艺术表现,塑造艺术形象。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对于“音乐创作理论”课程而言,则主要是剖析音乐表现和音乐形象的实质,讲述不同音乐形式、音乐风格的“语义性”及其对于完成“音乐表现”、塑造“音乐形象”的“类比”意义与“象征”意义。这一层次的教学无疑也可通过具体的音乐作品进行“案例式教学”。以上是“音乐创作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一门课程,也可以说是多门课程;可以通过常规的课堂教学,也可以通过讲座来实施。
“音乐创作理论”作为一门课程或一个由多门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应设置在“作曲技术理论”(传统的“四大件”或“五大件”)课程之后、“毕业创作”之前,与“一对一”的“专业主课”教学平行。“音乐创作理论”与其他课程一起,共同构筑一个立体化的课程体系,在从单一技术训练到综合素质培养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本文所阐述的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本科学段课程设置的基本构想。
①陈应时《对于改进作曲技术课教学的一点浅见》,《人民音乐》1964年第9期,第30页。
②赵晓生《阿炳启示录》,《音乐艺术》1994年第1期。
③例如第二届全国和声学学术报告会(1987,武汉)、第一届全国复调音乐学术会议(1989年,西安)、第一届全国曲式与作品分析学术会议(1990,北京)等。
④薛艺兵《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黄钟》1998年第4期,第3—8页。
⑤王飞《我国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之我见》,《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1期。
潘祖君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