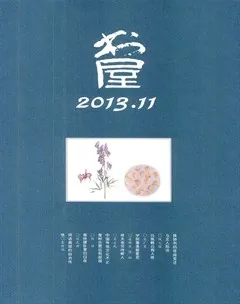漫话“渔樵”
“渔樵”,在汉语词汇里是一个奇妙的组合。这本来是两个动词,意为打渔和砍柴,是两种极其常见和平凡的职业和劳动。合在一起,又可以视为两个名词看待,即渔父和樵夫。这两种劳动者又被文人合二而一,并被赋予了极其高雅、旷达甚至超凡入圣的品格,仿佛他们无所不知,而且具有哲人的智慧。就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时候遇到的那位渔父吧,好心地问他怎么到了这一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导他说:“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不听劝告,说什么“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见他这样固执,只好苦笑着敲起船帮离去并且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再没有什么话说了。我们不论赞成不赞成渔父的说法,他的形象和言谈都是高雅的。高雅的渔父还有的是,姜子牙、严子陵不都是“钓叟”吗?而最风雅的渔父,大概要数唐代的张志和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他这首《渔歌子》谁不耳熟能详?有了这么多留名青史的“渔父”,难怪“渔”要和高尚以及学识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元散曲里美化和拔高渔夫的小令多得惊人,且看下面两首:
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夫
黄芦苇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白贲:(正宫)鹦鹉曲·渔父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幺)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蓑衣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两首都强调渔父“不识字”也那么高雅。至于樵夫,识不识字也是一样。请看马致远的《(南吕)·金字经》:
担头担明月,斧磨石上苔。且做樵夫隐去来。柴,买臣安在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
砍柴卖柴的朱买臣当然是樵夫中的佼佼者,但已经不复存在。“空岩外,老了栋梁材”,是说自己和别的朋友们都怀才不遇,只能隐沦来做樵夫。满腹牢骚,溢于言表。但是,没有牢骚、隐于山林的樵夫还是有的,且看赵显宏的《(中吕)满庭芳·樵》:“腰间斧柯,观棋曾朽,修月曾磨。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不饶过猿枝鹤窠,惯立尽石涧泥坡。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
“观棋曾朽”是说,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数童子下棋,站在一旁观看,一局终了,拾起斧头欲去,斧柄(柯)已经腐朽。回到家里,无人相识,原来已经过了百年。这表明,樵夫会遇到神仙,别人就办不到。“修月曾磨”,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月亮由七宝合成,人间有八万二千户给它修治,苏轼就有“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的诗句。可见樵夫都是高手。“连理枝”比喻夫妻恩爱,樵夫不忍锉伤,只在人迹罕至的猿枝鹤窠、石涧泥坡挥斧头,说明他们为人的善良。樵夫王质遇仙和武陵渔人误入陶渊明的理想国桃花源,可谓无独有偶,异曲同工,而刘子骥和太守等士大夫就与桃源无缘,也说明“渔”和“樵”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
渔和樵原本是两码事,为什么被文人,特别是失意、退隐、有些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文人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把上举那些高雅脱俗的渔父和樵夫当成了自己心目中“渔樵”们的代表,或曰理想的化身。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樵夫和渔父是和山水最亲近的人,正如白朴所说的“乐山乐水总相宜”,所以他们就成了文人们讴歌的对象,把他们看成超然于世局物外、远离名缰利锁、却又像看戏一样旁观兴亡成败、当作茶余酒后谈资的理想化了的人物,亦即自我情怀的载体,说什么“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张昇《离亭燕》);“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陈与义《临江仙》);“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麽渔樵没话说”(马致远《夜行船.》)。杨慎的《临江仙》在说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后,接着不是也来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吗?就连苏轼,也在《前赤壁赋》里说:“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他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曾开荒东坡,可能确实过了一段“渔樵”的生活。因此,“渔樵闲话”成了稗官野史的天地,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一点,元代散曲作家胡祇遹的一首《(双调)沉醉东风》,可以被认为其中的“代表作”:“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又是两个“不识字”的渔父樵夫,但已经是“渔樵士大夫”了。在实际生活中,渔樵们和士大夫们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前者所过的日子决不会和后者同样悠闲和潇洒。但在某些士大夫的笔下,前者尽管大字不识,却可以德才兼备,博古通今,而且饮酒食鱼,有着“不虞匮乏”的自由,成了当时的天之骄子。我们读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再读他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这是诗意的栖居,和生活实际相差甚远。事实上,古代的渔民比普通的农民还苦。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在贪官污吏和渔霸地头蛇的盘剥勒索下,是不要命地去求一线生机的。至于樵民,请看白居易的《卖炭翁》吧:“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瞧吧,这就是樵夫们过的日子!这样的“渔樵”,能够有什么财力学问、闲情逸致去饮酒品茗、说古道今呢?因此,这些远世虑、傲王侯、“帝力与我何有哉”的“无怀氏之民”,决非现实中的人物,而是理想化的幻象。其所以如此,是和文人即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士”,也就是“文人”,不像西方还有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技术人员、议员等等可以具有许多身份和选择多种职业。他们唯一的进身之阶就是通过科举“学而优则仕”。在这条独木桥上绝大多数都仕途蹭蹬,沉沦下僚。少数人即便中举得官,也会由于仕途凶险,往往因为正直、敢言而遭到贬谪、远黜、放逐之祸,上面提到的柳宗元、苏轼、杨慎不过是几个例子,至于蒙冤而死的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通过儒学的考试中举的,而儒家固然主张“入世”,却并不排除“出世”即退隐的必要性,如孔子就再三地说过这样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况他们在服膺儒教的同时,又无不深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遗世独立、自给自足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例如“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孟浩然总算是个地道的“隐君子”吧?其实早年的他是很想求得一官半职并因而进行过“干谒”的,这表现在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九龄)》那首诗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但倒霉的他在王维那里碰上了唐明皇,问他有什么新诗,他竟以《岁暮归南山》作答,中有“不才明主弃”之句,惹恼了皇上,这就彻底地断绝了他的仕途,不能不在《留别王维》里慨叹“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了。至于王维,又是个朝中的隐士和佛教徒,可称为富贵闲人,《赠张少府》最能表现他的行事和思想:“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里,他又回到屈原遇到的那位渔父跟前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论怎样廉洁正直,热衷事功,自我宽解,力求旷达,也难免时有退隐、避世甚至看破红尘、历史虚无之感,因而借酒浇愁,吟诗解闷,寄情山水,托身渔樵,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逋逃薮,有点像现在具有共同意趣的文化人经营的那种沙龙,却没有固定的地点和召集人,而且不会有什么危险。到了元代,广大的汉族文人备受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成了连“九丐”都不如的“十儒”,亦即最下等的贱民,加上行之千年的科举也被废除,从而断绝了他们的出路,不得不隐沦于勾栏市井、花街柳巷或山林农舍,写他们以退隐、牢骚、怀古、和历史虚无主义为主题,“渔樵闲话”为“迷彩服”的散曲,成为唐诗宋词之后文艺园地的一朵新花。但由于他们自我封闭,脱离现实,以历史虚无主义对待过去、现在以至于未来,完全没有对普遍的民生疾苦有所担当和思虑,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在整体上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大大地落后于前辈的唐诗和宋词,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诗中最灰色的一页。现在,蒙元帝国已经成为历史,散曲作为一种诗体却还存在,虽然在文学创作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倒是“渔樵情结”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最后,仅以笔记式的拙作《(中吕)升平乐》一首,聊表我对“渔樵现象”的浅见:“且假渔樵为作嫁,饮酒吟诗更品茶,通今博古闲磕牙。讥评将相,笑傲王霸,唯我独尊,谁也不怕。(幺)文人失意远堂厦,退隐田园近桑麻,青山绿水寄生涯。胸中块垒,借酒浇下。正是渔樵,最堪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