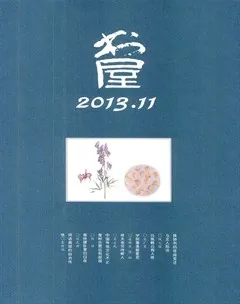有关《茶花女》的碎片和浮想
五月迷人之夜,中国第一个以“第一女主角”身份进入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张立萍,在杭州大剧院歌剧舞台上,以美妙歌喉向全场欣赏者倾诉茶花女的凄美爱情悲剧时,我正在住宅的台灯下重新翻阅《茶花女》小说。心想:今夜杭城,至少有一千六百名歌剧观众和一个小说读者,在重温(或初尝)小仲马与威尔第分别塑造的这个催人泪下的艺术形象。今年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二百周年诞辰,世界各地竞相上演大师根据同名原著改编的歌剧《茶花女》。165年来,这个经典形象及其爱情故事,征服了并还在征服全世界,也勾起了我半个多世纪来的“玛格丽特情结”(注:《茶花女》女主角在小说、话剧里叫玛格丽特,在歌剧里叫薇奥莱塔)。
记忆碎片
第一次接触《茶花女》是十四岁那年。一个假日下午,路过青年路口金门电影院(后改名新中国剧院),看到《茶花女》电影广告,那时只热衷于好莱坞打斗影片,可犹豫一下之后还是跨进门去,心忖或许这是个神话故事——一朵茶花变成了一个女孩子吧?
我是红着眼睛走出电影院的。纯洁美丽又无限悲怆的情愫,填满了我这个懵懂少年的胸腔。
事后知道这部影片是由乔治·顾柯执导、来自瑞典的好莱坞巨星葛丽泰·嘉宝和罗伯特·泰勒联袂主演的,高贵美丽的嘉宝与英俊潇洒的泰勒,演技精湛,珠联璧合,使这部影片成为经典。虽然许多年后也看过法国、波兰等国的多个彩色版本,但总觉得没有一部超得过这部黑白片。未知是否先入之见的缘故。
感动之余我猜测:这样的佳片一定是根据小说拍摄的。我一家家书店去寻找,终于在如今官巷口新华书店(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启明书店发现了。那一瞬间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这是一个印刷装帧都显粗糙的版本,纸张很差,字体排得密密麻麻,顶天立地,但对我来说赛过瑰宝,立马回家向妈妈讨了零钱又赶回书店买下。还记得店员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因为当时穷学生往往只看不买,了为驱赶“看白书”的学生,店员常常拿鸡毛掸子朝着学生翻看的书粗鲁地掸灰……
小说接连两夜读完,一边读一边泪流满面,这是生平第一次为小说哭泣。这时我知道了《茶花女》小说最早已有林纾根据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译”成的版本——《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还在小说之后写了话剧本(几经周折才出版),我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剧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赛过图书馆,允许读者随意阅读,并且有供读者使用的桌椅,我在那里读完了这本书。剧本结构严谨,可没有小说动人,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玛格丽特不像小说中那样孤独地魂归离恨天,而是死在及时赶到的情人怀抱中(恰似电影描述的一样)。
从那之后,我一直盼望能看到话剧版的《茶花女》。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某剧团来杭公演《茶花女》了。我兴冲冲赶往新中国剧院(即当年的金门电影院),结果大失所望。《茶花女》剧名没变,剧情差不多,可话剧却成了沪剧,场景移到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名、地名全部中国化了。——我最恨的就是把外国戏中国化,总觉得不伦不类,当时还写了篇歪评在报上大放厥词。
让我大开眼界、欣喜若狂的是,1979年,中央歌剧院来杭公演的《茶花女》。少年时代对茶花女的美好记忆,穿越沉重岁月重新燃烧。
当晚,杭州剧院座无虚席,多数杭城观众第一次凭借威尔第的旋律和歌唱家们的歌声,如痴如醉领略了十九世纪巴黎那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观赏中央歌剧院不同歌唱家的表演,与李光羲、王信纳、管自文成了朋友。一天,去剧院买票,恰逢管自文来票房,就相互交谈起来。管自文说,演唱歌剧是要付出生命的,第一次演《茶花女》时,泣不成声,根本无法唱下去而只好终止。每次演完都一时无法从角色中走出来,觉得自己已经跟茶花女融成一体了,“好多歌剧演员就是这样死在舞台上的”。
管自文还说,现在有些年轻演员只注意演唱技巧,缺少感情投入,听起来声音很好听,但没有内在的东西。说着,她轻声示范,薇奥莱塔咏叹调唱了没几句,眼泪就夺眶而出……我暗忖:这就是艺术家的虔诚!
彼此谈得投入,随后我们又到剧院办公室继续交流。她说:“真奇怪,我感觉咱们好像很久前就相熟了似的。”我想,正是《茶花女》的魅力瞬间拉近了观众跟歌唱家的距离。
若干年后,我有幸在上海大光明影院连看了两场多明戈和斯特拉塔斯主演、用意大利语演唱的《茶花女》歌剧电影,那当然是世界级的表演,但至今留存在我印象中的,却还是中央歌剧院的那出《茶花女》。
享受哀伤
爱与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想,《茶花女》该是体现此言最为典型的佐证。爱情是美丽的,死亡的介入更使爱情升华到圣洁的层面。难怪以死亡告终的凄美爱情故事成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主流。记得当年电影广告是这样宣传美国爱情片的:“缠绵悱恻,哀感顽颜,超凡入圣,无上文艺巨片。欲观从速,以免向隅。”
嘉宝的《茶花女》、琼·芳登的《谪仙怨》、考尔门的《死吻》(原名《双重人格》)、某某的《孽海花》等等,都属“缠绵悱恻,哀感顽颜”之类。
人真是奇怪的东西。在现实生活里,没人喜欢悲剧,力图避开痛楚哀伤;可在艺术欣赏上,喜欢悲剧的人远众于喜剧爱好者,力求“悱恻”、“哀伤”、“潸然泪下”。人们在对艺术形象悲苦命运流淌的同情眼泪之中获得快感,泪流越多,快慰越大。“苦戏”广告如称此剧能让你“哭湿三块手帕”,就是对这个戏的上佳评价,也是抛向看客的巨大诱惑。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各地观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涌往影院,为《卖花姑娘》、《妈妈再爱我一次》慷慨挥洒热泪,换回巨大情感满足的轰动事实,堪称悲剧艺术魅力之有力明证的典型。
看看,在生活中避免痛苦,在艺术上追求哀伤——这就是现实与艺术的差别之处。两者的不同还在于“原料”与“成品”存在的差异。
《茶花女》的成功,人们在欣赏之余,总有浓郁的兴趣去探究它是用怎样的“原料”制成的: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是谁?除了小仲马自述之外,后人多方探究,终于厘清了来龙去脉。原来玛格丽特的“模特儿”是一位出身低微的诺曼底贫穷的农村姑娘,名叫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十五岁时被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带到巴黎打工,凭她的天生丽质和聪明超常,进入大都会声色场所,改名玛丽·杜普莱西,渐渐成了一名受公子王孙竞相追逐的名妓。小仲马在杂耍剧场看戏时与她一见,就被她的美色和特殊的气质所迷恋,坠入了一场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局的恋情。小仲马这样评价自己为之神魂颠倒的情人:“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小仲马只是单方面动了真情。玛丽却常常移情别恋,轮换着接待围着她转的一个又一个浪荡公子。她真正要死要活爱上的不是小仲马而是匈牙利天才钢琴家李斯特。为了跟随这位外国艺术家周游世界(务须有一个与李斯特相匹配的体面身份才能与之公开露面),她不惜利用佩雷戈伯爵的感情跟他结婚而获得“伯爵夫人”的头衔。遗憾的是李斯特始终没有带她出国。患有肺病的玛丽·杜普莱西二十三岁在巴黎香消玉沉时,李斯特正在基辅,于热烈的掌声中成功地演奏完《邀请华尔兹舞》。
现实生活中,小仲马是觉得玛丽再也无法回到正路上来而离开她的。也不存在小仲马父亲劝阻玛丽离开自己儿子的情节(玛丽还曾有过引诱大仲马的举动)。总之,小说是精心剪裁了事实、大大美化了人物的。小仲马以自己真挚情感,将巴黎声色场所的一场寻欢作乐,提炼、升华成一段“超凡入圣”的爱情故事,塑造成了一个撼人心魄、魅力永恒的艺术形象。我十四岁时初赏乔治·顾柯导演的《茶花女》黑白电影,玛格丽特对阿尔芒说的那句台词:“我无缘拥有幸福。让我活在你的心里好了。那就什么人都看不见我了。”至今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而这个形象的原型也成了丰富人类文化的一个亮点。如今到巴黎的茶花女粉丝们,想必都会乐意去蒙马特公墓拜访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鑲嵌着茶花和酒杯的玛丽·杜普莱西墓。这是这个烟花女子对世界的贡献:没有她,也就没有茶花女。
《茶花女》叙述了美好爱情。但世界上真有永恒的美好爱情吗?我想了又想,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美好爱情只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中被截取的最佳的一段!由于死亡的介入,茶花女故事嘎然中断,被切下的这一段正是阿尔芒与玛格丽特恋情中最最动人的一段。它足以代表爱情的纯洁美好。试想一下,如果让故事继续下去,会有好结果吗?
小说获得全球感动,人人都谴责阿尔芒父亲粗暴干涉儿子的婚事。但我弟弟赞同老杜瓦尔。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难以同意自己的子弟去跟一个挥霍无度的妓女结婚的。我曾与弟弟争论了好久,最终我认同艺术跟现实是不同的。有些东西,只能停留在艺术欣赏之上。这是人的虚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