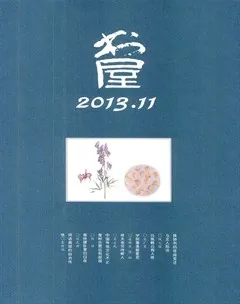科技宰相苏颂
一
苏颂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宰相;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在以官为本、以权为准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属于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与雕虫小技。像他这样政治、科技并举的“双料人才”,在中国古代社会,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他那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故居芦山堂,大门两旁有副楹联写道:“尚书御史翰林第,将相公侯科学家。”
苏颂活了八十二岁,别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即使今天,也算高寿。表面看来,苏颂左右开弓,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其实,他的一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风光”。
苏颂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十三岁考中进士,第二年任宿州(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后任知县、馆阁校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虽时上时下,辗转于婺州、亳州、杭州、濠州、沧州、应天府等地,但总体而言,还是不断升迁;直到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六月,年已七十三岁的他,擢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掌领尚书省、中书省政务,统管六部。隋唐时期,皇帝为了控制相权,将宰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部分,宋朝沿袭如旧。因此,苏颂所任之职,就是实际上的宰相。须发花白的他,好不容易荣登百官之首,可不过大半年时间,即元祐八年(1093)三月,又遇党争,无辜受牵,遭到弹劾。洁身自好的他,认为高居相位,必须受到朝廷所有官员的尊重与拥戴,一旦出现物议,则应激流勇退。因此,他当即上书,主动请辞。宋哲宗、高太后一再挽留,苏颂毫不恋栈,连上三书,辞去相位,离开汴京,出知扬州。也就是说,他在宰相位上呆了仅仅九个多月。两年后,苏颂以中太一宫使的荣衔致仕,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病逝。
尽管没有突出的政绩,没有显赫的功勋,可苏颂忠于职守,为人正直,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就连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也对他盛赞、仰慕不已,撰文称他“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勳府”,“以是心每慕其为人”。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颂任地方官时,总是关心民瘼,体恤百姓,尽其所能地“惠爱于民”。比如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不久,马上奏请疏浚自盟、白沟、圭河、刀河等四条河流,以防水灾;知沧州时,疏浚沟河、支家河等工程,解除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在杭州知州任内,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自来水”了;在淮南转运使任内,盐价上涨,又赶上一场饥荒,苏颂不仅降低盐价,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以致神宗皇上对他赞赏有加:“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
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还反映在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农田受灾而哀愁:“滂沱连月雨,愁叹斯民病。已紊四时和,更伤群物性。垄麦将萎摧,况值风威劲。我愿天地心,慎举阴阳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无复三月中,惨惨行冬令。”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直向岁寒期茂悦,肯同时俗论甘辛。优游且做江南令,惠爱于民此最亲。”
苏颂还参与了不少外交事务,或为伴送使,或任生辰使,虽职务有别,但都是出使辽国。他遇事镇定,随机应变,每次都不辱使命。回国后,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对此,《宋史·苏颂传》有所记载。当皇帝神宗问及辽国的“山川、人情向背”时,苏颂答道:“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二之意。”他认为宋、辽两国应继续和平相处。“神宗然之”,认可、采纳了他的外交建议。
出使辽国,苏颂收获颇多,他根据自己的出使路线及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创作了《前使辽诗》三十首、《后使辽诗》二十七首,记载辽国的山川风光、道路交通、农牧特点及风俗民情。这两组外交组诗,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除文学意义外,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后来,他以宋辽外交往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编写了一部名为《华戎鲁卫信录》的书籍。
北宋后期,政局动荡,党争十分激烈。苏颂为官之时,先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争;哲宗朝时,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新法遭废,守旧派受到重用,其内部又形成以洛阳人程颐等为主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为领袖的朔党,三党互争,形同水火。苏颂为官五十多年,历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各党各派都在争取他,比如王安石大刀阔斧地革除旧政,希望他能“加盟”改革派;苏轼是他的同宗之侄,曾一同坐牢,可谓患难与共,亲情加友情,蜀党自然极力拉拢他;刘挚与他同署办公,两人诗文互答,政见颇同,朔党将他视为同道……可是,苏颂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位居京城担任中央高官,始终坚持不树党援、不入派系、处事以公、不营私利、洁身自好的政治原则。
不介入党派系列,苏颂势单力孤,要想办成一点大事,形成规模效应,却无人支持响应,这,恐怕也是他政绩平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苏颂孤身一人在风波险恶的官场奋斗,也就难怪屡经挫折了。纵观其政治生涯,曾有过两次生死考验。
第一次是宋熙宁三年(1070),任知制诰时。
知制诰之官始于唐代,专为皇帝起草、撰写诸如册立太子、任免高官、宣布征伐等重要的诏书、文诰。知制诰又称内制,与起草一般诏令、文书的外制——中书舍人相对应。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王安石颁布新法,受到朝野上下的争议乃至反对。朝廷急需得到基层支持,于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经人推荐召至汴京,拟任命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
宋神宗批示李定任职的词头之后,送中书省,正值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当班,他认为李定不符合任命要求,拒绝起草诏书,并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神宗收到封还的词头,当即免去宋敏求官职,并御批道:“速送别官命草。”于是,苏颂被推到了“前台”。他没有被神宗的愤怒与权威所吓倒,陈述李定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举荐失当的原因:资历不够,政绩不显,不符合选用擢拔规定,违反了宋朝选官旧制。因此,他不仅反对李定任官,还为宋敏求辩护。神宗态度坚决,命令又一当班的工部郎中、中书舍人李大临起草诏书,没想到他也封还了词头。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人的一致封还,被人称为“三舍人议案”。
这一任命反反复复多达八次,双方僵持一月有余,最后以三舍人免职、神宗让步而告结束。
苏颂因恪尽职守、不为身谋,被称为“三舍人之冠”。他这样做,也为自己埋下了隐患,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受迫害囚入牢笼,面临人生的第二次生死考验。
元丰元年(1078)五月,苏颂在权知开封府任上遇到了一桩案子。
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住持行亲,说他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官员孙纯。苏颂了解到,原来是行亲花了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行亲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抵债。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行亲。苏颂认为孙纯讨账无可厚非,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住持支配也无不可。于是认定这是徒弟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纪,便以杖责罚处。
一般来说,案子一结,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有人却拿苏颂断的这桩案子大做文章,被城皇卒参了一本,状告他偏袒孙纯。御史台官员舒亶审理此案,他是李定的朋友;而此时的李定已升任御史中丞,是舒亶的顶头上司。“三舍人事件”虽然过去了八年,可李定总想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机会终于来了,他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李定与舒亶密谋,制造了一起冤案。
舒亶经过审理发现,苏颂与孙纯乃亲戚关系。两人既为亲戚,就可定苏颂徇情枉法的罪名。
原来,苏颂女儿刚刚嫁给同事李徽之子,李徽家族十分庞大,有数百人之多,如果“顺藤摸瓜”地牵扯,则可牵出孙纯是苏颂女婿李徽儿子的从妹之子这一“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苏颂当初判案时,并不知晓这一姻亲。于是,他被传讯到御史台,接受舒亶的审讯之辱。仇人为他寻出这么一个确实存在的远亲,哪怕百般冤屈,也有口难辩。于是,苏颂以故纵、偏袒孙纯之罪,受到惩罚——降职秘书监,出知濠州。
苏颂遭贬,离开京城赴濠州上任,可李定、舒亶却不肯罢休,对他继续加以迫害。一番策划,他们翻出苏颂元丰元年(1078)六月判决的另一桩案子——陈士儒案,送交大理寺重审。
这桩案子,因国子博士陈士儒的母亲被奴婢害死而起。陈士儒之妻李氏厌恶他的生母,常对奴婢们说:“博士母亲死后,愿意留下的,增加薪金;想要离开的,赠送银钱。”法吏审案时,认为李氏虽暗示奴婢杀母,但没有明言,情虽不容,罪不至死。作为主管官员的苏颂,其态度是不以行政干预司法,由法官以事实为准,依法判决。
案子了结上报,被大理寺驳回重审;再次上报,又被驳回。几经反复,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就连神宗皇帝闻知此事,一次上朝时对苏颂道:“听说你和法官想对陈士儒一案宽大处理,奴婢杀母,此乃人伦大恶,要穷究到底,不可纵容。”苏颂回道:“办案当以事实为准绳,对当事人,我既不敢宽容,也不敢加重处罚。”
陈士儒案久拖未决,一直拖到苏颂受贬赴濠州任职也没有最后判定。此案一经翻出,苏颂便难以逃脱李定、舒亶编织的第二次罗网与冤狱。他们仍像上次那样,从亲友关系入手予以加害。一番摸排,李定、舒亶又拎出了一条特殊的关系网:苏颂与吕公著是好朋友,而陈士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吕公著的妹妹。这样一来,苏颂又成了罪人,且“言之凿凿”:原来他在好友吕公著的请托下,有意宽纵李氏,哪怕皇帝过问,也不予理睬。
元丰二年(1709)九月,苏颂从濠州回到京城。此次并非荣迁,而是以待罪之身受到押解,关在汴京御史台监狱。
最后,苏颂冤狱在神宗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才得以宽大处理:释放出狱,撤职归班。
三
朱熹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首仕泉州府同安县主簿时,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有感于他的故乡同安已不知其人,“虽其族家子不能言”,遂建苏公祠以作纪念。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为立苏颂宰相祠堂,写了五篇相关文章,对其科技成果只字不提,他所看重的,是苏颂的平生节俭,公正清廉;他所弘扬的,是其道德修养,“然而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他建祠的目的,是振兴教育,扭转社会时风。
由于朱熹的提倡,苏颂这位乡贤渐为当地百姓所知,其学识风范也在不断地激励、鼓舞后人。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位于同安孔庙内。进入祠堂,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唯公一人。”横幅为“正简流芳”。正简,宋理宗朝时对苏颂的追谥。
其实,苏颂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推崇,主要在于他那卓越的科学贡献。
苏颂刚入中央做官时,先后担任馆阁校理、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太常博士等职,其主要工作,就是编撰、校正古籍。他埋首其中,誉抄校勘,一干就是九年。家中所藏古籍,大多为他亲手抄写。这项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培养了他认真求实的科研精神、刻苦沉潜的科研作风以及扎实渊博的文献功底。
苏颂的主要科技成就,一是研制新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二是主撰药物学著作《本草图经》。正是天文学、医药学这两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得他在科技方面独自一人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水运仪象,天文学名词,专业性较强,即使今天,如果对天文学不感兴趣,一般人也难以弄清其内容与性质。仪,指浑仪,一种古代测量天象的器具;象,指浑象,一种球面星图,形状与地球仪相似,上面绘有星象图。水运,以一种漏水驱动装置,促使浑仪或浑象转动,与天上的恒星同步运行。水运仪象,是古人在天文观测中使用的一种人造计时器,现代称之为水力天文钟,其原理是以漏水驱动浑仪或浑象,自动计时。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人就设计了一种名为日晷(又称日规)的计时器,但它在阴天、夜间不起作用;而水运仪象,则是一种更为科学的,以非天文的物理过程作依据的计时器。
苏颂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是将浑仪、浑象及报时装置组合为一体,由水力推动的天文仪器。难能可贵的是,苏颂建造的这座高约十二米、宽约七米的巨型天文仪,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之上的。为此,他撰有《新仪象法要》一书,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零部件形制、总体构造,并配有相应的设计图纸及文字说明。水运仪象台被毁,后人正是根据这部传世之作,“按图索骥”地成功复制。
古人重形象思维,求技巧实用,科学理论与科学精神十分匮乏。而苏颂特别强调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讲究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坚持理论与实践并举,在古代显得尤为珍贵。
关于水运仪象台的原理与结构,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有所说明:“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这是水运仪象台的结构组成;其运转模式是“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至于效果,则是“备制二器而通三用也”。
苏颂创制的水运仪象台,一个最大的突破与特征,便是实现了观测的自动化。他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层置放观测天体的浑仪,下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中层是使浑仪、浑象转动的机械装置。水流冲激轮轴,仪器开始运行,水运仪象台具有三重功效: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示牌、准确报时。
正是水运仪象台与《新仪象法要》,为苏颂争得了五项世界第一。
第一、二、三项世界第一,均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高度评价与定论,他认为“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因水运仪象台的顶部设有九块活动屋板,他认为苏颂是世界上最早设计、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又因水运仪象台可以循环往复地等速度运转,这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是现代钟表的先导与前驱。
《新仪象法要》中绘有水运仪象台的全图、分图、详图等透视图、示意图六十多幅,绘制机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种,是世界上留存至今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机械设计图纸,为苏颂创下了第四项世界第一。
《新仪象法要》绘有星图十四幅。为免图象失真,使绘制更加精确,苏颂采用圆、横结合等新的绘图法,绘星一千四百六十四颗。而欧洲晚四百年观测到的星数,也只一千零二十二颗。西方科技史专家认为:“从中世纪直到十四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苏颂由此创造了第五项世界第一。
水运仪象台落成之后,苏颂又研制了一台假天仪。假天仪也叫天象仪,是一种普及天文知识的仪器。与人们站在天球外观察天象的浑天仪不同,假天仪则可进入仪器之中,看到逼真的人造星空。因为这样的天象是人为模仿假造的,故名“假天仪”。在古代,欲将天象模仿制造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技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据相关资料记载,苏颂所造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振铎先生研究复原了苏颂这座假天仪,并发表论文《我国最早的假天仪》,后又提出苏颂所造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假天仪,也属世界第一。这,便是苏颂创立的第六项世界第一。
苏颂的第七项世界第一,是编撰了《本草图经》一书。苏颂在研读《内经》、《外台秘要》等历代医学专著,校订整理《神农本草》、《灵枢》、《素问》、《千金方》等医典八部,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经过四年艰苦努力,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图经本草》二十一卷的编撰工作。
《图经本草》所收药物九百三十三种,全都绘有图样,注明花形、果状、效用等,对药性、配方提供依据,纠正了历代本草书籍中的谬误。该书集古代药物学之大成,新增药物近百种,附单方上千个,并一改过去本草著作的单纯药物学性质,将其提升到博物学的高度。明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便得力于这种博物学特性,他对《图经本草》不仅赞扬有加,还大量征引。李约瑟认为“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的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十五世纪才出现的大事”,而十一世纪《图经本草》就已问世,在同类医学著作中自然名列世界第一。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图经本草》的编撰,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并非苏颂一人所能完成。但苏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两项创世界之最的成果,都是在他担任科技官员时取得的。
第一次是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苏颂最初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便挑起了主持编写《本草图经》的大梁。
作为一名科技官员,既要懂行,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又要做好管理工作,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所有科技人员的潜能与积极性,苏颂正是二者兼顾;他既重历史,也重当下,开展全国性的医药普查工作,发动广大医师、药农提供医药标本、图谱;既进行从书本到书本的校订,更以实物对照书本,相互参证,纠正混乱,去除错讹;最后由他严格把关,统一审理,重行撰述,于是才有出类拔萃的《本草图经》问世。
苏颂第二次担任科技官员,是在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受诏定夺新旧浑仪。
虽然有了主持修撰医书的组织经验,并且儿时苏颂就对天文极感兴趣,时常把玩家中收藏的浑天仪小样,渐渐心有所悟;他于历法也有研究,十六岁便作有以天文历法为内容的《夏正建寅赋》;参加进士科考那年,试题为《历者,天地之大纪赋》,结果苏颂名列第一,此文流传至今。尽管如此,苏颂内心十分清楚,这次所担当的重大任务,显然比第一次更为艰巨。
他一上任,便成立了“制造水运仪象所”,所有成员,都亲自物色、考核、确定。作为一名伯乐,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这匹难得的通晓天文历法的“千里马”,立即奏请皇上将他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在外地寻访人才时,苏颂发现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擅长仪器制作,便调他“专监造作”……科研发明,人才是关键,苏颂深明此理,将一大批得力干将“网罗”在自己身边,量才器使。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宝贵人才,不仅成为他的“左右手”,更为研制水运仪象各显其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研制方面,苏颂宏观决策调控,微观把握执行,反复实验,认真严谨,确保万无一失。他先做理论研究,与部下反复研究,由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从可行性上进行论证;再制作模型,进行相关天文实验;当实验成功,“候天有准”后,造成小木样呈报皇帝;尽管这些都没有误差,但苏颂并不急于建造实物,而是制造大木样,在尺寸大小、机件结构等方面,与将要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完全一致,演示实验,奏请皇帝派人鉴定;当一应准备工作按照严格的要求检验合格之后,苏颂这才命人制作铜造的水运仪象台,历经三年零四个月,终于大功告成。
苏颂“平生不信命术”,既重科学理论,也讲科学实践,提出了“合道尽理”的科学哲学命题。
除道德、科技外,苏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于法律、历法、教育学、地理学、水利学、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皆有较深研究,并创作了大量颇具文学价值的诗歌,他留下的两册《苏魏公文集》(苏颂死后赠司空魏国公,故名),里面所收文字,便见证了他丰富的思想与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