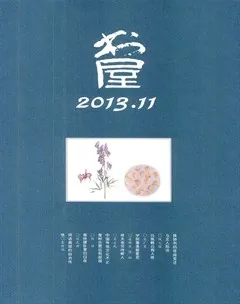题钟题(一)
《天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谢不周、张辉、李永平,整体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字数11.2万,161页,定价15.90元。
【钟题】 书中第一篇《太行山的笑话》未能写好。周作人杂诗“打油”一首有云:“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掐臂至见血,摇头作游戏。骗尽老实人,得无多罪戾。说破太行山,亦复少风趣。且任泼苦荣,领取塾师意。”肖跃华君读之,不知感觉如何也。癸巳初夏,钟叔河题于念楼。
钟先生七至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房子,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方一小块微明,可以让自己产生一点想象,因此他对天窗一直抱有好感。2003年从美国回来后,他写过一篇《天窗》,寄到一家报纸副刊如泥牛入海。后来周实、李永平先生让他将新写的东西编成一册,他便将它收了进来,全书亦以此命名,原拟叫《天窗集》,和已出版的《念楼集》、《偶然集》相衔接。可李永平先生觉得天窗之为物很有意思,却以不要“集”字为宜,他从善如流,只留下了“天窗”。但仍决定将五十七篇文章分为“念楼杂抄”、“天窗小集”。“《天窗》之外又开个小‘天窗’,所以不嫌重复者,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天窗的特别记念而已”。
“杂文要杂,散文要散,随笔要随心所欲”。钟先生的这些短文亦杂,亦散,亦随心所欲,但充满着渊博的学识,迷人的理趣,点石成金,引人深思。他自称“未能写好”的文章如此开篇:“中国山多,人也多。若问全国多少亿人最熟知的是哪座山,那一定是太行山。因为‘天天读’过‘老三篇’,都知道有一座太行山挡路,自己的任务就是‘每天挖山不止’,以期‘感动上帝’来把山搬走……”结尾则云:“太行山仍然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上帝却如尼采说的那样‘死掉了’。山本来是移不开挖不动的,移山填海,无非梦呓,何况并没有人真去挖过一锄头。”
“笑话”信手拈来,自然质朴,信是好文。
《小西门集》:岳麓书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曾德明,封面设计郏宝雄,字数20万,印数5000册,361页,定价35.00元。
【钟题】 长沙小西门,刘献廷称为“天下风景绝佳处”。跃华君曾服务此地多年,不知尚存在印象否?然“建设”日新,遗迹渐归澌灭正可惜也,癸巳清明后一日,念楼钟叔河。
该书从钟先生已刊行的十多本书中选出同类文章若干,加上尚未入集的几篇新作,共计六十七篇,另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和钟先生夫人朱纯的《关于“同人报”》、《老头挪书房》。书名循例取其一篇名,曰《小西门集》。“全世界最美的图书”设计者朱赢椿先生,曾表示愿为这本书作整体设计,亲自监制,代理出版。惜“天”不随人,未能如愿,但钟先生仍然十分感谢,“朱君所制的书衣我确实喜欢,希望今后还能有得到的机会”。
刘献庭(1648—1695)祖籍江苏吴县,生于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字君贤,一字继庄,别号广阳子,清初地理学家,著有《广阳杂记》。他康熙年间旅行湖南,对小西门有如下描写:“长沙小西门,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
我1983年10月入伍来到长沙时,地理学家笔下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早已荡然无存,三百多年的城市“建设”,小西门已成为长沙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鲜有人知道小西门曾改名黄兴门、坡子街曾改名黄兴街的历史掌故,连诗人们也想象不出这里曾有竹篱茅屋的踪影。我们中队在小西门附近的坡子街担负金库银行守卫任务,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人都想成为“万元户”的年代,装着真金白银人民币的押钞车进进出出,次数逐月逐年增多,方知市场经济发展之迅猛,国人的“行色匆匆”取代了“清雅淡远”,“物欲横流”淹没了“绝无烟火气”。喜耶!悲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