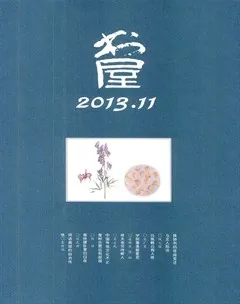王国维的“美学劫”
1907年,三十而立的王国维可谓意气风发。一方面,他的哲学修为日益精进,不仅对叔本华、尼采深研有得,还先后四次通读康德,自觉已领会无碍——纵有小碍,也应该是康德“其说之不可持处”。就现代哲学而言,懂得康德,百事可做。而在文学创作上,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相继刊行,王氏自评曰:“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三十自序·二》)。就当时文学界的反响来看,这一评价并非孟浪。既入康德哲学之门,又在文学上获得成功,正是左右逢源之际,王国维偏偏彷徨起来。下面这段文字,中国学人早已耳熟能详: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这段感慨有相当合理的背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哲学转型的动荡期,德国古典哲学被讽为“泥足巨人”,体系竞赛难乎为继;种种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哲学质木无文,面目可鄙;埋首做哲学史的梳理虽成功可待,毕竟心有不甘。歧路亡羊,王国维大有苦闷的理由。
“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一语值得深究。此种转移的前提,是文学能够提供哲学所不能提供的慰藉,一种哲学难以使之落实的理想境界。王国维对自身才性的评价是:“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与其说这是自谦,不如说是自剖心曲,王国维已打定主意不做纯粹的哲学家或文学家,而要在理性与感性、哲学与文学之间寻求新的定位,这岂不就是要做美学家?
何谓美学家?王国维既已否定了“纯粹之美学”(当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可信度,却又不青睐经验论美学,这美学家从何做起?要将此问题解说分明,须暂时回到叔本华。叔本华是德国哲学家中屈指可数的具有美学天赋者之一,与王国维可惺惺相惜。叔本华当然可以说是美学家,但他不是简单地继承了既有美学的传统,而是通过重构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极大地改造了美学的面貌。叔本华的哲学被称为悲观哲学,其核心是一种悲剧情境:人生而为人,所谓自由只是幻象,个人意志无时无刻不受世界意志的掌控,主体也好,客体也好,不过是森罗大网中的某一节点;但是,人总有机会跳出此罗网,与世界形成通透明澈的对视关系,此时一即是全体,全体即是一,欲求关系转化为纯粹的认识关系,主客、物我不过是一念流转。叔本华试图使人相信,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自身所受束缚,就有机会摆脱这束缚,实现所谓涅槃。此一观念对王国维诱惑极大。
1904年写作《红楼梦评论》时,王国维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将《红楼梦》揭示为“彻头彻尾之悲剧”。所谓悲剧,要义不在于能否摒弃大团圆结尾,而在于能否摆脱尘世牵绊,求取真正的解脱。王国维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向来就是“世间的”、“乐天的”,总是希望人间的矛盾能够在人间解决,所以不惜狗尾续貂,以餍阅者之心。哪怕是最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桃花扇》,也摆脱不了现世计较,其超脱不过是“他律”的超脱,其性质终究是“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唯有《红楼梦》能够“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故其价值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王国维虽为叔本华的超脱之境所吸引,但他并不相信个人真的可以实现彻底的超脱,换句话说,人可以死,但未必涅槃。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诘问:照叔本华的意志论,人与我的差别本是一种执念,我之意志本是世界之意志,如水之在川,那么仅仅一人如何实现超脱?身为词人的王国维,有两首词作正适合解说此一困境:
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独倚栏杆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两首词皆是从高处俯瞰。“可怜身是眼中人”,自以为超脱者仍在尘世之中,有点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成就感转瞬即灭,只有无聊的苦役日复一日。“闲中数尽行人小”,观世者仿佛跳出三界之外,然而风雨一来,上下同尘,最终被俗世时空俘获。王国维相信,“小宇宙之解脱,视大宇宙之解脱以为准故也”,所以解脱也是典型的可爱而不可信。但是,王国维话锋一转:
《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欢迎之也。
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救赎是面向个体的,既提供超脱的理想作为精神慰藉,又提供审美上的直接满足:“自己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此种期许或许只是一厢情愿,中国人未必能够从《红楼梦》中得到精神救济,他们能够理解何谓“出世的胸襟”,却未必能够理解悲剧式的毁灭。
王国维创作悲剧虽力有弗逮,但以悲剧之精神解说艺术却能深中肯綮。此种解说的微妙处,是将艺术内在的悖论阐发分明:艺术是超脱之境的现实化,而此境界本是不可现实化的。由此,艺术批评的工作首先就是要解说艺术作品如何自成一世界。作为审美客体的艺术作品虽有特定载体(一首诗、一幅画等等),却非实存之物,不在时空之中,因为其本质是纯粹理念,“离充足理由之原则而观物之道也”。不在时空中并不是说我们在描述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时完全摒弃时空框架,那意味着无法做任何描述,而是要在艺术作品中发现一个不同法则的世界,即跳出由欲求、功利构成的现实时空,另辟一个艺术时空,用清代大画家恽南田的话说即是:“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学批评”,它“理念先行”,非常明确地要以艺术作品的感性材料去证实哲学境界的存在。此种工作交给哲学家做容易穿凿附会,交给王国维,却正是本色当行。
但是,果真用“本色当行”四字,却未免让人低估此种美学批评的难度。对王国维来说,仅仅对文艺作品做静态的阐发是不够的,文学艺术不仅仅是描摹哲学之境,更要显示后者如何在现实时空中创生。在叔本华这里,美的显现始终带着涅槃的性质,涅槃是一个动作,一个瞬间,一种发生与实现。文学作品俯拾即是,真正的艺术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王国维正是要以此美学的机缘度量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了进行此种度量,他还特别打造了一个概念工具,即古雅。古雅范畴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问世,它有日常与学理两义,前者近似于古朴典雅,尤其适用于中国文艺,后者则主要包括两层内涵:其一,“天下之物,有绝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绝非利用品者”,“其制作之人,绝非必为天才,而吾人视之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名之曰古雅”;其二,“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此为第一形式,“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它形式以表之”,此为第二形式,古雅即此第二种形式,“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古雅虽为第二形式,但是把握这一范畴的难点在于理解何谓第一形式。王国维以康德主义者的口吻说: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也就是说,一个对象成为审美对象,与一个对象的形式化是同一个过程,但是,第一形式不是特定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外部特征,其哲学核心是理念与形式的同一,也就是理念与直观的同一,艺术存在的价值正是为了显示两者先天的、纯粹的同一性。与之相对的第二形式,则是意在美化、直接作用于感官而且可以有所分析的形式,接近——但不等同于——我们一般理解为“外在形式”或者“形式手段”的东西。仅仅在第二形式上用力,便只能成就古雅之作品,不能成就真正所谓艺术。
提出古雅说的最直接的效应,是第一形式被极大地神秘化。王国维认为,我们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如“神”、“韵”、“气”、“味”等等,“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这一逻辑在《人间词话》中得到贯彻,王国维宣称,“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无境界而仅有格调者,便是所谓“隔”。王国维不厌其烦地辨析说,词中之情景直接呈现为第一形式之美,是为“不隔”;一切艺术,如果第二形式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以至于让人不觉前者存在,也是“不隔”;相反,“蔽于其第二形式,因不能见有第一形式,或仅能见少分之第一形式,皆是隔也”。对于姜夔的作品,王国维既承认其美,又认定其隔,原因正在于他认为姜氏不过是以第二形式之美取胜,美则美矣,终不入第一流之境界。王国维作此类判断时,多是点到为止、不加分说,遂使后人怀疑他对姜氏的贬抑只是一己之偏见,进而怀疑到他的评价原则是否公允。其实,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王国维在对古今词人的评价中体现出这样一种逻辑:能给人美感的,并不就是有境界、有精神、有生命的,因为我们所谓的美感有可能来自于第二形式。大多数审美判断其实都是针对第二形式做出的,之所以同一审美对象会引发不同评价,是因为我们只能依据“表出第一形式之道”去感知对象,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判断,“由时之不同,而人之判断之也各异”。从第二形式到第一形式是本质性的跃进,感性的魅惑被否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用“闹”字能化物为人,化虚为实,化静为动,如此种种都可解,但何谓“境界全出”?无解。境界用于评说,境界本身无可评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虽讲“会心”,并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类形容,但这仍然是以准确传达阅读感受为目的,而境界说的真谛恰恰是叫人超脱于感受之外。王国维以此维护了他所理解的文学批评的美学品格。
然而,此种美学乃是不祥之物。以境界论词,未必能让我们真切把握艺术的存在,却足以让“隔”成为一种精神创伤。王国维既由叔本华领入美学,便永远欠后者一个涅槃。“不隔”即真情真景的创生,创生即涅槃,故生与死同义。惟其如此,王国维激赏尼采之言:一切文学,吾爱以血书者。同样是美学家,同样做文艺批评,宗白华将美学引向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礼赞,他所设立的矛盾关系在个体与传统之间展开,由此展示出艺术在特定文化中的内在超越。王国维则俨然是在做外在超越,要从传统中突围而出。他所强调的是,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而所谓突破习惯,就是冲破那个有能力将文学重新俘获的现实世界,或者说,文学的陈套积习本身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现实世界。作为词人,王国维自负地说:“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他不是要依循现成的格调去表现“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而是孜孜以求那种“境界全出”的创生。必须承认,王国维的一些代表作的确翻出新意,堪为绝响,然而,如果整个词的传统自成一世界,而此世界的原则由古雅所承担,那么“境界全出”只是暗夜中的一瞬光明。王国维只肯向第一义用力,等于是要以萤火照亮长夜。此种用力的结果,固然有可能收获杰作,但也有可能被推入两种境遇:其一,境界的戛戛独造,最终使词越出古典文学的阀限,转为现代文学,王国维的《人间词》中许多篇什正是如此;其二,现代人越是苦心孤诣,与古人生死相搏,越是使经典卓尔耸立。“池塘生春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种作品的境界无法超越,不只是因为才能高低,更因为它们既定义了何谓境界,又使境界无可定义。王国维的词作曾引发友人感慨: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过来,果真能“与古人并”,恐怕会甘心向古人低头;果真能在创造中挑战传统,恐怕会主动臣服于传统。艺术境界的每一次现代创生,不过是对原初之物的模仿;个人独创的意志,终究要消融于艺术世界的整体意志。或许那“境界全出”的紧张之后,未必就是永恒的超越,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
在写于1905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对一贯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循循诱导:“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而在此之前两三年,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对一群天真烂漫的中学女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艺术所完成的对存在,亦即对痛苦的美学解脱,按其性质仅仅适用于审美升华的刹那;当此解脱发生时,存在和痛苦仍然留存于我们的本质的基底。”艺术现身的瞬间带给我们的究竟是超脱的快乐,还是存在的沉重与痛苦,这快乐或痛苦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持续,显然不是某个“美学导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至少对叔本华和王国维来说,美学不是学问,而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纠结。此纠结并不“可爱”,却让人沉迷,因为就在此纠结之中,真理之澄明与遮蔽的永恒争执,一层深过一层地展开。徘徊于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王国维,最终堕入“美学劫”中。此劫的后果,直到一代国学大师于知天命之年毫无征兆地纵身一跃,方才毕现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