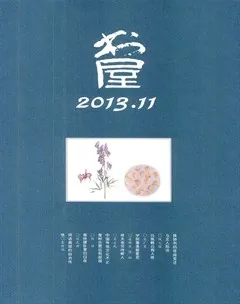家书抵万金
“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陈独秀给儿子陈松年的两封信,是迄今仅见的他的两封家书。陈独秀一生走南闯北,家的观念不强,也不大给家人写信,不像“书信作家”胡适那么善作家书。
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个儿子。他上有两个哥哥:延年、乔年;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鹤年。另还有一姐一妹。也就是说,陈独秀儿女成群。陈独秀在《敬告少年》等名文中对中国青年有过宏观的期待,这其中自然包括自己的孩子,却没有胡适《我的儿子》、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此文写于1919年,至少十年后鲁迅才真正做上父亲)那么具体的育儿经。
陈独秀对儿子的管教是粗放的。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1915年),延年(十七岁)、乔年(十三岁)从家乡安庆到上海读书,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店堂地板上,“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高君曼既是延年兄弟的姨娘,又是继母,不忍心孩子如此清苦,遂托潘赞化以老朋友的资格去恳请独秀,务让延年兄弟在家吃住,免得在外面受罪。陈独秀反而说,(此乃)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1〕。为此潘与之“强争数次,终不可行”。实则陈独秀是在儿子身上实行“兽性主义”教育: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顾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以改变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的状况。
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乍闻似觉残酷,但他还是成功了。仅听潘赞化叙述的一则故事,就可见出延年兄弟在艰苦中已磨砺成钢铁汉子。
回忆五四运动之冬十二月某日夜十一时许,法文班散课,余由校归,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小羔羊,以手抚肩背,仍服袷衣,既问曰:“子无寒乎?”延年路旁拱而立曰:“尚可。”余曰:“望过我家,我将衣子以棉服。”延年道:“不需,谢!”余曰:“近闻汝父在北京因五四学潮已被京警局长吴炳湘(合肥人)逮捕了。同人以同乡关系正在多方营救中,汝知之乎?”曰:“已有所闻。”余试问之曰:“汝对此事感想如何?有无恐怖?”延年曰:“即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之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余难之曰:“假使同人援救无效,汝之感想将何如?”曰:“不过中国失去一有学识之人,当然可惜耳。”
由此则不难想象,延年、乔年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为何成为“陈氏两英豪”;1924年9月、1925年春延年、乔年奉命回国为何担当大任,尤其是延年被人称之为“小马克思”,“比其父独秀办事更彻底痛快”,因为政见不同甚至与身为总书记的父亲分庭抗礼;1927年6月延年在上海被捕,吴稚晖何以电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必欲杀之而后快。次年2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陈氏兄弟次第慷慨就义,堪称英烈兄弟。
陈松年生于1910年,比两个哥哥小得多。他出生之际,父亲就与他的姨妈高君曼私奔了,1913年反袁失败后再也没回过安庆。松年从小没见过父亲,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暑假的事。此时松年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陈独秀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捕,旋解押南京。次年暑假松年带着安庆蔬菜去探监,两个熟悉的陌生人默然对视,第一次见到父亲,松年不免悲欣交集而潸然泪下。据说陈独秀为此甚为不快,瞪着两眼,呵斥儿子:“没出息,流什么泪。”他见不得人流泪,尤其是儿子。父亲说话两眼发光的表情令儿子震惊,以致终生难忘。陈松年晚年接受《陈独秀大传》作者任建树访问时还说起此情此景。
陈独秀爱子之情迥异于常人。延年、乔年牺牲后,高君曼在家中设灵位,为之“剪纸招魂”,“而独秀仍讥其迂腐”。然而在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狱中,陈独秀竟老泪纵横,以酒酹地,祭祀两个壮烈牺牲的儿子——延年、乔年。诚如鲁迅所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只是壮怀激烈的陈独秀寻常难有此表现而已,同狱的濮清泉说,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2〕。
“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陈松年对父亲又敬又畏。自1933年暑假探监后,他年年暑假到南京狱中看望父亲。他真正跟父亲近距离相处,是陈独秀1937年8月21日释放,经武汉入川避居江津时期。当时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搞总务,也代一点课,这是潘赞化的安排,潘时任国立九中总务主任,国立九中安徽人多。从此松年与父亲隔江而居,时而带着妻与子去见父亲,让他在艰辛著述之馀享受些许天伦之乐。
陈独秀入川时,安庆老家也有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危险,于是松年携家眷及祖母(陈昔凡之妻,独秀之嗣母)奔父亲而去,独秀的大姐一家也不期而至。不管陈独秀处境多么艰难,在这患难之际他仍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现存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两封信,就是入川之际叮嘱松年如何将这个大家庭团队安全地带到江津。两封信原件现珍藏在松年之子那里,秘不示人。陈独秀留给他们的遗珍仅此而已。本书所获两信手迹的影印件,一来自安庆图书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编的白皮书《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上的小照片,很不清晰,只存其意象而已;另一封是从安庆独秀园陈列版上拍摄下来的。
两封信内容,在诸多陈独秀研究著述中都有过交代,我更感兴趣的是,陈独秀在信中与儿子交流的那种特有的姿态,以及这种姿态所传递的特殊的父爱,更能见出陈独秀另一精彩的精神片断。先看第一封信:
松年:
祖母及汝等动身后,曾托李侠公先生以航空信请求史岳门君(信宜昌二马路平和里十七号门牌),派人于大和抵埠时照料,并代购赴重庆船票,不知此信到达否?不论此信曾否达到,你务必到史君处去一趟,留下你们的住址,以便我到宜昌时寻找。我或能于明后日乘行营开重庆的差船(偕包先生家眷同行),在宜昌换船时,我必登岸寻你们。你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在宜昌候我,倘一时买船票不得,我到宜昌时,或随原船同行,或另觅他船同行,都好办。倘收到此信时有船可行,可将我附来寄潘赞化先生信原封由航空信寄去(信中空处填某公司船名,至要!),以便到重庆时有人照料一下好些,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注:掉一“可”字)省此小费!葛康俞(三人同行)已于昨晚乘龙安轮船赴宜昌,你务必打听清楚于船抵宜昌时去接他们一下,并望告诉他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候我!包先生嘱告恽子世先生在宜昌候他家眷回到重庆,不必回汉口,此信可与恽君一阅,恽子世太太亦同船。
父字
十四日
此信系1938年6月14日寄自汉口。原信封上写明:“宜昌天后宫二十九号,夏侯智安先生转恽子世先生交陈松年收。汉口吉庆街165号陈寄。六月十六日。”
在陈独秀儿子中松年可能较为木讷,在那国难当头的乱世由他带着一大家子从宜昌赶往重庆,稍有闪失就会出岔子。所以陈独秀给儿子的信中,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极细微的安排,对每个细节都有极周到与坚定的叮嘱,信中反复出现“务必”、“重要”、“千万”的字样,不仅多处使用惊叹号,还再三缀以重点号。这在陈独秀通信史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论学、议事,还是论政,哪怕给中共中央致信中谈根本意见也没有如此。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心情是何等焦急,这个闯荡四方的男人第一次感受到对家、对儿子,尤其是对母亲(虽为嗣母,亦待之至孝)的责任,他要动员一切智慧与力量将这个逃难队伍安全转移到抗战的大方后——重庆。
再看第二封信: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此间租店屋,非绝对没有,但生意外来人不易做。据邓季宣的意见,景羲仍以和胡子模合力在此开米店为妥当。在此收谷碾米运往重庆出售,与本地人交涉比较少也。季严等已到重庆否?倘大批人俱到,乡壁街住不下,罗太太(方志强女士)及季严夫妇,可住金家巷的房子,此房子可与薛农山先生接洽,此人上午在黄家垭口四达里五号住宅,下午则在《时事新报》社。他们已到后(否),望即写信告诉我。
父字
八月九日
此信系独秀于1938年8月9日寄自江津。
信中所称的“孝远”即方孝远(按,方孝远当为方孝博之误),桐城人,后在国立九中教书,系独秀旧交。仲纯即邓仲纯,邓绳侯之子,邓季宣之兄,时在江津开设“延年医院”,独秀即住在医院中。景羲即吴景羲,独秀大姐的儿子,商人,其父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设“吴永顺”酱园。季严是景羲之弟,曾参加革命,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1937年抗战前经其妻李秀泉营救出狱。罗太太即罗汉之妻。罗汉,北大学生,曾追随独秀多年,后受北大同学会委托住江津,照顾独秀,同住于“延年医院”中,于1938年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时一去不返。不久,独秀的母亲谢夫人病死江津,独秀遂搬往鹤山坪。胡子模应为胡子穆。
与第一封信的急促相比,第二封信从语气到书写都从容得多。
在第二封信中,陈独秀不仅为这个从重庆再度转移到江津的难民队伍寻找住房,还为大姐的儿子们谋生出谋划策,更有趣的是他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困境与难堪告诉儿子。
邓仲纯(邓庆初)是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五世孙,早年与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他是学医的,抗战初先于陈独秀立足江津,开了个“延年医院”,谋生有方,于是写信邀陈独秀来江津。陈独秀携家欣然前往,没想到邓仲纯之妻闭门谢客。邓医生可能还是个“妻管严”,面对此情此景一时别无招术。陈独秀虽落难,毕竟是个大名士,以往所到之处,都有朋友接待,为之设宴洗尘,如今如此狼狈,累累如丧家之犬,“进退两难”。“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这是陈独秀在儿子面前的一声感慨:“出门之难如此”。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四海为家的陈独秀第一次感到出门的困境,“幸祖母未同来也”,独秀嗣母谢氏即松年之祖母,此从松年视角呼之为“祖母”,独秀恐老母经受不起此种打击,所幸她未同来不知其详,当然陈氏父子也不会将此情形告诉她,免得她一同受辱。可见独秀在困境中仍心细如发,体恤母亲。换一个人,对此不堪情节,藏匿尚且惟恐不及,哪肯与外人道及,更何况对自己的儿子。陈独秀则不然,他在致儿子信中娓娓道来,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试问中国古往今来谁有陈氏这般坦荡的胸襟。陈独秀在儿子面前,毫不摆父道尊严,在信中似与友人平等交流,不存任何芥蒂。这在中国父子通信中也是少有的。
胡适与儿子多有通信,口气也都是平和,但他决不会如陈独秀在通信中将自己的“隐私”暴露给儿子。胡适视父子关系“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父亲对儿子的教与养,是人道的义务,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父亲只希望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3〕。这自然是五四后新型的父子观。但胡适对儿子仍然是在“教训”,不似陈独秀对儿子是倾吐、是交流,尽管松年终生敬畏父亲,不似胡适之子思杜那么顽劣。
独秀山前日影斜
安庆收藏家孙志方先生最近寄我几份有关陈松年资料的复印件,其中有省立安庆黄家狮小学、私立安庆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国立第九中学等校的聘书,从而知道陈松年三十年代曾在这些学校或任自然课(动植物)教员,或任事务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谈话会1945年11月29日在美专校街七号进行,到会的除陈松年,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与学生如明甫、王星拱、王云五等十人,由何之瑜记录。这不是原始记录稿,而是陈松年事后“缮印”,分送未能参加会谈的远道亲友,以便周知。
这份谈话会记录最精彩处在版税的分配方案与陈氏遗书处理方法。其版税重头用于对遗著的出版与对陈独秀的纪念与宣传,其次再是对后代的教育经费。陈独秀的遗书则赠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管。遗憾的是,陈独秀至今逝世已七十周年,当年参会者也已全部逝世,他的遗著仍未按当年的“订约”出版,于是谈话会种种设想都已落空。这份发黄的记录稿早已飘落红尘,幸有心人拾得才作为历史遗存收入本书。
“谈话会”后两年的1947年春,陈松年又将父亲的遗骸由长江水路从江津运回安庆,让他“落叶归根”。陈松年将生前离异的父母同穴合葬于安庆市郊的叶家冲。不管陈独秀生前性格何等倔强,死后只能听从这个很内向的儿子安置了。据说,陈独秀原配高氏卒于1930年,临终时叮嘱陈松年,一定要和陈独秀合葬。
引笔至此忽然想起房秩五的《感事示陈松年》,录此作为本文的结语:“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4〕松年在城门外种地数亩。
注释:
〔1〕见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204页,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1月编印。
〔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3〕《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4〕房秩五:《浮渡山房诗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