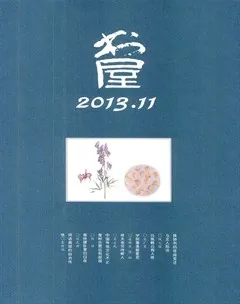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略似尧章仰石湖”:陈毅与龙榆生
陈毅,世称“儒帅”,是一位极富文人气质的开国元勋。1945年,柳亚子曾有诗“兼资文武此全才”加以盛赞。长久以来,陈毅与新、老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任职上海市市长期间“敷扬文教”,团结了大批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文化人,安排他们进入文史馆、参事室、博物馆等机构。调到中央后,他与周恩来一起负责知识分子工作,因直言敢谏而受到拥戴,如1961年与平杰三谈论右派问题,认为失之过左,应从宽处理;在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更是让知识界欢欣鼓舞。
龙榆生(1902—1966),原名沐勋,号龙七、忍寒居士,江西万载人,与夏承焘、唐圭璋合称为二十世纪三大词学家。夏承焘认为龙榆生“使百年来倚声末技,顿成显学,阙功甚伟”。学者张宏生总结了龙榆生在治词上的成就:一、将词视为专门之学,从声调格律入手,揭示出词的特性;二、不仅论词,而且能写词,故多会心之言;三、在论词与选词时把雅与俗、普及与提高融为一体;四、把握古代词学脉络的同时试图引导现代词学的进程。在日常生活中,龙榆生的交游甚为广泛,其中既有文坛名家,如朱祖谋、赵熙、陈三立、陈寅恪、钱钟书、冒鹤亭、李宣倜等,也有政界显要,如胡汉民、毛泽东、曹荻秋、萧向荣等。而他与陈毅之间那段相交甚契的情谊更是令人艳羡。1955年,龙榆生作《岁晚书怀寄陈仲弘副总理北京国务院》七绝三首,其一云:“略似尧章仰石湖,每思务观在成都。明时幸许容疏放,惭愧年年总故吾。”石湖即南宋著名政治家、“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尧章即姜夔,务观即陆游。范成大对姜夔与陆游都有知遇之恩:他对姜夔赞赏不已,累加提携,与之合创词调,还将家姬小红转赠;范成大任成都知府时,邀陆游为参议官,或纵论国家大事,或诗酒酬唱。龙榆生常以姜夔自况,自然,陈毅就是知人善用的范成大了。
陈毅、龙榆生的相知源于龙氏对国军将领郝鹏举的策反。1940年,郝氏脱离胡宗南,改投汪精卫,逐渐得到重用。1944年,他出任汪伪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驻守徐州。眼见日伪溃败在即,他打算自谋出路,转投民盟。但是民盟不打算掌控军队,张东荪就建议他或起义,或依附中共。抗日胜利后,郝部被国民政府收编,自觉不得重用,遂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宣布退出内战。但是郝鹏举反复无常,终在1947年2月为华东野战军俘获,并因逃跑而被击毙。
龙榆生与郝鹏举颇有私交,故在策反过程中出力甚多。1943年8月,龙榆生北上,见到张东荪,谈到希望为国出力,以“共同负起这个打击敌寇的责任”。回沪后,他推荐学生钱仁康到郝府教授钢琴,试探郝氏的动向,并做思想工作。9月,郝鹏举任苏淮特别行政区长官兼保安司令,龙榆生赠《水调歌头》,中有“天下事,几青眼,与吾谋。平生为感知遇,所愿得分忧。淬砺江东子弟,相率中原豪杰,风雨共绸缪”。含劝诫、鼓动之意。1944年夏,龙榆生再赴北平,与张东荪、许宝騤共商策反郝氏之事,决定由许氏前去洽谈。1945年1月,他到徐州会晤郝鹏举,商讨起义事宜。2、3月间他又同张云川(张经常出入解放区,与陈毅素来相熟)一起劝说郝氏,并托张与华东局接洽。此外,龙榆生还计划做“一笔更大的生意”,即策反以刘夷为主的一批江西籍的国军将领。他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让许宝騤感叹不已,“我总想,像榆生这样一名骚人词客,在政治上竟又是这样大有深心,这大概是我国士大夫传统的习性,亦可见民族意识入人之深”。龙榆生对策反郝鹏举的“徐州事”是引以为豪的,直到1961年与夏承焘清谈时还提起。他原本打算到苏北拜谒陈毅,惜因病而未成行。但是,陈毅对龙氏的所作所为是明了于心的。
陈毅、龙榆生的直接交往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起初,陈毅以为龙氏在1949年已被蒋介石杀害。龙榆生《述怀诗》(1950年)有一则小注说到:“七年前北游,曾拟间道往苏北访陈士弘(仲弘)将军,行抵徐州,忽患肺炎折返,至去冬在沪始与将军相见。将军谓:‘闻君已为蒋某所杀,幸获生还,亦始料所不及也’。”1949年9月下旬,已是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入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与农工民主党代表张云川聊天时,得知了龙氏的状况。回到上海后,陈毅立即召谈闲居在家的龙氏,并安排了工作。据龙榆生自传:“一九四九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席上,张云川对陈毅将军谈起我来,陈将军听到我还活在人间,异常高兴,立刻把我的地址记了下来,一面要云川通知我,说他一到上海,就要照顾我的。果然,十一月初,陈毅市长到了上海,就找我去谈(地点在建设大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会),问我愿任何项工作?我表示希望回任大学教授或专心著作。十六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就送了聘书来。名义是编纂,不必随例上班。”龙榆生对陈毅始终心存感激,认为如果没有他的掖护,自己就将流离失所。
“蔼蔼陈将军,执手色转愉。置我文物会,勉更效骀驽”(龙榆生《述怀诗》)。陈毅对龙氏青眼有加,给他安排了一个自由而合心意的工作。龙榆生对这位年长一岁的将军也极是尊敬,从1949年到1966年之间,他基本上每年都有献诸陈毅的诗词。查阅《忍寒诗词歌词集》(2012,复旦大学出版社),与陈毅有关的诗词共计二十余首(阕)。
1951年4月,上海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12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兴起。次年1月,“五反”又全面铺开。这让与日伪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龙榆生惶恐不已,他先后写了《我劝导伪军郝鹏举起义的经过》、《汪精卫心目中的我和我当时对他的看法》、《我在解放后所犯的错误》等数种交代材料。历史问题让他极度紧张、抑郁,甚至一度精神失常,“一九五一年四月,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又是‘三反’学习,搞了半年之久。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因不了解政策,发生了错觉,有些神经失常”。但是,他还是积极、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力求与时代贴合。1952年元旦所作《沁园春·沪上元旦赋呈陈仲弘市长毅》中“结习难除,将军知我,改造还凭有此身。惊魂定,待殷勤揩洗,旧染灰尘”,即显示了他接受改造的决心。1952年3月,他写了《“三反”运动学习中给予我的伟大教育》,6月,又写了《学习陈市长关于‘三反’‘五反’结束报告的个人小结》。直到10月份“三反”结束,龙榆生的精神压力才慢慢缓解。不久,他被调入上海博物馆,任图书资料组组长。
1953年1月,龙氏三女儿新宜因恋爱问题自杀。3月21日,陈毅过文物管理委员会见访,慰其丧女之痛,龙榆生报以长歌,感恩陈毅的知心,“将军自是人中豪,温颜每为寒儒借”,同时传达出为世所用的欣悦,“寤寐以求终一遇,径获新生力当努”。同年国庆,龙榆生吟七律一首献给陈毅,中有“新生质变观唯物,统战功成在礼贤”,称赞陈毅礼贤下士,团结各界民众。
1953年春,龙榆生还与陈毅讨论过陈寅恪,事见同年7月龙氏的一首诗(题为《癸巳秋日追念陈散原丈兼怀寅恪教授广州》):“輶轩绝代早知名,博识多通有定评。安得移根来妙手,青编重耀左丘明。”后附有小注,云:“春间陈毅将军谈及寅恪目盲,谓安得医家妙手剜取死囚双睛为移植耶。”可见陈毅对陈寅恪目盲之事颇为叹息。事实上,陈毅与义宁陈家诸子早有渊源。1950年10月,陈毅、柯庆施等华东军政领导人在南京联名宴请文化名流,陈方恪在列,并与陈毅有过交谈。1951年6月,海军某部欲征用杭州牌坊山之地建荣军疗养院,陈三立夫妇以及陈师曾坟茔在迁出之列。陈氏兄弟遂向陈叔通、章士钊、李一平等能与高层领导沟通的故交求助。同时由陈方恪执笔给陈毅写信,恳请政府保留父母、兄长的长眠之地。经过李一平等向周恩来报告,中央电令停止征用该处。据有人回忆,后来华东局领导请李一平吃饭,陈毅曾说,接到总理电报,他立即将那些人狠狠批评了一顿。如果共产党人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将何以谢天下。1956年春,陈毅到广州,与夫人张茜前往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两人论及《世说新语》,谈叙欢洽。陈毅给自觉远离政治的陈寅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954年岁朝(阴历正月初一),龙榆生效仿苏东坡《春帖子词》,制词五阕献给陈毅,其一云:“儒雅雍容镇海疆,五年建设见辉煌。讴歌合共春潮涨,不是当时旧市场。”称赞陈毅对上海的治理卓有成效,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同年7月,陈毅交代文管会主任委员徐平羽,转嘱咐上海博物馆馆长,允许龙榆生专精撰述,不必随例上班。龙榆生又以苏东坡《临江仙》韵填词报谢,下半阕云:“换骨丹方凭指点,容吾极意经营。却将韶濩颂和平。含英期后报,作楫励今生。”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上海市市长职务不变,直到1958年由柯庆施接任)。陈毅更忙了,但与龙榆生仍来往频繁。1955年3月1日,陈毅到上海博物馆观画,约谈龙氏。他们一同观赏了文征明、石涛、朱耷等人的作品,见到文氏《石湖图卷》,陈毅特有感触,饶有兴致地谈到曾经的苏州石湖之游,画中情致似乎历历在目。他还贴心地询问了龙榆生家庭的详细情况,表示原意提供各种便利。不久,龙榆生赋五古《述怀呈弘公》,自比扎根沃壤的牡丹,“当春定重荣”。同年,龙榆生编定《葵倾集》后寄给了陈毅,还嘱托转献给毛泽东。
1956年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因陈毅安排,2月4日,龙榆生收到北京急电,特邀列席会议,6日晚得毛泽东接待。龙榆生日记记录:“七时半怀仁堂宴会,毛主席接见,握手甚欢。在座有周总理,董必武院长,郭沫若院长,邓小平副总理,沈、陈二老。与彭谈甚契,云拟出一刊物谈诗词。入席后与毛主席同一席,居左第二位,与毛对坐为周总理。三起为主席干杯。食鲍鱼时,主席问是否秦始皇之鲍鱼,对以此为鳆鱼。主席对众称‘我学问不及他’呢。”聚会结束后,龙氏仍旧激动不已,运笔填写《绛都春》,歌颂伟大的领袖与时代,“春回律琯。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海汇众流,宾集群贤同欢宴。欢呼兢捧深杯劝,看圆镜灯光缭乱。蔼然瞻视,熙然濡煦,彩霞迎面。长羡,乡风未改,美肴馔,双筋殷勤为揀。爱敞绣筵,乐近辛盘芳韶展。融融恰称平生愿,佇姹紫嫣红开满。冻梅徐吐幽芳,颂声自远。”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他已能在古典诗词中自如地融入“太阳”等极富象征意义的词汇。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翻阅过龙榆生在三十年代主编的刊物《词学季刊》。1953年,他又通过陈毅向龙榆生转达了问候与关怀,龙氏即以《水调歌头》为调,赋献四章,或“歌颂新民主”,或夸领袖如皎日“照临无远弗届”,或自勉“努力赴前程”。毛、龙二人交流过对词的看法(具体时间不详),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64年6月23日记载,龙榆生信函提到毛泽东说过:“词之为学恐难更有发展余地,意是就其形式言;就其内容声情言,尚可作为创作新体诗歌之参镜。”龙榆生还通过陈毅之口知悉了毛泽东对辛弃疾词作的一些看法。
宴会第二天,陈毅又招龙氏夜谈,龙榆生日记云:“八时,陈派张秘书来迓,倾谈如家人,一切当为好好安排云。”二人灯下促膝谈心,龙榆生详述了过去的生活经历,动情之处不免顿声长叹,陈毅遂有“君果命途多舛”之语。后来,龙榆生为赋《摸鱼儿》:“拨幺弦、赏音能几,十年禁惯憔悴。灯前接席成清话,诉尽平生心事。君看取,爱缓带轻裘,坐我春风里。河清可俟。幸得傍朝阳,飞腾意气,驽蹇尚堪使。缠绵意,渍透鲛珠泉底。骚怀无限凄悱。冥迷一往曾何济,自堕沉渊难起。尘乍洗,信再造深情,未觉吾衰矣。重调宫徵。待仰赞休明,千间广厦,更送万方喜。”
陈、龙在1956年的联系特别多:7月31日,陈毅招饮陈丕显、刘述周、盛丕华、曹荻秋,已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龙榆生获邀出席,赋诗纪盛时有“坐上六人我独逸”之叹。同年,陈毅有致龙榆生书信论词,中有“几生修得到梅花”之语,龙氏缀成《定风波》以报;陈师曾女弟子、时在上海市博物馆从事古画复制工作的江南蘋为陈毅画杜鹃扇面,龙榆生题词《江南好》;胡伯翔画马赠陈毅,龙榆生题七古一首。此外,尚有《八声甘州》呈陈毅,中有“把诗家从头细数,叹不为奸佞即颠连”,感喟诗人们的运道。
作为国家领导人,陈毅忙于政务,但“将军本色是诗人”,故屡有诗词问世,龙榆生也常取而和之(或和其意,或和其韵)。1957年11月25日夜,出席完中苏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宴会的陈毅道逢降雪,吟作《喜雪,祝干部下放》,由大雪纷飞转而谈及国家生产与建设,并对下放干部提出祝愿:“一祝身体好,精神更愉悦。二祝有志气,处处重团结。三祝大努力,亩产加倍获。城乡两配合,并举工农业。勤劳二十年,造成大强国。”龙榆生读后,联想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同事纷纷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争取参加体力劳动的行为,而自己病衰体弱,下去可能会连累农村的同志,倍感惭愧之下填作《水调歌头》:“幼惑孟轲语,偏自重劳心。孜孜矻矻窗下,误我到如今。万卷诗书何用,堕溷沾泥堪恸,感慨一沉吟。谁为换胎骨,领导有金针。上山去,动四体,拓胸襟。手披榛莽,邪许相和问鸣禽。万壑阳光照耀,楼阁参差木杪,无地不黄金。于此锻筋力,啸咏发清音。”龙榆生还根据陈毅词作自制词牌:陈毅曾有《南歌子·日内瓦会结束后驱车游洛桑》一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龙氏读后认为“不特托兴深远,抑亦复面目全新”,“因窃取为调名,次韵奉赞”,成词作《洛桑游》。
1956年8月,龙榆生调往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任古典文学教授。但在1958年5月被柯庆施点名,划为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政协委员资格也被撤销。此后,他的专著以及一些观点被点名批评,参与的著作也不能署名。这让他异常郁闷,在赠章士钊的诗中,有“不合时宜空恳款,细思臣罪信分明”之言。而就在此前不久赠陈毅的《清平乐》中,他还充满了豪情,“孰医予病,鼓起浑身劲。瞬息乾坤看变景,跃进应须相兢。敢忘再造深情,磨揩翳镜重明。此世此生难得,日新好颂河清。”直到1961年9月29日得以摘帽,境况才渐为好转。虽然身陷囹圄,精神不济,但他仍然惦记着陈毅。1959年,龙榆生默念次年为陈毅六十大寿,遂填《百字令》预祝寿辰。
1958年,陈毅继周恩来任外交部长,涉外事务增多,与之相应的是,龙榆生对国际局势也愈来愈感兴趣:1963年初,龙榆生作《满江红》怀陈毅,有“一片乌云,蔽不了、朝辉皎洁。堪笑是、幢幢阴影,刹那生灭”,嘲弄西方反华势力将迅速灭亡。3月15日及19日,听完陈毅的国际形势报告后,又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对反华势力小丑般行径的藐视。龙榆生对陈毅在国际间的奔走颇为关注:1964年3月1日,陈毅陪同周恩来由锡兰飞返昆明,龙氏作《满江红》。4月12日,有怀在雅加达的陈毅,又作《浣溪沙》。在这些诗词中,龙榆生一方面为中国国际声誉的日隆而高兴,赞叹“爱太阳、普照显光华,谁能敌”、“五星旗闪到天涯”;另一方面又为陈毅奔忙国事,“六洲何处不为家”的辛劳而担忧。
1964年5月1日,长期深受动脉硬化困扰、病情加重的龙榆生订立了遗嘱《预告诸儿女》,交代身后事,其中不忘表达对陈毅、毛泽东厚爱的感激之情。
吾以乡曲鄙夫,弱冠出游武昌、厦门、上海等地。由中小学教师,不十年而任大学教授,深惭忝窃。壮历艰屯,陷身敌伪。每思效辛弃疾之所为,挥戈奋起。隐忍谋划,所怀未遂,遂蒙垢耻,末由自白。幸今国务院副总理陈仲弘毅元帅能鉴其诚而予以拯拔,虽没齿难忘也。晚际河清之盛,复荷毛主席特电召见,并同宴席,当众夸奖,益思勉力自效。而文人积习,骄躁未除,旋蹈危机。省愆四载,幸蒙宽宥。蹉跎自误,夫复何言!儿辈散处远方,受党栽培,颇知自奋,所冀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教导下,各勉作螺丝钉,努力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伟大建设事业,以弥乃翁缺憾也。
龙榆生还提及存在身边的汪精卫、胡汉民诗文遗作以及一些照片,计划让儿辈备函递送给陈毅进行处置,主张对这些历史资料不宜轻加毁灭。
1964年7月底,陈毅回到上海,在处理国事之余,于8月2日派人看望了住院的龙榆生。三天后,龙氏带病前往友谊电影院听陈毅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1964年已经是大风暴的前夕,知识分子们生存极其艰难,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陈毅却仍然与龙榆生这样的旧式文人有诗词往返,颇可感慨。龙氏女弟子钱鸿瑛就记录了她到老师家中拜访时的一次独特经历:“有天他在高亢的发言中,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这惟一的听众神秘兮兮地说:‘有人来上海,送我一首词。’我问:‘是谁,什么词?’他迟疑一下,目光向四周迅速扫视一遍,见客厅门是关上的,就急急走向里间,拿了一张纸出来,递给我,低声道:‘是陈毅将军的’。‘啊’,我感到惊奇,不由自主发出这么一声,低头看词。我分明感觉到龙先生是经过考虑、持非常谨慎态度让我看的,似乎等我一瞥后就即抽走,也就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地往纸上搜寻;可怜连词牌都未看清,只记得标题是《蟹》,内容咏物而富有讽刺意味。等我急急‘搜’毕,龙先生果然急急拿走词稿,放回里间了。我惊魂甫定,脑中一闪:是否可请先生让我抄录这首难得的词呢?我终于未敢启齿。当时形势虽尚未‘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自1951年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宛如惊弓之鸟;龙先生让我看陈毅的词,已经是对我莫大的信任了。‘文革’一开始,龙先生和我就无法联系,此词的最后命运,也就不得而知。我猜想先生那时对陈毅同志的《蟹》,即可能彼此唱和。”(《词曲概论》序)
1965年秋,陈毅在北京政协礼堂宴请马一浮、熊十力、傅抱石、夏承焘、沈尹默及其夫人褚保权。这几位皆为龙榆生旧好,常有书信往来,陈毅遂托夏承焘劝告龙氏放宽心怀,多多出游,看看新社会。龙榆生得到夏氏书信,知悉传语后,填作《鹧鸪天》。同年11月,在东北工作的龙氏长子厦材到上海出差,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龙榆生在儿子回东北时,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交给他,让他到北京时托萧向荣交陈毅转呈毛泽东。龙厦材在《影印〈词学季刊〉后记》说到:“解放初期,陈毅市长曾和父亲谈起,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词学季刊》。我想,父亲命我以全份《词学季刊》拜托陈毅副总理代呈毛主席,或者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当政者与民主人士、文化名流之间多能相敬如宾,确然是快乐甜蜜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愉悦的交往逐渐转化、变异,甚至决裂。儒帅陈毅则一如既往,体现了对文化的敬畏、笃信,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与龙榆生,义宁陈家诸子等人之间的交往将作为佳话传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