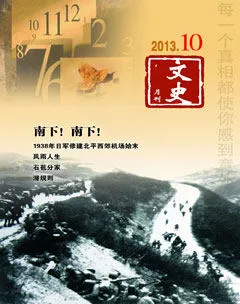“章”字应是“音”“十”章
“章”、“竟”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音乐的“音”字,说明这两个字都与音乐有关,所以我们在口头介绍“章”的结构时,为了怕它与也是姓氏的同音字“张”字混淆,常常说“立”“早”章。说“立”“早”章是不对的,应该说“音”“十”章才对。
说到“章”,必须谈到竟然的“竟”。如今的“竟”有终究、究竟、居然之意,而“竟”的本义并非如此。《说文解字》曰:“竟,乐曲尽为竟。”《周礼》说:“凡乐成则告备。”汉·郑玄注:“成,谓所奏一竟。”这说明,“乐曲终了”才是“竟”。
其实,乐曲终了之意的“竟”也已经是引申义了。甲骨文的“竟”字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一个言语的“言”字,下面是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古代,言语的“言”和音乐的“音”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乐器的形状,与下面的“人”字连在一起,是一个人拿着乐器在“奏乐”。
到金文时,“竟”上面的“言”字换成了音乐的“音”字,进一步强调了“竟”与音乐的关系,下面的“人”没有动,还是人在那里奏乐。小篆的形体虽然趋向了线条化,但它的结构与金文基本一致,仍然是一个“从音从人”的会意字,字意更是与金文完全一样,仍是人在那里奏乐。至于楷书的形体,当然是从小篆的形体发展而来的,也没有什么变动,只是字义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竟”不单单是音乐终了,也有了其他东西其他事情的“穷”“尽”之意。《玉篇》说:“竟,终也。”《广雅》也说:“竟,穷也。”这都是对“竟”的引申义最好的注释。《晋书·谢安传》:“看书既竟。”意思是说书已经看完了;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神龟虽然长寿,但也有死(终了)的时候。还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竟酒。”以及清·林觉民《与妻书》:“不能竟书而欲搁笔。”等等,这里的“竟”都是“穷”“尽”之意。
不仅如此,因“竟”在古代是“境”的通假字,所以国境的终了也称“竟”。古书里边境的“境”字都是我们上面谈到的“竟”字,《商君书·徕民》中“竟内不失须臾之时”的“竟”就是“境”意。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章”字了。“章”是一个会意字,从“音”从“十”。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竟”的引申义,是一曲音乐终了的意思。《说文解字》曰:“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后来,“章”与“竟”一样,不只是“乐竟为一章”了,诗竟、文竟也都可以称为章了。《礼记·曲礼》:“读乐章。”疏:“谓乐书之篇章。”苏轼《前赤壁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以及《史记·吕太后本纪》:“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这里的“章”都是诗文的终了,已自成一体,与我们现在“章”的用法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