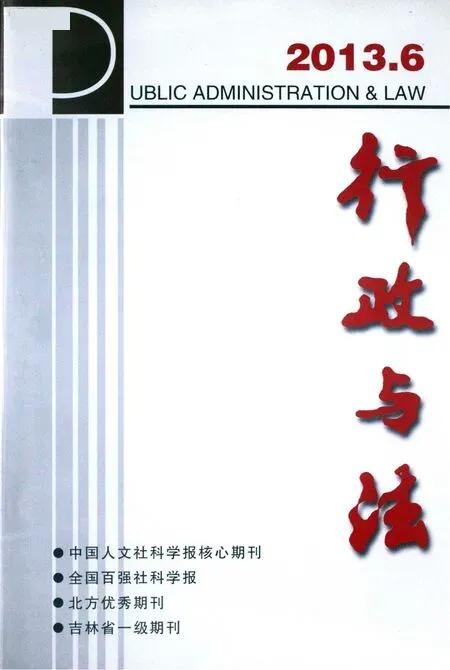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 王菁菁
(北京大学,北京 100091)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何谓正义,以何种标准界定正义,如何实现正义,是千百年来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所思考和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中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开始系统地对正义展开论述,而基本与柏拉图同时期的孔子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正义的思考和看法。
一、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
在柏拉图之前,思想家们虽然针对正义进行过不少探讨,但是柏拉图并不认同。在《理想国》中,他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流行正义观展开了批判。
首先,针对以刻法洛斯为代表的 “正义即言行诚实”的观点,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讲实话和将别人的东西物归原主这种行为在一些情境下并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并举了朋友变疯时不应将借来的武器还给他的例子。之后,波勒马霍斯提出“正义就是帮助朋友和加害敌人”,柏拉图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本身善良的唯一东西就是灵魂的美德,唯一真正伤害人的办法就是让其成为一个更坏的人。很明显,这并不是正义。然后,针对色拉西马霍斯“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论断,柏拉图从几方面进行了驳斥。第一,强者有时会在无意中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如果此时臣民按照强者的要求去服从这种法令,实际上就违背了强者的利益。第二,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所需要服务的唯一利益就是它的对象的利益,每种技艺对其服务对象都有一种无上的权威,目的是对其服务对象有利。第三,非公正并不比公正更加有利。每一种技艺都有给自己对象带去好处的功能。真正的统治者的目标是只为臣民谋取福利,这会造就一种现实,即当一个明理的人意识到别人在为自己服务时,也会立刻努力为他人服务。接下来他分别针对色拉西马霍斯的三个观点进行了批驳,对应地提出,正义者在品位和智力方面是更优秀的,正义能够维持内部的团结一致,正义者比不正义者幸福。
在以上批判的基础上,柏拉图把“正义”分成“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他认为,正义是一种可以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可以存在于整个城邦之中的属性,城邦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城邦的微缩,“城邦正义”正是“人民的正义”或“公民的正义”。根据柏拉图的理论,国家本身就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物,其建立是为了满足出于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后来随着分工不断扩大,行业不断增加,最后产生了专门负责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和专门负责守护国家的保卫者,国家正式形成。总体而言,理想国家主要划分为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三个等级,三个等级具有一定的世袭化倾向,但是理论上等级之间是可以根据每个人性格、能力和素质的不同进行流动的。他认为,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兄弟,但是人与人之间天生是有差别的,适合做统治者的人被造物主注入了金子,保卫者被注入银子,而生产者被注入了铜和铁。[1](p79)他们后代的属性未必和他们相同,此时他们就应该根据孩子固有的成分给他送到适合他性格的职位上。只要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僭越,城邦就实现了正义。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个阶级生活幸福,而是要让整个社会都最大程度地享受幸福生活。如果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三个等级都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社会就会发展成为一个秩序良好、井井有条的整体,就实现了城邦正义。
在城邦中,全部美德有四种主要的属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也就是以公共身份组成城邦的公民也有这四种主要的属性。其中,智慧是属于统治者的美德,使得哲学家能够洞悉整个国家最完善的管理方法;勇敢属于保卫者,指的是国家制度要始终保持的关于应当惧怕什么或不应惧怕什么的正确信念的力量;节制既体现在统治者身上又体现在被统治者身上,是天生优越和低劣的成分在有关两者谁应该被统治的问题上的和谐。而城邦正义则是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承担最适合他的职务并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从正义的性质的角度看,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是没有区别的,国家的美德就是公民的品质。
城邦正义指的是城邦内部三种因素的每一种都在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是每个等级的人都各司其职。那么,个人正义就是一个人性格中的每个部分都能够履行各自的职能。正义的人会使灵魂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协调,使之和谐融洽,避免各种因素相互侵犯各自的职能。反过来说,三种因素彼此干预对方的职能,造成灵魂中的一部分对抗整体,这就是个人的不正义。
总体来看,柏拉图设计出了一个理想城邦,这个理想城邦也就是他所称道的“正义”。柏拉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造物者,将他的“理想国”看成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不容质疑,不容修改。柏拉图以完美主义的观点欣赏他给城邦设置的分工制度,使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各司其职,把每个人牢固地镶嵌在整体结构的适当位置上。此时,每个人虽然从个体上看是不完善的,但是大家结合起来,通过他的“合理设置”,就形成了一种整齐划一的“完美”和“正义”。这种“正义”内含两个原则,体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化:一是效率,二是绝对的城邦利益。每个人的社会职位和社会地位不是个人选择的,而是完全从效率出发由城邦安排的,个人的主观偏好完全被否定了,一切都是为了柏拉图所认为的城邦利益。整个的分工体系完全服从于城邦的需要与城邦的和谐,个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作为城邦组成要素的层面上。所以波普尔也把柏拉图的这种“正义”称为“集权主义的正义”。[2]
二、孔子《论语》中的正义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荀子是使用“正义”一词的第一人。在《荀子·不苟》中便有“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这样的文字。[3](p27)在《荀子·正名》、《荀子·儒效》等篇章中“正义”亦有出现。此时,“正义”一词的意思与现今有所不同,多指官修者对前人的注再加解说的新注。[4](p634)荀子也用此词强调应以“义”为“正”,人的行为应出于“义”的动机。
虽然孔子时期并没有“正义”的概念,但是从《论语》的叙述中我们能够体会出孔子正义观之大略。而且,中国古代有“道统”、“道义”和“礼”等概念与“正义”一词含义相似。“道统”指儒家传道的统绪,《论语·学而》中就称赞“先王之道斯为美”。不过“道统”的构筑是在孟子的时代才开始的。“道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易传·系辞》(上)中:“成性存存,道义之门。”[5](p5)不过孔子一般将“道”和“义”分用,既用以衡量个人的行为和德性,又用来衡量政权的合法性。“礼”这个概念在中国也很重要,《左传》中有“礼,国之干也”的论述,《礼记》也明确了其概念:“礼,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矣。”儒家认为,每个人遵守切合其身份的行为规范,就能够“礼达而分定”,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得以实现,理想社会便得以维持了。
《论语》中孔子的正义观主要是通过 “道”、“义”、“礼”等词表现出来的。与柏拉图相似,孔子在讨论“道”、“义”、“礼”等有关正义的问题时,也既包括君子个人道德方面的正义,又涵盖诸侯国政权合法性方面的正义。他认为,当君子都以“义”作为做人行事的原则,处处不违背礼时,有“道”的社会才能够建成。这与柏拉图从个人正义能够推广到城邦正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个人伦理方面,孔子认为,人是有等级的,而有道者和无道者、君子和小人、士和鄙夫等是最简单最明显的等级划分。阶级之间并非不能流动,而是“就有道而正焉”,到有道之人那里可以匡正自己。[6](p9)“义”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根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然后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礼”,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如果做到了“义”,那么就遵从了人之本体的正当性,便实现了个人的正义了。正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同时,君子要注意去遵从“道”的要求,以“道”作为修身立世的信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到了国家层面,孔子将国家区分为有道之邦和无道之邦。而“邦有道”和“邦无道”的划分依据就是:“邦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也就是,符合正义的国家,其制礼作乐兴兵攻伐都决定于天子,而不符合正义的国家则决定于诸侯。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正义”是基于秩序之上的,符合“礼”的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孔子对于政权正义性和合法性的思考尤其体现在他对圣人德政的肯定与赞扬中。而这种“有道”需要通过因袭三代“礼”之精华达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有道的统治者“为政以德”,不仅以德得天下,更是以德治天下。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盛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盛赞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可以看出,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德性也是孔子判断国家是否符合正义的重要指标。
三、比较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
在文化的轴心时代,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中西方最富盛名的思想家各自对正义进行了阐述,其正义观有不少相似之处。
第一,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中都含有划分社会层次和进行社会分工的内容。在柏拉图的设定中,正义城邦分为统治者、生产者和保卫者三个社会群体,统治者负责管理城邦,生产者负责为城邦提供物质保障,保卫者负责护卫城邦,三者各司其职,整齐划一。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这样进行过明确表述,但是从《论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分层和分工的认可,以及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论语·子路》中就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孔子认为,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人之事,而务农种圃自食其力是小人之事。孔子以“小人”批评樊迟,可见他虽认可社会需要多方面人才的道理,却更希望学生能专注于“大人之学”。
第二,柏拉图和孔子都很重视和期待有德性、有能力的圣人或哲学家的领导,但是这种期待又都是很理想化的。柏拉图所认为的正义城邦是一个哲学王领导下的城邦。他认为,除非哲学家们在自己的国家当上国王,或者现在被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充分真正地渴望得到智慧,否则国家就不会摆脱灾难。[7](p136)而孔子推崇的是圣人的统治。类似于哲学王,圣人也是道德与知识兼备的人,也就是说,圣人的存在本身便是美德的体现。《荀子·正论》中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同“悬”)天下之全称也”,意思是圣人是具有最高品德、一切完美的人,是衡量天下万事万物的标准。他对尧舜禹和周公等人的推崇正是他缅怀和期待圣人之治的证明。
第三,柏拉图和孔子在个人正义方面都很重视个人美德的实现。柏拉图认为,努力寻求正义的个人应该把自身灵魂中的理性、激情与欲望加以合理分配,使理性居于主导的地位,驾驭激情,压制欲望,使灵魂达到最好状态。孔子则对君子给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将“仁”、“义”等条件纳入到个人正义的内涵之中。
但另一方面,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也有所差异。通过对二人正义观差异的研究,我们也能够管窥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首先,柏拉图对于正义的阐述比较明确,城邦正义的条件和个人正义的条件都井然有序,互不重合,而孔子对于正义的叙述则是体现在《论语》的字字句句中,对于“仁”、“义”、“礼”、“智”、“信”和“道”等概念的阐释条目繁多且涵义互有重合。可见,西方文化具有理性源流,而中国文化更偏重感性,需要综合起来看待才能窥得全貌。
其次,柏拉图的正义观较孔子更加乌托邦和理想化。柏拉图对正义的设想有一种极端的理性崇拜,是从造物主的立场对城邦和人的重新建造。个人只是一种符号,其命运就是被安排。而孔子的正义观有种人文的关怀,可行性更强,使人觉得君子、仁者、士是可以培养和塑造的,不同性格的人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培养趋近于正义的要求,暂时有缺陷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自我完善努力成为正义之邦。
第三,柏拉图寻正义于未来,而孔子则拥有复古的正义观。柏拉图要重构正义的个人和正义的城邦,以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理想国作为正义的载体。理想国只是柏拉图个人构想出的未来图景。而孔子则不同,他提出的关于正义的观点都源自于对礼崩乐坏时代的不满,认为欲达到正义就要克己复礼,回归尧舜禹和周公之治。他对国家合法性和个人正义所持的观点都是圣人之治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的投射。
四、启示
辩证地对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正义”的内涵,也对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性意义。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既应该重视制度设计的正义,也应该倡导个人行为的正义。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在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等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逐渐趋近于正义,但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切实落实最多只能实现“国家正义”,要构建和谐社会还应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相结合。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使正义的人构建正义的国家,却无法避免不正义的人做出损害国家的事。所以,在制度设计之外,为了构建和谐社会,还应重视培育个人美德,实现柏拉图所谓的“个人正义”和孔子的“德”。国家应通过教育和治理,全面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社会风尚,培育公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也正是柏拉图所倡导的,让理性居于首要位置,统驭激情,控制欲望。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应重视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新形势下,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警惕腐败,应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起。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中都体现了国家对于有德性、有领导能力的领导层的需要。柏拉图期待哲学王统治国家,孔子主张“德治”,正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为了构建和谐和正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应全面重视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坚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证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地位。
第三,构建正义社会、和谐社会,既要看到未来的光明,也要看到现实的问题。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追寻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有道之邦,,理想都是要植根于现实的,理想社会是作为目标存在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只有在现实中才能产生。柏拉图和孔子的畅想,都源自于他们各自游学和周游列国时的经历,他们各自也都尝试过在叙拉古、在鲁国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探讨正义的时候,要以中国现实发展情况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为着眼点,将理想性与现实性加以统一。
[1][7]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K.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Butler&Tanner Ltd,1945,p.79.
[3]梁启雄著.荀子简释[M].中华书局,1956.
[4]赵吉惠,郭厚安.中国儒学词典[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5]吴根友.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比较政治哲学诸问题初探[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