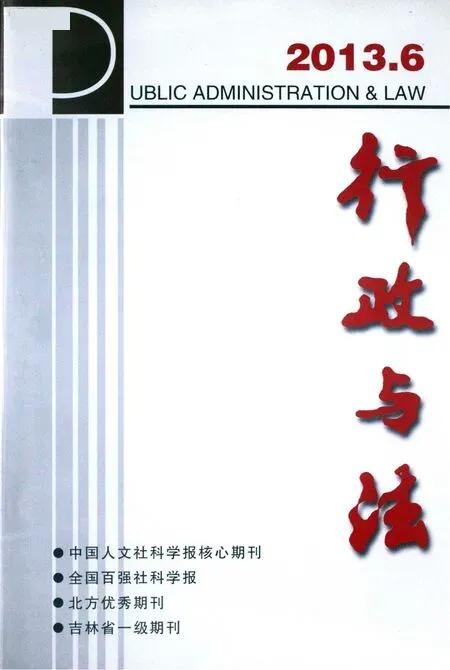战后德国养老金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 李 勇, 王一峰
(⒈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 100890; ⒉福建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08)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正式的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国家, 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889年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王国时期。经过120余年的完善,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养老保障机制。 在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挫败、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后的短期财政困境、1993年欧盟成立后欧洲经济“火车头”长期责任的压力以及近年来欧债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之后, 德国的养老金体系仍然能够持续地为全体国民提供较高水平的养老金待遇, 这也成为德国社会长治久安、国强民富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从技术角度或是制度层面看, 战后德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可借鉴之处。
一、战后德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从基金积累制向现收现付制的转变
早期的德国养老金制度属于完全积累模式,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由于大量的积累基金被强制购买政府债券,导致战后的养老基金名存实亡,最困难的时候仅够维持14天的支出。为此,德国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将养老保险制度从基金积累制 (Funded Defined Contribution)逐步转向为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原积累制度下的基金结余部分在随后的10年间用以偿付使用的改革方案。由于百废待兴,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大量死亡, 这一主张在当时迅速得到了选民尤其是得到了老年选民的支持。迄今为止,阿登纳那句名言:“人们总要生孩子” 仍然是倡导现收现付制养老金模式的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被誉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并担任过阿登纳政府中经济和劳工部长、副总理,后成功继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艾哈德始终激烈地反对阿登纳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由于与阿登纳政治观点的冲突,再加上1966年的德国财政危机,使得艾哈德在1966年底被迫辞职。在仅有的3年任期里,艾哈德政府并未对阿登纳政府的养老金方案做出根本上的调整,虽然其经济发展的理论至今依然受到德国及许多国家的认同。 而现收现付制的基本养老金框架在德国也因此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二)慷慨的养老金计划
20世纪70年代, 德国社会对于扩大福利的呼声日益高涨, 勃兰特所带领的社会民主党于1969年首次组阁成功。从价值取向上看,社会民主党更倾向于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1972年通过对养老金政策的改革,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养老金发放国之一。 其主要的改革计划包括:第一,实现高养老金替代率。对于有长期工作记录的劳动者, 将获得较高水平的养老金收入。例如:一个有着45年工作记录的劳动者在退休后可以获得退休前收入的70%以上, 而相应的养老金偿付水平在当时的美国仅为53%;第二,变“强制退休年龄”为“退休窗口”。取消原有65岁强制退休年龄,对不同群体实行有差别的弹性退休政策。 对于35年及以上工作记录的劳动者, 可以在63-65岁之间选择退休,而对于残疾、经常性失业人口和女性就业人口,则进一步放宽至60-65岁之间。
由于20世纪50-70年代德国经济的恢复及快速发展, 尤其是70年代之后在西德马克对美元的强劲升值的基础上,出口仍然得到持续性的增长。作为同样来自于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的继任者施密特坚持了 “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以及福利支出的扩大化。因此,申请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及养老金的给付标准均有所提高,而退休年龄却有所降低, 尤其是提前退休的现象频繁出现,使政府负担越发沉重。这一现象也恰好与施密特本人的执政理念从早期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向赤字开支政策的转变相吻合。
(三)削减福利的“节流”试验
作为战后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科尔在战后两德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对于欧盟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福利领域, 科尔也面临着由于劳动者基数扩大和来自欧盟国家人口流动增加所带来的养老金给付的挑战。
科尔在任期内始终致力于全面恢复 “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实践,对于社会民主党留下的慷慨养老金计划并不十分认同,短期内又受困于财政的压力,因此缩减福利势在必行。从1986年开始,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整体计划即付诸实施。“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那就是养老金(改革)”。这样的口号甚至成为科尔为谋求连任的主要施政纲领之一。1989年,新的养老金计算标准得到确认, 将养老金标准从与毛工资挂钩转变为与净工资挂钩(1992年开始实行),旨在维持替代率不变的基础上,降低实际养老金的给付标准, 以期通过这样的积累效应实现养老保险供给率从彼时的26.9%提高到2030年的36.4%,并且养老金的实际给付标准将从70%下降到64%。同时,联邦财政拨款奖励多子女家庭以鼓励生育和扩大未来的缴费群体。
两德合并之后, 由于原民主德国居民享有与原联邦德国居民同样的福利水平, 而原民主德国业已存在且不断攀升的高失业率使科尔的计划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更出乎意料的是,非但养老金融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与此同时,为鼓励生育而进行的联邦拨款却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关于法定退休年龄的修改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德国规定,从2001年起,除残障人士63岁退休以外, 法定退休年龄一律为65岁。1997年,又提出将“人口因子”引入到养老金的计算公式中,防止“长寿风险”所带来的对固有养老金制度的冲击。
(四)强化个人责任的“开源”实践
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所领导的“红绿联盟”在1998年大选成功后,随即废除了1997年的基于“人口因子”的养老金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同时,为了将养老金的供款率从20.3%下降到19.1%,施罗德政府不惜持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出。 这一政策遭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反对,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受到了质疑。
为了确保施罗德政府财政政策、 劳工政策和养老金政策的可持续性, 党内以劳工部长里斯特为代表的改革派于1999年开始对施罗德政策进行了修正。首先,对1997年改革中60-65岁之间的女性和失业人口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加以确认。其次,对于工作年限达到35年及以上就业人口,可以保留“退休窗口”的选择权,这项政策将在2017年全面施行。
2001年,里斯特计划正式通过,该计划规定,德国公民只要选择指定的银行或保险公司签订 “里斯特退休金” 合同, 便可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并且联邦补助将随着投保年限的增加而提高。施罗德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改革计划使养老金替代率在2030年达到67-68%, 供款率在2020年以前维持在20%以下,以及到2030年不超过22%。截至2007年,参保人只要每月投入毛工资收入的3%(2008年起提高的4%),便可获得114欧元的直接补助,同时,对有孩子的家庭,每个孩子可获得138欧元的津贴,到2008年,孩子的津贴标准可提高到185欧元。该计划在运行的头5年内,便筹集了近700亿欧元的资金,这成为施罗德政府关于养老金筹资模式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 另一项养老金改革计划“吕鲁普养老”也开始实行,以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保险系统。与“里斯特计划”相比,“吕鲁普养老”计划也享有联邦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具有更高的收益预期,只是无法获得联邦财政的补助。
“里斯特计划” 的自愿参保模式并非改革的初衷,只是迫于工会联盟和左翼政党联盟的反对, 方取消了该计划的强制性。因此,其所形成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联邦性的制度安排。 其被德国的学术界认为是改变德国养老金制度的基石,他们认为至此德国的养老金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现收现付制,而是一种带有部分积累制(Partial Funding)的复合模式。而“吕鲁普养老”计划的出现,更是被认为带有名义账户(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的某些特点和功能。
2004年, 施罗德政府再次通过一项新的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法案。 在养老金的计算公式中首次引入“可持续因子”作为计发标准之一,主要反映了供款人数与受益人数之间的变化趋势,以便通过对“可持续因子” 的随时调整以达到2001年改革计划所既定的改革目标。
施罗德执政期间的养老金“开源”实践,不仅为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开辟了更广阔的筹资渠道, 同时也使德国养老金制度告别了纯粹的“现收现付制”时代,逐步降低了其在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中的比例, 建立起了真正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制,强化了个人在养老金制度中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支持者们称其为“世纪变革”。
二、德国养老金制度的优势
(一)始终以德国民众“老有所养”为目标,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作为工业化强国,德国在战后60余年的发展中,以养老金制度为主体的福利体系几乎在每一届政府中都进行了调整与改革, 经历了从依靠个人积累向依靠政府供给的转变, 同时也经历了从政府大包大揽向更多地增加个人选择权利和个人责任的转变。 所有的改革政策都在不经意中体现了国家福利制度设计中对公平和效率的导向与侧重,但事实的结果是,德国养老金制度在政策或机制上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德国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即使从2000年开始,德国养老金制度更多地引入“私有化”的成分,也同样能够在基本稳定的缴费水平上提供较高水平的养老金供给, 在长达30年的养老金支付年度内, 缴费率稳定在18.3%-21.8之间,而替代率稳定在68%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德国的福利政策正在发生一种示范性的变化,即转向长期保持社会福利体系的有效性和支付能力。同时, 这样的改革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社会震荡。目前,德国养老金制度中所形成的基金投资等市场行为,其初衷仍然是保障养老金的偿付, 是为了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而投资, 并非为了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而建立一个可供投资的养老基金, 本末的关系在德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安排是清晰的, 总体而言强调的仍然是养老金的待遇问题。
(二)具有较强的长远规划性和政策衔接性
在德国养老金制度的政策制定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立足长期。 通常政策调整的目标是着眼于20年乃至更长时间段以后的政策效果, 而这样的时间长度恰恰吻合了每个劳动者一生可能参与的工作年限。福利供给的忧患意识在德国社会表现得尤为强烈,也正是这样的“时间预估”使得德国的每一代劳动者都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退休以后能够获得多少养老金待遇。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政府的每一项改革计划,但由于历届政府对于改革都抛出了一个较长的“适应期”,因而这样的长适应期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 虽然德国的政治架构处于政党林立的状态中,各党派的执政理念和实施手段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出于选票的压力, 在福利制度上的改革却呈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施罗德政府时期,代表社会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停止科尔政府所进行的“福利压缩”计划,而是从手法上变“节流”为“开源”,客观上延续了科尔政府的改革方向,即缩小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同时,由于德国政治游戏规则中“政党事先协商” 的传统又使得看似“噪杂”的国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定能够保证大方向的一致性。 以养老金制度为代表的德国福利体系并没有因为政治左、中、右的党派轮替而起伏不定,甚至有德国学者认为, 正是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而模糊了各党派的“个性”,使得党派差异因此在逐渐消失。
(三)具有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
对于养老金制度而言,由于积累时间长,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只有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才能给国民的养老金待遇带来良好的外部环境。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强调养老金私有化和个人责任增强的背景下, 个人账户的有效积累更加依赖于温和平稳的经济运行。德国自2001年开始实行“李斯特计划”,迄今为止,其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位于较低且可控的水平,这也为德国整体养老金制度的多支柱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外部条件。
三、德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客观冲击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出生率过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的国家, 对于未来缺乏劳动力的担忧, 一直出现在公众和官方的话题讨论中。 而与此同时,对于许多工业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剧,退休或面临退休的人口日益增加,德国也不例外。 德国长期以来稳定的养老金制度在人口结构异化的条件下,养老金给付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再加上德国政党制度和福利刚性的存在,现有的“开源节流”政策依然难以阻止政府支出失控的趋势。 德国政府对养老金的税收转移规模仍然从1991年的21%上升到了2006年的33%,在联邦财政预算中,2006年,对于养老金的转移支付总额已达770亿欧元, 这其中还不包括550亿欧元的对于参保人的附加支出以及110亿欧元的对于私人养老储蓄的津贴。
基于对政府财政支出失控的忧虑,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养老金制度将是不堪重负的, 甚至认为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是一个过时的且成本巨大的体系。当然,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 而对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德国政府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加以克服。 为解决这笔庞大的支出所带来的财政负担,2007年,默克尔政府通过了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二)外部的冲击
自2008年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危机给各国都带来了新的冲击,德国也不例外。资本市场的风险和萎缩导致德国养老金基金的保值增值计划也受到了阻碍,人们的收入降低,失业率增加,“里斯特计划”的参与群体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又出台了对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增加工资以及对于某些特定经济部门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 这些政策甚至引来了对于德国经济价值取向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对养老金制度的负面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2010年以来,由于“欧元危机”的影响持续发酵,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的 “火车头”,难免要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和负担。一方面,以“欧洲四国”(Euro PIGS)为代表的欧洲高福利国家,为维持超额福利支出而导致的政府债台高筑使德国不得不对其进行经济援助计划以保证欧元的“硬通货”地位;另一方面, 无论地中海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或是北海国家, 大部分法定退休年龄都低于德国5年甚至更多,德国政府单方面地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 德国高收入的精英阶层有可能为逃避长期工作年限的约束而在职业生涯的末期选择到其他欧盟国家工作, 而欧盟其他国家尤其是申根国家的长期失业人口则有可能在本国“退休”以后再来德国“碰碰运气”,因为在欧盟国家间, 无论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养老金的跨国转移都是十分便利的。 而这样一来对德国可能造成的冲击则是不可小觑的。因此,默克尔政府在实施“经援计划” 的过程中始终呼吁欧盟各国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四、德国经验带来的启示
不可否认,在社会政策领域中,中德两国囿于政治架构、治理理念、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相互学习和借鉴方面显得难以直接“嫁接”或“移植”,同时, 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德国养老金制度的标准也不相同。但是,对于养老保险乃至社会福利体系中所应共同遵循的思路以及对于相同或类似的社会因素所带来影响的回应, 德国经验或许是他山之石。
(一)不断满足人们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所有的社会政策中, 公平与效率都是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养老保障制度也不例外。从社会养老保险的视角看, 政府或公共部门主导的养老保障计划和以个人或私营部门为主的养老保障计划, 将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产生极大的影响。 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现收现付制与社会公平更多地联系在一起, 而将基金积累制与运行效率更多地联系在一起。 德国自1957年确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之后的43年即2000年, 开始引入非强制性的积累制方案——“里斯特计划”,同时,对于因人口和经济条件变化所造成的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所进行的每一步改革基本都属于“微调型”,同时给予全社会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和适应, 乃至尽量保证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一种养老金制度下。 没有大开大合的政策改变,也避免了大起大落的社会冲击。我国自1986年首次提出“社会保障”概念之后,1995年确立了“统账结合”制度,部分引入强制性的积累制,在2005年又调整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比例, 个人账户规模从原来的11%下降至8%,下降幅度接近30%。在农村养老保险中, 我国从1992年开始至2009年, 经历了农民个人积累、商业保险介入和财政补贴三种模式,并各自运行过一段时间。 这意味着我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向追求效率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又向追求公平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而这20多年又恰逢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对养老保障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既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也对全社会各个层面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管理思路”不断出现的今天,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国家应该满足人们新的、更高的需求。
(二)尽量缩短多重标准的持续时间
德国在二战后开始的养老金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扩大覆盖面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制度初期,矿工的养老金就独立于社会养老金制度之外。1990年东西德合并之后, 原民主德国居民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与原联邦德国接轨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然后,德国政府致力于尽快确立全社会统一的养老金政策(如缴费标准、运营模式、给付标准、优惠政策等),尽量缩短多重标准的持续时间,为公众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制度设计。目前,我国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过程中, 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 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等,导致对不同人口的参保制度作出了主观性的割裂,例如: 城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给付标准远高于农村养老保险,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又采用分级、定额的缴费形式,随着人口流动的继续加快、居民身份变更的日益增加以及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快速推进,养老保险政策的分化又给未来统一社保政策造成了新的障碍,即一个分散化、撕裂化甚至破碎化的养老金制度既缺乏公平也没有效率。因此,我国需要借鉴德国的做法,缩短多重标准的持续时间,缩小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
(三)延长退休年龄
同德国一样, 我国目前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形成了“蘑菇状”的人口年龄结构。德国在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更倾向采用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而不轻易改变其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结构。 德国目前已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而且,德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已提交了一份继续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9岁的政策建议。虽然长期以来德国也面临着较高的失业率,至少从统计资料上看, 世界银行所公布的我国近20年来的失业率均远低于德国,但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为60岁。因此,为保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尤其是保证统筹账户的支付能力, 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或许也是我国可以选择的办法之一。
(四)控制通货膨胀
对于实行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 抵御通货膨胀是社会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发育尚未成熟,因此,在“统账结合”制度中,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基本局限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上。 自2008年我国为抵御次贷危机而实行种种经济刺激政策以来, 一个很严峻的负面影响是物价上涨超过预期水平, 通货膨胀的风险日益加剧, 并且有可能进入长期的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状态, 而这是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运营所始料未及的。我国自2008年开始,居民消费指数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1年以来,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的局面更加严峻, 已经远高于目前长期法定存款利率。 如前所述,德国在引入部分积累制的过程中,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使得“里斯特计划”能够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实施。因此,要确保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 无疑只能在扩大资本市场投资比例和严格控制物价水平上涨的两种可能性上进行政策选择。
[1]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Volume 10.One Germany in Europe: 1989-2009,The Pension Problem,February,1996.
[2]Axel H.Bбrsch-Supan,Christina B.Wilke: “Reforming the German Public Pension System”.AEA meeting,January,2006.
[3]Kai A.Konrad,Gert G.Wagner:“Reform of Public Pension System in Germany”.Discussion paper No.200,February,2000.
[4]Christine Ante:“Pension Policy Reforms in Germany”.Working Paper No.10 March,2008.
[5]Husmann Jürgen: “Germany:Efficiency and Affordability in Social Security through Partial Privatization of Provision for Risk”s,Bulding Social Security:The Challenge of Privat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eries,Vol:6,2001.
[6]Nicolas R?ssler:“The German Pension System:An Overvies”.Mayer Brown,2009.
[7]Holger Bonin:“15 Years of Pension Reform in Germany:Old Successes and New Threats”,IZA Policy Paper No.11.July,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