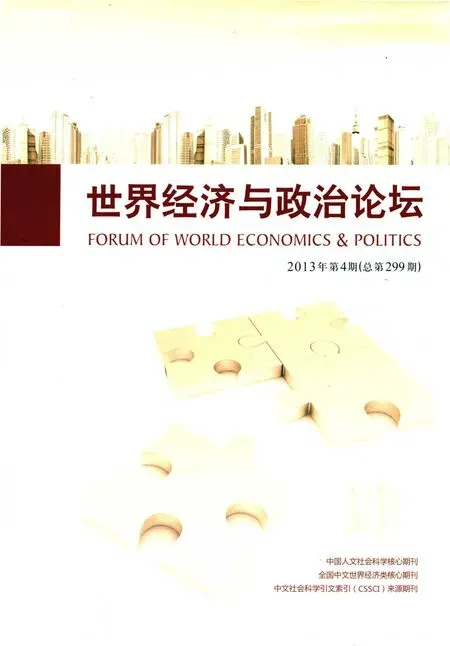关于南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海洋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点
江红义 周理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遍布大小岛屿,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南沙群岛陆地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823000平方公里。典型的热带植物资源、丰富的水产资源、奇异的海岛资源、潜力无限的海底资源,显示着这片区域特别的价值。南海问题其实并非新问题,从19世纪始,西方殖民者及南海周边国家不顾历史事实,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便产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且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区域巨大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储量被侦查确定,南海周边国家在此区域资源争夺的公开化,南海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不断复杂化、国际化。与此对应,我国南海问题相应研究横纵推进,通过梳理,大致可以发现两条研究主线:史地研究与法律研究,并逐步呈现多学科交叉相融的态势。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国际卷入的繁杂现实,更高层面的海洋政治分析研究,即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以海洋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以有效的海洋管理为保障、以具有威慑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为后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海洋利益,呼之欲出。
南海问题的发展阶段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先有西方殖民者后有南海周边国家,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已逾二百余年。我们可以将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按照侵犯程度和形式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管辖权阶段。“1800年,英国船只Bombay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①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J],载《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第217-224页。,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犯南海的先河,“南海问题”由此而生。随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侵犯南海。德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83年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②刘文宗:《我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之一)》[J],载《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47-51页。。法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98年12月,法国殖民者法布里埃向殖民部提出,欲在西沙群岛上为渔民建立供应站”③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页。的企图。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犯始于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带领200多人入侵东沙岛,动用刀枪,驱逐在这里捕鱼的中国渔船,拆毁岛上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坟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行焚化,推入水中”。④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5-66页。这一阶段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在南海进行测绘、以西文或汉语音译命名岛屿、擅自开发海岛资源,其实质是对我南海管辖权的侵犯。
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主权阶段。随着中国持续衰弱,1933年4月,法国炮舰“阿美罗德”号(Alerte)和测量舰“阿斯德罗拉勃”号(Astrolabe)由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Chevey)率领,遍历南沙群岛其余各岛,详加“考察”,以示“占领”,从而制造所谓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随后,日本于1933年8月21日由日本驻法代办泽田致文法国外交部,对于法国占领九岛表示抗议,并声称“诸岛应属日本”①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68-75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9年3月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月9日以所谓“台湾总督府”发表第122号文告,宣布占领“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连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隶属高雄县治②《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3页。。194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陆续接收和派兵驻守南海诸岛。与此同时,法国重新将侵略的魔掌伸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0月5日,法国军舰“希福维”号(Cllevreud)入侵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竖立石碑。对我国政府决定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派军舰“东京”号(Tonkinois)到西沙群岛,当驶至永兴岛,发现该岛已有我国军队驻守时,则改驶至珊瑚岛,在岛上设立行政中心③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M],台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62-63页。。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包括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绘制南海诸岛地图并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等一些必要措施,从而有效维护了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第三阶段是南海周边国家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阶段。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上,南越当局发表了对南海诸岛所谓的主权声明④吴士存:《南海争端的由来和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1956年,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和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并宣称对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传统主权⑤贺鉴、汪翱:《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J],载《学术界》2008年第1期,第254-259页。。就菲律宾而言,1946年7月23日时任菲律宾外长季里诺声称:“中国已因南沙群岛之所有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该群岛在巴拉望岛以西200海里,菲律宾拟将其合并于国防范围之内”⑥曾达葆:《新南群岛是我们的》[N],载《大公报》1946年08月04日。,其觊觎南沙的企图昭然若揭。1956年菲律宾人克洛马频繁到南沙群岛进行活动,从而制造所谓“发现”南沙群岛的“克洛马事件”。1956年5月19日,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加西亚公开宣称,菲律宾在南海中发现“既无所属又无居民”的岛屿,“因而菲律宾继发现之后,有权予以占领”①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83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前苏联在南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南海“边缘地带”特性进一步凸显。1969年5月,埃默里等人的《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协调委员会技术报告》发表。在两者的共同刺激下,与二战后联合国系列海洋法会议所催生的海洋意识相结合,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强占南海岛礁、瓜分海域、掠夺资源,南海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
南海问题的研究历程
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演进,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总体而言,1928年以前主要是用地图疆界线段表达国家疆界的主张。其中代表性的地图有:1880年王之春著的《国朝柔远记》,即已记载东沙群岛属广东省管辖②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2页。。“1901年陈寿彭译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一第二图《中国滨海及长江一带下至中国海南洋群岛》,此图是由英国海军海图局编制的,图中把南海诸岛标绘为中国领土。1908年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地图集》,也是把南海诸岛绘属于中国”③林琳:《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中国主权的确认》[J],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03-106页。。1905年王兴顺重订《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将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万里石塘”的名称划入我国版图。图中用长方形图例把“万里石塘”标明为府一级行政单位④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1-312页。。1912年,地图学家胡晋接、程敷锴编绘出版了《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在这幅系列地图册里,有一幅《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图中出现了南海的连续疆界线标示⑤胡晋接、程敷锴:《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之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M],上海:亚东出图书馆1912年。。
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则开启了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①张明亮直接把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视为南海问题研究的起点。参见:《早期的南中国海研究》,载《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7页。。在随后的长达84年的时间里,前50年基本上以史地调查与考证或者介绍居多,后30年才进入大规模、多学科复合研究阶段。
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激发起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公肃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胡焕庸的《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以及陆东亚的《对于西沙群岛应有之认识》②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吾行健辑),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1939年渝三版;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再版。等。以上论著都对法国侵占中国南海诸岛的事实进行了揭露,并指出法国所占领的南海九小岛属于南沙群岛而非原来国人认为的西沙群岛。但是,囿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学者还无法拿出有利的证据证明南沙群岛确系中国领土。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接收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而激发起国内学者再次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杜定友的《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③杜定友:《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M],载《西南沙志编篡委员会》1948年版。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前人关于南海争端的研究成果,批评了30年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诸岛研究的错误言论,还介绍了当时南海诸岛史地资料的收集情况。此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④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以及杨秀清主编的《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⑤杨秀清:《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M],载《海军总司令部政工处》1948年。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部分岛礁、“克洛马事件”以及菲律宾与南越针对南海诸岛的相关言论,激发起国内学者对南海问题展开研究,从而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南海问题研究的序幕,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长傅、崔琦、邵循正、朱契、王斤役、陈栋康等⑥李长傅:《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南海诸岛简史》[N],载《光明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7版;崔琦:《奇怪的发现》[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邵循正:《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西沙群岛是中国之领土》[N],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8日,第4版;朱契:《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N],载《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学术论文主要有:王斤役:《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J],载《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王斤役:《南沙群岛史》[J],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陈栋康:《我国的南海诸岛》[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仍然主要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中国人民发现、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来相对平静的南海波浪乍起。南海沿岸国家及地区纷纷对南沙提出主权要求,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其海域被分割,并且这种侵占和分割呈现蔓延的趋势,南海问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由点到面逐步走向活跃并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将近40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早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史棣祖、谭其骧、劳祖德①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J],载《地理知识》1975年第9期;谭其骧:《七洲洋考》[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J],载《历史与文物资料》1979年第3期。、林金枝、韩振华、戴可来等。其中林金枝与韩振华②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J],载《南洋问题》1979年第4期;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N],载《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七洲洋考》[J],载《南洋问题》1981年第3期;《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南海诸岛史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坝葛鐄、坝长沙今地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三辑)》1988年第12期。通过自身研究赋予成立于1956年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的前身)以新的学术生命力,自此以后该研究所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戴可来③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N],载《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通过自身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基地郑州大学历史系(今越南研究所的前身)的基础。1983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随后该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南海史地研究的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吕一燃、李国强④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J],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及郑州大学历史系在我国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依然具有活力,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林金枝、韩振华、李金明、郭渊①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A]、《中国人民对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开发的悠久历史》[A],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韩振华:《有关我国南海诸岛地名问题》[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李金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札记》[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我国南海疆域内的石塘、长沙》[J],载《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主权争端的现状》[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等。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等。、戴可来、于向东②戴可来、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J],载《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戴可来、童力:《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1996年,中国南海研究中心(今南海研究院的前身)成立,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吴士存③吴士存:《南海资料索引》[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等。此外,陈史坚、张良福、陈启汉、林琳、刘南威、陈克勤、黄盛璋等学者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分别作出了一定的研究④陈史坚、钟晋樑:《南海诸岛志略》[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J],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J],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克勤:《中国南海诸岛》[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J],载《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总之,国内学术界在宏观上对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到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更多的方面,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他们通过自身研究,以不可辩驳的史实从法理上证明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发现、最早命名、长期不断经营开发与定居利用,并且历代均进行有效管辖与行使主权。所以,中国拥有对南海群岛主权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是充分的、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并对越南所谓南海主权的“历史及法理依据”予以批驳。
其二,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研究。据有案可查的资料,早在1980年,张鸿增⑤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J],载《红旗》1980年第4期。开始明确将国际法引入南海问题的研究之中。1990年以后,随着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不断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地理研究与国际法研究相结合,拓展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这是这一时期该领域研究十分显著的特点。于是,国内学术界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南海问题,其中赵理海①赵理海:《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J],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J],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海洋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翠柏②杨翠柏、唐磊:《从地图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作用看我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杨翠柏:《时际国际法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发现”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J],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承认”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等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他重要的学者主要有王可菊、马涛、赵建文、王建廷等③王可菊:《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兼评越南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行为》[J],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2期;马涛:《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J],载《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5期;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J],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建廷:《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与此同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学者们④许森安:《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内涵》[A],“21世纪的南海:问题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C],2000年5月;高之国:《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李令华:《关于南海U型线与国际海洋边界划定问题的探讨》[J],载《现代渔业信息》2005年第12期;《南海传统九段线与海洋划界问题》[J],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立法与实践》[J],载《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系统研究了南海断续国界线及海洋划界等问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进行了密切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⑤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J],载《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金明:《从国际法看菲律宾对我国南沙群岛的侵占》[J],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年第2、3期;《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看黄岩岛的主权归属》[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南海争端与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领土争议》[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历史性水域、疆域线、抑或岛屿归属线?》[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郭渊:《从近代国际法看晚清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求索》2007年第2期;《对南海争端的国际海洋法分析》[J],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2期。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先后运用地图与国际边界争端中的作用、时际国际法、“发现”与“承认”等国际法中的各项原则,并对国际法中与此类原则相关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均可证明中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主权,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都是违反国际法的,从而以详实的法律驳斥了南海周边国家侵占我“断续线”内岛礁及其海域的国际法主张,并对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历史性权利、以国际法路径解决南海争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三,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研究。进入21世纪,域外大国纷纷插手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趋势,一批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海权研究的学者们及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参与到南海问题研究之中。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南海研究院、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等,其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①李金明:《从东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J],载《东南亚》2004年第3期;《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郭渊:《从睦邻政策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争端为考察中心》[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5期;卢明辉:《南海争端与东南亚国家的扩军》[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邱旺土:《印度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影响评估》[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②张秀三:《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因素与我国的对策论析》[J],载《东南亚》2001年第2期;鞠海龙:《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张明亮:《冷战前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南海研究院③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地缘政治、资源、航道》[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的研究人员在此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地缘政治研究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在南海问题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王传军、邱丹阳、刘中民、蔡鹏鸿、何志工、张小稳、马为民、张瑶华等④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1期;邱丹阳:《中菲南沙争端中的美国因素》[J],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5期;刘中民:《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及对策》[J],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J],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何志工、安小平:《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张小稳:《近期美国升高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战略意图及其影响》[J],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1期;马为民:《美国因素介入南海争端的用意及影响》[J],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期;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J],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关于南海争端国家的国别研究,分别探讨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政策、扩军、海洋划界等问题;关于南海问题中的台湾因素研究,探讨了台湾的南海政策及动向,以及两岸南海合作问题;卷入南海争端的大国研究,分别探讨了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卷入南海争端的原因及后果等问题。
其四,解决南海问题具体对策研究。正如前文所述,南海问题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目前南海问题的焦点主要是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其基本形势是: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五国六方控制,其海域被六国七方分割。针对南沙的主权争端,有关各方纷纷提出了关于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解决南沙主权争端的有效可行方案、或对目前各种方案进行分析研究也就逐渐成为南海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并形成了以下研究领域:一是关于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基本理论及具体实践的研究,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廖文章、肖建国、余民才、蔡鹏鸿、罗国强等①廖文章:《海洋法上共同开发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国家实践》[J],载《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台湾)》2007年第2期;肖建国:《论国际法上共同开发的概念及特征》[J],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余民才:《论国际法上海洋石油共同开发的概念》[J],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蔡鹏鸿:《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罗国强:《“共同开发”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与展望》[J],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具体实践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金明、于文金、李国选、周忠海、安应民、邵建平等②李金明:《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及争端的处理前景》[J],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于文金、朱大奎:《中国能源安全与南海开发》[J],载《世界地理研究》2006年第4期;李国选:《南海共同开发制度化:内涵、条件与制约因素》[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周忠海:《论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的法律问题》[J],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5期;安应民:《论南海争议区域油气资源开发的模式选择》[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邵建平:《如何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东南亚国家经验的视角》[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二是关于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方案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国强、鞠海龙、葛勇平、蔡鹏鸿等③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鞠海龙:《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现实思》[J],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葛勇平:《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及中国对策分析》[J],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9期;蔡鹏鸿:《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三是关于南海问题的国家海权战略研究,主要涉及军方的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张世平与王生荣、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石家铸、海军政治部的吴纯光等,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鞠海龙等①张世平:《中国海权》[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王生荣:《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年版;石家铸:《海权与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吴纯光:《太平洋上的较量——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基本结论与反思
南海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历时两百余年的老问题了。研究由问题而生。南海问题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领域,而是一个历时近百年的老研究领域了。通过上述对于南海问题研究的概述,我们可以对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作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一条主线:以史地研究与法理研究为主线,并逐步实现多学科研究的融合。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里,史地研究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从1928年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投入研究人数最多、生命力最强、产生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史地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向国人及世界证明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主权。对此,中国有充分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可见,史地研究的本质就是法理研究,两者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随着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与国际法研究相融合。当然,早期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主要是习惯法规则。1958年四个海洋法公约的制定,使海洋法由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转变,但基本上代表的是海洋大国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一部系统的体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利益的成文的海洋法体系。于是,从成文的国际法角度研究南海问题成为一个基本趋势。1990年以后,随着法学在国内学术界逐步走向繁荣,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逐步实现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的融合,并将国际法逐步渗透到地缘政治研究及资源开发研究领域之中,极大拓展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这在史地研究领域诸如李金民、李国强、吴士存等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缺陷: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研究相对不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然而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21世纪以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史地研究和法律研究,而对策研究相对不足。在世纪交替之际情况稍有改观,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的主张;二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南海问题逐渐成为美、日、印等域外大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而不断插手其中。于是,国内学者将对策研究聚焦于地缘政治研究和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研究之中。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主要围绕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及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而展开,即使目前较为充分的关于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军事战略而展开的,缺乏前瞻性、综合性的国家行为战略研究。
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尽管40年来国内学者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但现实情况却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其一,侵权被强化。目前,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并且各侵权国家还通过行政管理及国内立法等手段对其侵权行为不断予以强化。如菲律宾于1988年设置“卡拉延市”对其侵占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09年制定领海基线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越南则分别于1982年设置黄沙县、2007年设立长沙县,分别对其所侵占或主张管辖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12年6月21日制定《越南海洋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其二,资源被掠夺。虽然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但是南海周边国家在抓紧抢占南海岛礁及海域的同时,还不断加快对所占海域资源的开发活动。仅以油气资源为例,据世界权威能源咨询机构HIS公司2002年数据显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田至少有53个。仅2001年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两侧的原油开采量就高达3 746.9万吨,约等于中国近海原油产量的2.1倍;天然气384.2亿立方米,约等于中国近海天然气产量的9.3倍②萧建国:《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其三,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中国。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以双边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但南海争端国家丝毫没有诚意,反而以结成各种形式的同盟共同对抗中国。这种同盟主要表现为:各争端国家相互结成同盟,其中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代表,试图结成“南沙集团”以共同对抗中国;以东盟为舞台频繁向中国发难,使中国疲于应付;拉拢美、俄、日、印等域外大国,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或结盟共同对抗中国。上述结盟形式使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
一个呼唤:南海问题研究呼唤海洋政治分析。目前,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维护南海权益不仅是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地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海洋政治问题,要求我国必须在国家层面对内对外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否则必将陷入更加被动局面。
海洋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点
海洋政治学是目前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之一①张森森、俞丽虹、梁钢华:《“海洋意识”的缺失困惑》[J],北京:《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6期,第24-26页。。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对涉及海洋的公共政策及法律问题予以研究、教育和讨论。再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其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卧龙岗大学海洋政策研究中心,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海洋政治的过程就是国家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使海洋由“公有地”转变为国家或国际组织对海洋的某些区域享有特定管辖权甚至拥有完全主权的过程。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海洋权益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稳定实现和拓展国家的海洋利益。“由于海洋政治由来已久,牵涉广泛,其内容绝非任何一部著作所能包罗”②[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但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海洋政治的基本要点予以分析。
其一,海洋利益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之所在。海洋利益以海洋价值为基础,海洋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早期海洋给人类提供了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价值。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海洋给人类社会不仅提供了诸如资源、通道等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安全层面的价值,如马汉所言的“英国的强大应更多地归功于海洋”①[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M](范利鸿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及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所言的“被大陆分割的全球水域,只要控制了七大洋就能控制陆地上的事务;控制海上的交通线和咽喉要地,而后采取封锁,或向陆地派遣军队,就可以达到控制陆地的目的”即是。而国家所拥有的具体的海洋价值观直接决定着海洋利益的实现程度。仅以美国为例,“自1789年以来,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6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二亿一千万人口的世界大国,但它从未失掉过与海洋的密切联系。虽然十九世纪美国曾一度转向内地开发国土,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突出了海洋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海洋对国家利益、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关系,由此而改变了对海洋科学和拓展利用的态度,“国会的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有关美国在海洋事务方面新权益的立法及拨款要求迅速作出反应”②[美]杰拉尔德·丁·曼贡:《美国海洋政策》[M](张继先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 页。。充分认识到海洋价值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充分实现和维护海洋利益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成为海洋大国是成就强国的唯一选择,因为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其获得成为伟大国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一切价值。
其二,海洋利益的稳定实现有赖于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确立。在人类经略海洋的早期阶段,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主要由包括武力在内的国家海上力量而确定。在各海洋大国海上力量的反复较量与平衡中,相应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也开始逐步确立。随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国际海洋秩序也逐步由少数大国主宰的“海洋霸权”时代走向众多国家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国际习惯法规则也逐步向成文法转变,以武力为后盾的“海上力量”逐步被以法律为后盾的“海洋权益”所代替。由于现代国家所享有的海洋权益是由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所确认的,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与海洋法的关系问题。海洋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法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海洋法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形式上来说,现代海洋法经历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内容上来说,现代海洋法所确立的各种制度,包括领海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国际海底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即使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也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支持,其在立法工作过程中“进行的争论和妥协以及它所提出的建议的模糊笼统,清楚地表明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论坛”①[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页。。可以这样说,海洋法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海洋政治过程,没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就没有现代海洋法律制度。
其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是推动海洋法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海洋法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法,而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法,它是沿海国家的利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平衡协调的结果。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是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本身就是各主权国家协商一致、各方利益折中妥协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大量的空白点、模糊和不确定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例如,关于海域划界的问题、关于大陆架划界的规定、海洋与外空的关系问题、海洋的军事问题、南极洲海域的地位问题、专属经济区与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剩余权利问题、岩礁与岛屿的区分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等。因此海洋法是不断发展的。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尤其是海洋大国的加入而不断扩大,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无视其存在及其价值。主权国家对待公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充分尊重公约,在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维护、实现和拓展国家管辖海域内及国家管辖海域外的各种海洋利益。面对因海洋法所客观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之处而导致的包括海域划界在内的各种矛盾,沿海国家也应该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在敏锐把握海洋法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推动海洋法的发展。
其四,综合发展国家海洋能力是充分实现海洋利益的基本路径。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了海洋科技能力、海洋经济能力、海洋管理能力、海洋军事能力等内容。目前国际海洋竞争实际上就是海洋科技的竞争,谁能在海洋科技上领先,谁就能拥有海洋开发的主动权,并能够为海洋管理与海洋军事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在国际“蓝色竞争”中赢得主动,因此海洋科技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海洋科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没有现代海洋科学技术便没有现代海洋产业,因此国家海洋经济能力就是通过各种海洋开发手段实现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发展海洋经济离不开国家有效的海洋管理,海洋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海洋开发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序性,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的海洋管理能力是国家海洋经济能力的根本保障。对于沿海国家而言,需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完善海洋立法,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法律的效力等级,将国际海洋法向国内法进行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执法体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公约赋予沿海国家管辖海域内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管制权等落到实处。质言之,“只有国家的事实的管理,才能保证国家海洋权益的最终实现”①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自人类经略海洋以来,海洋军事经历了一个由前台逐步走向幕后的过程,尽管目前军事手段不再作为一个解决海洋矛盾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其始终是作为一个海洋政治中的威慑手段和最后手段而存在的。因此,国家海洋军事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后盾。当然,国家海洋能力还包括国家海洋地缘政治的运用能力。地缘政治环境是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利益的外部环境。充分研究国家所面临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能够为国家持续稳定实现海洋利益提供外部环境支持。总之,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其综合功能在于提升国家海洋利益的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从而使国家在海洋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
具体到南海问题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南海是我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这是因为我国海岸线被双重岛链束缚,缺乏有效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我国的海上周边环境及安全形势是最为严峻的。唯一拥有战略纵深的广阔海域就是南海。南海不仅给我国提供了包括资源和航线在内的最为丰富的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政治、军事及安全层面的价值。而且南海问题又具有特殊性,它并不涉及到谋求海洋扩张或海洋霸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维护合法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问题。因此国家更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去应对这一问题。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少规定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不少缺陷的”,这是“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全面谅解的必不可少的妥协,在制定错综复杂的海洋法律制度时必须付出的代价”①赵理海:《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题》[A],载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157页。。也正因为如此,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公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支持自己声称的主权和管辖权,并积极主动地付诸实际的管理和控制行为,致使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争端的南海问题日趋白热化。截至目前,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最长已逾四十年,我国的持续拖延,一旦使得周边各国对于南海岛礁的占领形成一种国际法上的有效占领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南海争端的解决便会更为艰难。反观我国,尽管在应对南海争端中也付诸一些包括立法、行政管理、开发、战争等国家行为,但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缺乏积极主动的国家行为战略,这也是造成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日益被动的根本原因。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南海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通过历史地理研究虽然可以证明我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主权,但实际上却停留于自说自话的境地之中;通过国际法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依据国际法的相关原则证明我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主权并有效驳斥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国际法主张,但实际上由于国际法所存在的自身缺陷而导致出现互相争斗较劲的局面;通过地缘政治研究使我们对我国海上周边安全环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实际上往往使我国陷入理性与民意的矛盾之中而无所适从;通过共同开发方面的研究虽然为我国实施南海资源共同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准备,但实际情况却是“争议没有搁置,开发没有共同,资源都给别人开发了,而中国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②李金明:《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35-41页。;通过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为我国维护南海权益提供宏观战略指导,但在解决海洋权益纠纷方面军事手段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而存在。不可否认,上述研究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前南海问题研究最为欠缺的就是海洋政治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国家如何在南海问题上积极主动地付诸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的研究。海洋政治要求正确认识与处理国家与海洋法的关系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应该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又不拘泥于海洋法。由于南海断续线、线内水域的性质及“历史性权利”等问题在现代海洋法律制度中本身就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我们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充分把握海洋法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积极主动的综合性的行为战略实践我们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各种权利,以此推动海洋法的发展①2002年12月17日,国际法院把马来西亚与印尼有争议的苏拉威西海两小岛——利吉丹(Ligitan)和西巴丹(Sipadan)判给马来西亚。有的学者认为,该裁决忽视了“发现”、“历史性”声称,而支持连续、有效的占有、管辖或控制达到相当一段时期且无遭到其他反对等证据,体现了海洋法的新发展。Mark J.Valencia,“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anuary 9,2003,p.21.。这种综合性的国家行为战略以海洋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以有效的海洋管理为保障、以具有威慑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为后盾,使我们在南海争端中逐步居于主动地位,为未来的和平谈判积累足够多的筹码,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海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