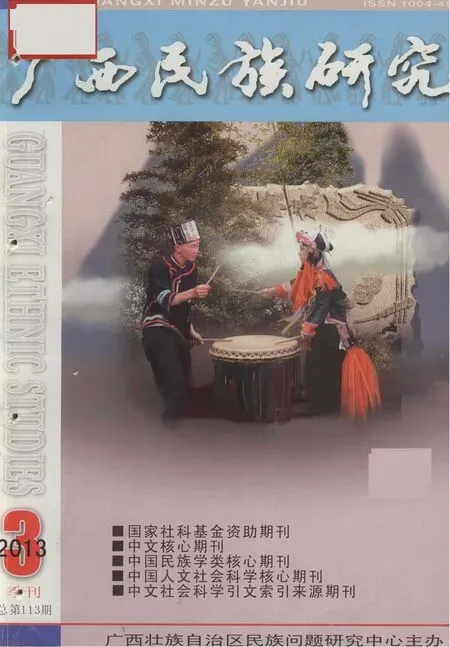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政策与实践特色*
郝亚明
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是国际人权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也是衡量一国人权状况的关键性指标。首先,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是普遍人权的根本要求。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布:“每一个人都享有本宣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普遍性是人权的首要特征,少数民族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是人权的应有之义,也是人权实现的必经之路。其次,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人权国际保护发端于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一些早期的国际条约如《奥格斯堡和约》 (Peace of Augsburg)和《威斯特法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都涉及到了少数民族宗教等方面权利的保护问题,为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制度和实践定下了基调。[1]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少数民族人权屡被严重侵犯的历史事实也催生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其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人权国际公约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再次,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数千个民族生活在200多个国家之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存在。“鉴于人类历史上族群之间的不宽容、仇视以及压迫一直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通常成为这些冲突中违反基本人权行为的最直接受害者”。[2]1从这个角度来讲,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石,是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最后,世界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事业亟待加强。在理论方面,人们关于“少数人”的界定、“少数人权利”的法律和政治哲学基础等问题存在广泛争论,以至于这一领域被称为“无结论的少数人权利问题”。[3]在实践方面,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在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众多挑战,诸如人权保障内容、效果、方式、后果等问题在很多社会中都缺乏基本共识。在制度方面,尽管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的“不歧视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少数群体的人权而制定的,然而为少数群体的人权做出特别安排而进行的标准制定工作却进展缓慢。一些人权批评家甚至认为,“在国际人权的法律框架内,少数群体的人权被边缘化了,这些最易受侵害群体的权利甚至被排除出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框架之外。”[4]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使各少数民族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各少数民族人口共为113792211人,占总人口的8.4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广泛分布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并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民族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交错居住格局。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是民族平等政策的首要原则,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体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工作,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以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条文为基础,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实施全方位的保护。综合而言,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政策与实践体现出以下特色。
一、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领域的全面性
人权的内容设定对于人权保障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权内容的全面性也可以视作衡量一国人权保障状况的重要层面。早在人权国际保护事业发展的初期,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就在人权内容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前者认为基本人权仅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则坚持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一般而言,人权实践过程会受到历史社会现实和政治理念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在本国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上会呈现差异。少数民族人权作为人权体系中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部分,其内容设定更是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息息相关。针对内容的差异,世界各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不承认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必要性。例如法国宪法规定:法国只存在一个法兰西民族,任何具有法国国籍的人都属于法兰西民族。[6]法国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针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内容,所有公民享受形式上平等等内容统一的人权保障。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并将其视作与主体族群存在文化差异的群体。这种类型的国家往往以多元文化主义来应对民族问题,尤其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权利的保护。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往往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这类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实施全方位的保障,力图通过特定的民族政策来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保障领域的全面性正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政策与实践的首要特色。
第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保障。政治权利是人权的核心要素,保障少数民族人权首要就是维护其政治权利。在中国,各族人民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国家依法保障各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中国政府普遍性地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旗)等民族自治地方以确保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对于散杂居少数民族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利,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予以保障。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有一名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专门在全国各地创立民族院校并开设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积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7]
第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保障。首先,国家优先安排大量建设项目,兴建铁路、公路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积极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现代工业,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国家重视消除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努力改善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770多万人。再次,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支持力度,积极组织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统计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向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20889.40亿元,年均增长15.6%。[8]此外,国家还积极制定系统化战略,推动民族地区发展。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所有民族自治地方全部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或者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有关优惠政策。近年来,国家相继制定和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近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等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7]
第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广泛应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都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电信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中国人民币主币除使用汉字之外,还使用了蒙古、藏、维吾尔、壮四种少数民族文字。[8]国家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大量资金对民族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和维护,将大量的民族文化艺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和传承。与此同时,国家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
第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社会权利的保障。社会权利与社会成员生活息息相关,保障少数民族的社会权利是维护其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公共政策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特殊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充分保障其基本社会权利。在教育发展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相关的义务教育、双语教育、高等教育等予以全面扶持。经过60年的努力,民族地方已形成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少数民族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8]在医疗卫生保障方面,国家注重政策倾斜,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投入大量财力,初步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为尊重和满足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需求,国家实行优惠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众特殊生产生活必需品提供稳定的保障。
二、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核心内容
生存权顾名思义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指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存条件获得基本保障的权利。[9]74而发展权作为生存权的一种延伸,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的集体的国家和民族自由地参与和增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并享受发展利益的一种资格和权能。[10]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它人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它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11]38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基本主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中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存艰难、发展落后,基本人权缺乏保障导致了其它人权的全面缺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了对少数民族人权的全面保障。
通过对部分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制度的改革来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一些民族地区在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上还保留着农奴制度、政教合一、土司制度、部落头人制和家支制度等。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和经济剥削、废除人身依附的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是保障少数民族生命权、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最根本措施。[12]以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为例,其社会形态基本特征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统治制度;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占有农奴人身;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农奴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农奴阶层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差役,社会停滞不前、经济崩溃;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13]1959年,中央政府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根本上为藏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坚实保障。
通过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来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权状况的改善与发展受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居于基础性地位。[14]301经济发展是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首要条件,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薄弱,普遍存在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在云南、西藏、海南等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15]少数民族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有的民族甚至濒临灭绝,其生存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民族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状况,国家推行系列民族经济政策,调动特殊资源,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保障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及其它人权保障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少数民族生存权得到基本保障,且质量显著提高。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71.40岁的平均水平,7个高于汉族73.34岁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发展权也取得巨大进步。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13170元,增长了30多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3389元,增长了19倍。[8]
环境权泛指个人、集体、国家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民族环境权是民族对其地缘内环境的占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16]环境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少数民族个体和少数民族集体而言,环境既是他们文化与文明的来源,也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大多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同时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忽视环境保护的行为,目前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森林覆盖日趋下降;水土流失严重;草原沙化、碱化、退化严重;植被稀疏,动物生长环境恶化;土地荒漠化日益突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17]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中国政府确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程全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项目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22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近半数在少数民族地区。[18]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在大江大河上游禁止森林采伐,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及以粮代赈等。国家妥善解决生态建设补偿问题,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牧民国家给予粮食补助,对因禁止森林采伐而减少财政收入的地方国家给予财政补助。[8]
在多民族国家中,人口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容易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贫困问题仍较突出。为了保障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国家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人口较少民族采取特殊帮扶措施,重点解决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200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政策,国家民委等有关部门和相关省区采取了相应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2003年国家首次将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列入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对于22个人口少于10万的少数民族约63万人口实行特殊扶持政策,力争在三至五年内使他们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通信交通等方面得到较大改善。[19]2005年,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重点扶持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2011年,相关部委又联合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通过二期规划进一步推进人口较少民族的纵深发展。这些具体政策措施的出台及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人口较少民族及其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保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持。
三、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础
应然人权是人权的一种理想化状态,实然人权则是指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的人权。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从应然人权走向实然人权都必须具备制度基础,没有制度基础的应然人权只是无法实现的虚幻和理想。“权利制度化是权利实现的首要环节。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首先应在政治上解决好权利平等问题,其关键在于制度选择。”[14]177中国少数民族享有广泛的人权,这种人权的享有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制度基础的。不在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其人权保障就只是一句空话。中国法律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即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的规定,是国际人权文件中所没有的内容,体现出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方面的超前性。[20]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地区人权建设的可靠政治保障。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由于统治者长期执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与制度,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存在都难以得到承认,更别说享受平等的人权保护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探索之中就逐步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设想,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坚持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保护聚居少数民族人权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形式。截至2013年,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 (旗)。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8]鉴于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较小、人口较少并且分散,不宜建立自治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通过设立民族乡的办法,使这些少数民族也能行使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共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11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有民族乡。[1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营造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状况,凸显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制度在保护少数民族人权实践中的优越性。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政策、制度和法律三位一体的基本特征,在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从内容构成上来看,主要包括以下5个层次:1.宪法,包括确认少数民族人权的条款,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款,规定国家和上级国家机关在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中的职责的条款;2.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3.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中,关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和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条款;4.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5.有关机关和部门为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少数民族人权的具体政策文本。[14]209这样一套政策与法律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确认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应当享有的人权,规定了少数民族人权实现的基本方式和具体途径,构建了自治机关和国家政府部门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在于实现少数民族在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利,让各民族通过自主决定本民族事务的方式来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依据相关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大致包括以下若干方面:1.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2.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3.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4.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5.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6.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7.自主发展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
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效果与中央政府的作为息息相关。中央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为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其一表现为中央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上级国家机关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中央政府对民族地方自治权的尊重、在国家决策中尊重民族地区的需要,这本身就是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一种尊重。其二表现为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与帮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把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并将其体现在相关法规和政策之中。为贯彻这一国家意志,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突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优先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力度、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扩大对外开放、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口支援、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照顾少数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需要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权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民族地区人权建设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族平等原则指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促进民族地区人权建设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路径
在少数人权利保护领域,国际上基本达成了两项共识:第一,尊重人权价值理念的核心是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一样,平等地享有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1]第二,为确保在民族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能够在事实上有效地实现与其他民族的成员平等地享有某种权利,还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21]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权利的平等保护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特殊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是实现实质意义上权利平等保护的途径和保障。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实现路径,平等保护上的彻底性与特殊保护上的超前性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政策的两大特色。
平等是人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容,人权意味着实质意义上的权利平等。现代人权的基本要求就是权利的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即使人们之间存在肤色、种族、宗教、语言等差异,也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区别对待。”[22]224在人权领域,平等保护意味着“非歧视”原则。联合国的《关于增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的规定》中把“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民族或社会起源、出身或其他身份的差别而采取的区分、排除、限制和优惠,其目的和效果是为了消灭或削弱所有人在平等基础上对权利和自由的享有和行使”。反对歧视是为了“防止任何阻碍个人或群体享有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平等待遇的行为”。[23]在任何一个多民族社会中,政府或统治者都不应阻碍国家非歧视地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个体享有人权,尤其是要确保那些在种族、族群、文化、宗教或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个体的各项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8]这种平等与非歧视的原则在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政策体系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民族平等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实践的基石。经过60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少数民族人权实施平等保护的政策法律体系。少数民族人权平等保护遍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各个领域。
联合国在对少数民族人权进行平等保护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在平等的基础上享受权利和自由并不意味着在每一情况下的相同对待,当给予不同境遇的人以同等待遇,不但不能实现平等,反而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24]。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与主体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大多处于结构上的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境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在起点不平等的条件下,基于“非歧视”的平等保护原则,充其量能够实现的也只是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上的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的主要设计者,李维汉曾指出,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的影响,使其“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时,不能不在事实上受到很大的限制”[25]256。平等作为现代法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必然要求某些情况下对权利进行特殊分配,对弱势群体的实际利益进行必要的补偿,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达到维护其实质性利益的目的。[26]这种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法律上民族平等走向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理论不谋而合,这种认识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特殊保护的理论依托。
从国际视野来看,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依照其运作的领域和宗旨,可以区分为优惠政策与特殊措施两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依从共同的规则进行互动的“共同领域”中,为消除少数民族因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导致的不利局面进而实现实质平等,所采取的特殊照顾称作“优惠政策”;而在社会中那些属于少数民族维持其群体特性和自我认同的“分立领域”中,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群体延续的目的所采取的政策称为“特殊措施”。[2]19按照这种理论划分,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也是通过优惠政策与特殊措施来实现的。
为了在共同领域中创造和恢复平等,中国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在政治参与、经济贸易、教育、就业、人口生产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在政治参与方面,国家设立民族自治地方以确保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实现,由本民族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长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确保人口比例过小的民族拥有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等。在经济贸易方面,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在民族地区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转向转移支付力度,为民族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提供巨大的税收优惠,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资源开发和深加工项目,鼓励民族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发展。在教育文化方面,国家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投资,完善教育设施和教育配置,同时确保少数民族学生都能享受到教育优惠。在就业方面,国家规定应给予少数民族特殊照顾,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考试录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中,为少数民族预留部分名额,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少数民族。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众也予以变通执行,城镇居民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孩子。
除以上民族优惠政策之外,中国政府还出台了若干属于“特殊措施”的民族政策以确保少数民族权利。其一,在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家积极组织抢救和维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办公室,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挖掘、整理、保护。其二,在民族宗教信仰方面,国家除了从法律上确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外,还积极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宗教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宗教教职人员,并对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维修给予资助,对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给予补贴。其三,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与保护方面,国家积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字,推动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及应用。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以上,约有3000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8]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中允许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答卷。
[1]周少青.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问题[J].世界民族,2011(5).
[2]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无结论的少数人权利问题[G]//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编译.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1999.
[4]信春鹰.国际人权问题热点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1994(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OL].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6]德全英.关于少数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R/OL].[2010-9-26]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0-09/26/c_12606837.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R/OL].[2009-9-27]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126896.html.
[9]李云龙.人权问题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0]江习根.发展权含义的法哲学分析[J].现代法学,2004(6).
[11]董云虎,常健.中国人权建设60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12]廖敏文.国际人权法与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民主改革50年[R/OL].[2009-3-3]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3/03/content_203509.htm.
[14]郎维伟,王允武.中国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人权保护[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杨寿川.我国民族经济政策与实践[J].思想战线,2000(4).
[16]王光贤.人权:民族与民族权利问题[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17]朴今海.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R/OL].[2005-2-28]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206981.htm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R/OL].[2004-3-30]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fzsh/2004-03/30/content_329706.htm.
[20]白桂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与中国国内立法: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问题[J].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2005(2).
[21]何立慧.论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J].民族研究,2007(4).
[22]王家福,刘海年.人权与21世纪[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3]UN Human Rights Fact Sheet No.18 on Minority Rights(1998).
[24]杨芳.国际人权法对少数民族人权的平等保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0).
[25]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G]//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6]常健,刘坤.论人权的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J].人权,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