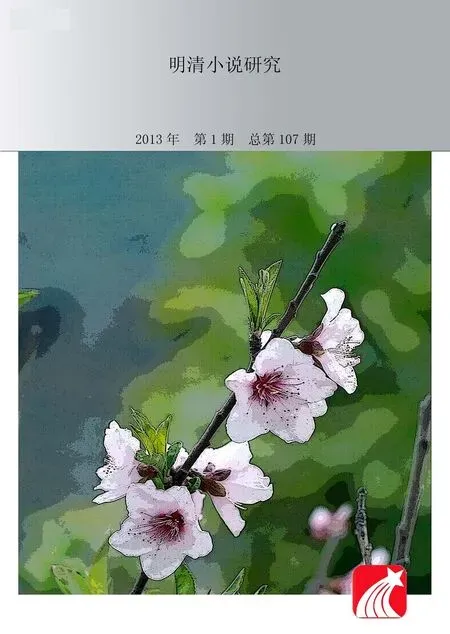中国吝啬鬼之谜
——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
· ·
摘要严监生是吝啬鬼,是一个中国吝啬鬼。他临终前两个指头的哑谜,不仅是绝妙的特写,也是一个反讽。严监生形象渗透和表现着民族文化心理,正是这一点使其得以成为与世界一流吝啬鬼形象相比肩的典型。其吝啬鬼之谜不仅勾联着小说的结构和主旨,也为《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探索小说提供了佐证。
关键词严监生 中国吝啬鬼 《儒林外史》 长篇探索小说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史上有四个著名的吝啬鬼,他们是莎士比亚塑造的夏洛克、莫里哀塑造的阿巴公、巴尔扎克塑造的葛朗台和果戈理塑造的泼留希金。而将《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与这些举世闻名的吝啬鬼形象相提并论的做法也久已为人们熟识。其实,对于把严监生形象理解为超级吝啬鬼,认为作者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地讽刺的说法,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质疑。那么,严监生形象究竟该作何解?本文试从对严监生形象的细读入手,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
一、对严监生形象的质疑和细读
较早地对严监生形象提出质疑的,是夏志清先生。夏先生认为第五、六回中严致和之死这个素来为人称道的场面,脱离上下文看,“是一幅守财奴的绝妙的漫画”,但是“一个真正的吝啬鬼不可能在他已死的妻子身上花费如此多的钱”,夏先生认为吴敬梓安排了一个两根灯芯的故事乃是艺术上的罅漏:“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难以割爱,这样,严致和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尽管这与前面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作者……将他描写成一个软弱、轻信、郁闷乖僻,同时也不无铺张的人”①。
之后,对严监生形象的质疑主要从人物性格本身和作品思想内容两方面展开。或认为严监生“热情待人,苛于待己,好要面子”②,不是对金子的执着狂,故而不能称之为吝啬鬼。或认为严监生是“自虞畏缩综合症”③。或认为严监生具有“自我压缩、自我作践的性情”,活着仅仅是“为他人制造乐趣”④。或认为严监生在必要的时候很舍得花钱,“不能说是太吝啬,只能说是节俭,又加上怯懦。他实在是活得太累”⑤。或认为严监生代表着作者对金钱的深刻认识,“应该为严监生招魂”⑥。
综上所述,质疑严监生形象的焦点是:严监生形象是矛盾的,关键在于他固然悭吝异常,有的时候又颇舍得花钱;质疑严监生形象所得的共识则是:他是活得痛苦和压抑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严监生究竟是不是一个吝啬鬼?他为什么有钱、肯花钱却还活得痛苦压抑?这些问题关涉到形象本身的特质和作者的态度及手法,而答案只有通过细读文本才能找到。
我们先把严监生在这两回中的“花钱”行为统计如下:1、打发差人,两千钱;2、了结严大官司,十几两银子;3、为王氏看病,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4、为扶正生儿子的妾,送王德、王仁每位各一百两;5、为娶赵氏为妻,请客备席,五十两,仍交与二王;6、殡葬王氏,用了四五千两银子;7、送二王乡试盘费,并向二王托孤,赠每位各两封银子,具体数目未详;8、亡过前瞩赵氏为严大一家准备了些别敬等等。
我们再把严监生一家平日的生活状态列举如下:1、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⑦;2、“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⑧;3、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4、每年典铺利钱三百两,严监生给王氏作私房,这笔钱王氏历年俭省共余五百两;5、严监生意外发现这五百两后,怀念王氏,“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⑨;6、严监生死后,“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⑩。
上述材料至少构成几组矛盾:严监生为别人花钱如流水,待自己一家人则苛刻异常;家中下人成群,却账务、家务每每夫妻自己动手做;为王氏择医用药的出奇大方和自己病后的异常悭吝;原配王氏的俭省和继室赵氏的享福等。解读这些矛盾,也就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
吝啬鬼的共性是贪婪、苛刻、无情。严监生的算账和不放心,类乎操劳。不过,他典铺一年的利钱,已经是300两。比较诸位作馆先生一年的馆金从十几两到几十两不等,即可养活一家人,即可窥得严监生的贪婪;而放高利贷几乎也是吝啬鬼聚敛财富的一致手段。严监生待自己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是相当苛刻的。
那么替家兄息讼、替妻子医病、出葬的大方开销和怀念妻子以致病倒,是不是严监生的人情味的体现呢?从小说中对严贡生的描写以及严监生对乃兄的评价,我们可以说,严二对严大与其说有感情,不如说有担心。如果说严监生替兄买单是因为乃兄如狼,他对王氏的态度则需仔细体味。
我们不能说他“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不是在真诚的怀念发妻,我们却看这怀念因何而起?恰是因为发现了王氏积攒的500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于是种下心口疼痛的病根。小说中在这次发现之前的一个细节,恰恰为严监生并非热情、轻信、铺张提供了证据。作者先写赵氏田上的各项收成都不忘了给两位舅爷各备一份;再写赵氏劝说严监生把意外发现的这项银子给王氏做几回好事,余下的送给两位舅爷做应试的盘程。这时作者写得着实精彩。“严监生听着他说”,也就是不做声听赵氏说,但他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他的心理活动:“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情不自禁的发狠动作,正是他此刻不耐烦赵氏大手大脚、憎恶两个舅爷贪无休止,而又无可奈何、难于表达的一种自然发泄。
严监生之病,固是因怀念亡妻而起,而怀念的原因在于,“为严二积聚家私,新妇不如旧”。他怎能放心、怎能不急躁呢?“人财颠倒”是严监生和王氏的共同之处,王氏的守财是天生的还是严监生教育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严监生在给王氏零花钱时就已经算到王氏舍不得花,确是真的。一个面黄肌瘦、路也走不全,总是虚弱的妻子不能让我们信服严监生“对正妻王氏,一往情深……平等和信赖”这样的说法。若是真疼爱王氏,为何还要她事事操劳,王氏的病又因何而起呢?故而严监生就王氏而体现出的“人情味”其实质还是金钱味儿,其核心还是吝啬。
严监生是贪婪的、苛刻的,“要钱不要命”的,再加上他临终见性的经典细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严监生是一个吝啬鬼。
二、中国吝啬鬼之谜
那么如何解释严监生花钱和不花钱的反差,以及他的压抑痛苦呢?这确实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个谜,不妨就称之为中国吝啬鬼之谜。
严监生也许算不得恶人,但也绝非善良之辈。他在妻子卧病在床之际迫不及待地要敲定扶正赵氏一事,是促成王氏死亡的重要原因。说严监生具有“自我压缩、自我作践的性情”也是没有根据的。从他对兄弟、妻舅和妻妾的了解,以及处理官司的明白,安排家事的心机来看,他的“胆小”是由于“有头发可抓”,为保住命根子采取的韬晦行为,而不是天生的脾性。他也绝不是“软弱、轻信、郁闷乖僻,同时也不无铺张的人”。他的压抑痛苦,并不是由于自身的性格或心理缺陷,而是由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因此直关小说的主旨。
严监生在什么时候舍得花钱,为什么花钱?上述罗列的各项开支,不过是三件事而已:其一是代兄消灾,其二是医治和殡葬亡妻,其三是扶妾为正,并无一样是用于自家消费享用。而这三件事共同指向的,其实是严监生的心病:家产和子嗣。为保住这两样命根子,他只能倒贴恶兄、贿笼贪舅。严监生的肯花钱,皆出自不得已。临终前的“两个指头”,才是本性流露。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和世界文学中其他的吝啬鬼一样无情,就认定他不是吝啬鬼,那样做的出发点本来是不妄加比附,结果反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身了。
严监生为何活得太累?首先在于他与严大以及二王的身份地位不同。对于严大和二王的功名,小说中都有明确交代:严大是优贡,二王分别是府学廪膳生员和县学廪膳生员。而对于严监生,只闲闲地说了一句“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 “在国子监生中,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合称五贡。由五贡出身而任官职的人和举人、进士一样,称之为正途,和杂流出身者不同”。而廪膳生员,每年可以从国库领取白银四两。这就是严贡生对二王称“你我为朝廷办事”的根由。严致和的监生是不是捐来的,作者没有明说,从小说中严监生的步步小心和临终遗言来看,似大有可能。第五十六回《幽榜》中有严大而无严二,应该可以算一个曲折的证明。而在家族之中,严二既是老二,正妻无出,只有一个妾生的儿子还小,在宗法社会中与有五个儿子的严大比,自然是势弱的。
其次,他“恐怕寒族多话”。殡葬王氏是我们所见的严监生最大的一笔开销。“除了接受前朝的灵魂不灭的观念外,西周出现了慎终追远的孝道观念。这种观念把养生和送终观念等量齐观,重视送终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养生”。而“明清两代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使厚葬的盛行成为可能。明清厚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向来倡导的‘孝道’,宋儒把丧祭看作是‘礼之大本’,认为丧祭是孝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种观念到明清时代发展到了极致”,故此严监生欲守财而不得也!他笼络二王,由来已久,为的就是在事关礼法的时候,“恐怕寒族多话”,需要二王出来说话。因为中国人看“人”,“是把他放入社会关系中去定义,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人格体系”。“恐怕寒族多话”,才是严监生为严大买单、贿笼二王、为妻子延医用药并厚葬之的根本原因——不如此则扶妾立嗣之事难行矣。没有为社会认可的名誉将无立足之地,不合礼法之事必将寸步难行,这是那个时代制约严监生的文化环境。正如其他四个著名的吝啬鬼都反映出各自所属的民族、时代特点,严监生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文化标本的模塑。
他累就累在身为一个吝啬鬼,既要遵从礼法,而聚敛财富又并不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撑。在临终托孤时他自明心迹:“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他更“高远”的人生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后继有人、光耀门庭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在他看来,读书进学为的就是功名富贵,功成名就后才可以扬眉吐气地生活。他“内受乃兄欺压、外受舅爷挟持”,“自奉极俭,而被诈极多”,腹背受敌,其身份不足以抗击,苦闷压抑其目标更不甘放弃,焉能不算计忍让,忧心如焚,有苦难言,一命归西!
作者对严贡生的恶德败行大力鞭笞,对严监生的态度却是多层次的。有对他腹背受敌的理解和悲悯,有对他为钱所役的讽刺嘲笑,更有对他富贵功名之梦的深刻洞察和鞭笞。相应地,作者写严监生的手法也是细致曲折的,不仔细推敲,就不能体会那两根灯草的哑谜藏着什么样的辛酸和荒谬!
若以“两根灯草”的细节配之以一贯吝啬的情节,仅是讽刺了一个吝啬鬼而已;而以“两根灯草”的细节昭示严监生的表里不一,前后印象的差异正是作者反讽得力之处,中国吝啬鬼之谜正要从这里索解。则我们并不认为舍得花钱和不舍得花钱的矛盾是作者艺术上的罅漏,或可据此否认严监生是吝啬鬼,而恰恰认为这是作者高明之处和严监生这个吝啬鬼的独特之处。世风浇薄,斯文零落,确实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关目;但吴敬梓写严监生这个吝啬鬼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告诫世人正确面对金钱;不是为了赞扬其勤劳节俭;更不是要“为严监生招魂”;他的真实意图还应该从读书进学、功名富贵上去落实,这也正是严监生形象关联全书的所在。
我们越是了解财富对吝啬鬼巨大的异化力量,也就越是了解严监生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所承受的痛苦,越是惊异于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吝啬异于常人与花钱如流水之间的矛盾在严监生身上并非只有对立没有统一,而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严监生作为吝啬鬼的特质,是由他的个性和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共同制约的。严监生不是善人,却是畸零人;算计一生也徒劳一生;愚弄他的,不只是对金钱的占有欲,更是对读书进学或曰功名富贵的幻想。他是吝啬鬼,而且是一个科举噩梦中迷醉的中国吝啬鬼。对这个形象的复杂和独特有了足够的理解,才能了解他堪与世界一流的吝啬鬼形象比肩的典型地位。而对中国吝啬鬼之谜的索解,也有利于我们探求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创作手法。
三、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
我们试着以对严监生形象的分析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这一部分将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作为长篇探索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主旨以及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首先,我们对有些回目是“伪书”或“应该是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等争议采取存疑的态度,拟将全书56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其次,我们不同意“它的缺陷在于结构不好……好似一个个中篇的连缀”一类的看法,认为其症结在于受“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块“里程碑”当然是长篇小说,它独特的结构是与其思想上的探索性相一致的艺术上的有意识创新,和它艺术上的其他创新一样伟大。
给我们很大启发的是Slupski教授关于《儒林外史》三个层次的见解。不过在具体的层次分析上,我们和Slupski教授的看法不尽相同,认为《儒林外史》结构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纪传性结构层次、抒情性自我言志层次和超越时空的哲学层次。
纪传性结构层次是小说最为外显的第一个层次。在揭示八股科举造成唯功名富贵是从的世风以致一代文人有厄的同时,自然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世态百相。“时光将一批批儒林人士送入作者的笔端,又从而将他们送出画外,这就形成了作品浅层面上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然而全书明里既有‘功名富贵’作主脑,暗里又有‘时间顺序’为主线,这就形成了作品深层面上的虽云颇同短制,而实乃整饬长篇……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形态’”。
抒情性自我言志层次隐居在第一个层次之上。 正是真儒奇贤和能养能教、有体有用之才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反映了吴敬梓的政治和人生理想——将儒家的名教与魏晋的超脱、礼乐兵农的政治理想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相结合,化民族文学抒情传统于小说之中,有学者称之为“意在言志的诗化小说”,也即Slupski教授所说的“抒情性自我表露的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哲学的层次。“中国叙事文学和中国哲学一样,是用‘绵延交替’及‘反复循环’的概念来观察宇宙的存在,来界定‘事’的含义的”。“全书没有一件事一个人物是作为完全、纯粹、绝对、永恒的对象来描写的。一切莫不在推移中消长隐显,即便那些理想,那些比较肯定的人物也作为精神探求过程中‘有限’之物来展示”。“《外史》的故事地点转换之频繁也是中国小说所罕见的,它的每一回都很难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层次并不以明确的哲学论述为其基础,而是建立在小说时间和空间的张力之中。它的核心是价值追问 。
下面一一加以分析。正如小说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以王冕为楷模提倡原儒思想;在作者编织的“生活流”之网上,有些人物就像枢纽一样,是小说勾联进退之叙事结构的小中心,如王冕、周进、范进、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等人,严监生无疑也是这些纲目性人物之一。作者对他的讽刺和悲悯之心,是和对整个小说中其他功名迷的态度一致的,涵宕出与《堂吉诃德》相类的悲喜剧融合的艺术特质。而读书进学的魅力竟然超过了金钱在一个吝啬鬼心中的地位,或者说成为他最舍得花本钱的投资项目,又使得人物携带着他民族和时代的份量,在世界文学吝啬鬼的队列中独具其悲剧内涵。
众所周知,第二个层次中吴敬梓塑造的一些真儒和奇人的形象,和小说中的严监生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即理想和现实的参差。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是“出”:孝悌忠恕、仁义育德、礼乐兵农、清议致用。他的审美理想是“处”: 吟咏性情、乐天知命、江山佳丽,所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是也。他的生活理想是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特色的个性自由:在杜少卿的河房里,“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高兴起来也可以携着妻子的手看风景。个性自由的目的在于人性的尊严。夏志清先生认为尾声部分四个庶民形象,“在如此简短的文字里,表现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尊严,这在中国小说里是少见的”。
严监生是《儒林外史》中丧失了人性尊严的小人物中的一个,作者深刻的悲悯即落脚在此。对国家而言“富国裕民,作育英才”和对个人而言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统一于这个自我言志的层次。出于对这一精神空间的建构,作者将逸闻趣事从前人或时人的文字中信手拈来,其中也包括一些艺术水准不高的“耳食”部分。我们依据这个层次,认为那些有可能是伪书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小说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抒情性自我言志层次体现了作家对江山、士人、百姓和儒家文化的深沉的热爱,也寄寓着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贤人和奇人将我们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薪尽火传的希望。
而借助科举梦幻下诸多读书人可悲复可笑的人生,如我们所分析的在金钱和功名双重煎熬下严监生压抑痛苦的一生,作者以这些人物的漂泊和死亡含蓄地指向了第三个层次。在小说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张力之中,科举制艺之风钳锢天下对应着一个朝代的兴衰,使得小说具有了超越故事时间之上的寓言性质。“瞬息烟尘中的真儒理想和名士风流”,当此一“士风世态图”穿梭而过之后,灭之不尽的,是油然而生的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既然一切终不免风流云散,有永恒的终极价值值得我们追求吗?换句话说天下有道吗?而短暂的生命该如何度过才是有价值的?小说在此超越了前两个层次,而上升到面对时空的永恒,个体生命价值该如何确立的问题。这“人生往何处去”的问题,标志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儒林外史》“对通行价值观的质疑”,显然和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潮是一致的。
《儒林外史》中那些具有鲜明个性色彩而又匆匆走过的每一个角色,都被“时间的镰刀”收割到永恒的长河之中。周进之哭、范进之疯、严监生之死……庄尚志之隐、虞育德之出、杜仪之悔……通过各自的经历和彼此的聚谈,他们“互见而相赅”地指向这一疑问。如果说那百十个小星是所有人,也是一个人;作者以收放自如的结构将所有角色构建成一个活动整体,实际上勾勒了明清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文化、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心路历程。
《儒林外史》的三重结构和丰富内涵为后来者开拓了道路,也带来学术的争鸣。正因为《儒林外史》的层次不是平面的,而是三个层面的套组,关于它的主旨的讨论也相应地是多元化的。我们倾向于陈美林先生的看法,吴敬梓是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在“述往思来”,“作者的创作动机即隐含于此”。“作者关注的就不仅是他自己以及周围知识分子的物质境遇、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他更关心他们的精神寄托、安身立命的基点,他希望知识阶层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并防止它们的失落”。这一创作主旨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探索小说的特质。我们尝试着把小说的主旨再推进一层,到达更深的中心:人应该怎样活着?而这个中心即关联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实际上严大和二王这两对兄弟在《儒林外史》的兄弟群像中率先出场,也正如第一回中“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一样,揭示了关乎全书主旨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科举的成功者往往不仁不义?为什么国家选才的制度却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败纲常,变“兄友弟恭”为“兄弟参商”?读书和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假设捐来的监生之推论能够成立,实际上严监生并不是文人,虽不是文人,他却念念不忘功名。正如卧闲草堂批鲍文卿“名戏而实儒也”,从精神凭藉和思想背景来说,严监生也可以说是“名商而实儒也”。联系对比胡屠户、金有余、庄濯江、方盐商这一系列形象,我们说严监生也许不见得有商才,不像庄濯江担得起“士魂商才”的评价,至少也是商人士魂。小说中不具备文人身份而其价值观却得到作者肯定的还有一系列老人等其他形象,同样为作者所讽刺的也不只是文人,“作品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其它社会阶层的成员……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可见作者虽以儒林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又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把整个社会文化纳入了他省察的框架之中。
我们注意到,幽榜上恰巧没有这位严监生。连一根灯草都要节省的他偏偏浪费了自己的一生,他念念不忘的未来的功名恰恰是没有未来的。这种反讽的语境在小说中并不是单一的艺术手法,而是反复勾联递进到作品的深层主旨——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深刻地省察。“‘反讽’在《外史》中绝不只是一种手法,而是一个主题级的宏观特征,一种基本的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隐含着吴敬梓对整个人生的基本看法”。
两根灯草的哑谜无疑是一个高潮。人们容易看见严监生临终两个指头的吝啬鬼招牌,仅把讽刺的矛头停留在这里;确实,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不过,人们却不容易看见胆小的严监生大胆的内心追求:要让子孙后代读书进学功名富贵,严监生的等式是读书=进学=功名富贵=人生的价值。对金钱和功名的汲汲营营在严监生这里合二为一,他牺牲金钱为的是换取子嗣的富贵,盘算的还是盈利的买卖,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花两百两银子买个“义形于色”出来,“未免太便宜了些”。他和儿子先后死去继而家产被严大霸占过半的结局,正是作者对他毕生幻梦的揭破和批判。
可怕的是,这个等式并不是严监生一个人的,而几乎是全社会的。一代文人有厄,我们的文化也病了,那竖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的严监生,用一根灯草的垂念,拷问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严监生之病是时代病的象征。正是这一点使得知识分子出路的问题,上升为更具普遍意义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并关涉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小说中真正令人惊悚的是,真假儒士虽然在价值观和人生道路上迥然不同,但讲究文行出处的人无一不陷入困窘之中,正如颓败的泰伯祠所象征的那样;严监生们固然是虚度一生的,那些真正的才德之士同样也几乎一事无成,他们的品性才学、追求努力似乎都只有不了了之,既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更不能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严监生追求功名富贵之心炙热到作为一个吝啬鬼可以牺牲金钱,杜少卿则正相反,他不惜装病来放弃功名富贵;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因为没有“中”而被剥夺了话语权。杜少卿为保持儒家真谛和个性自由而换得“杜家第一个败类”的“美名”,与其他几个真儒的进退自如不同,杜少卿是彷徨无所依的。严监生的舍不得一根灯草和杜少卿的散尽家产,压抑的都是心中挣扎不出来的呼喊!
“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中华文化停滞在复制文化泡沫的漫漫长夜之中而日趋凋敝。在小说中“如此清醒而深刻地诉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和社会的颓败”,吴敬梓是第一人。礼乐兵农的理想既已成为过去,吴敬梓又不能满足于“中国封建士大夫在宦海沉浮中发明的‘精神胜利法’”;他对应沉重的文化教育危机,进行了多种探索,而徘徊于矛盾之中。小说用心刻画了各类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人物,参差变化、同中有异、往复勾联,细腻地再现他们的思想追求和人生历程,一方面抨击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荼毒,提倡真儒、真名士和淳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全盘观照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探索知识分子和民族文化的未来,完全可以称之为探索小说。
应该怎样活着才能保持士人的品格,如何才能树立有益于民族未来的文化精神?作者曾通过迟衡山的议论表达了一种探索,即“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将追求功名与追求学问分开,希望这是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讲学问的只讲学问,固然有助于学术的独立和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然而和隐逸一样不能不引起质疑:“如果所有优秀的文人都放弃他们传统的出仕的责任,那么他们不就会将这个世界永远丢弃到那些汲汲追求私利的世俗的人手中吗”;“而所谓的‘功名’,在一定的意义上,正是个体对社会所作贡献的一个标尺。……如果每一个人都放弃‘功名’,远遁山林,那么谁来担荷这个有序亦无序的生存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通过内心自觉地修持,即可在“人伦日用”之中领悟超越的价值世界,而不必等待上帝的启示。“如果说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这便是一种具体表现”。既然只能依赖理性救赎,而所谓“为生民立命”,对儒士而言,隐逸永远是第二位的选择,承担、任事才是根本的。固然“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而弃天下于不顾是与作者“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的初衷相违背的。故而作家虽于第55回四奇人身上指出了唯有经济独立方有人格独立之可能的卓见真知,究竟还是为只可独善其身不能兼济天下而遗憾、彷徨,其高山流水之所凄清婉转者,正是“那种难以名状的悲剧感”。尽管深刻体味到传统文化的危机和社会的颓败,仍不能改变作者原儒思想的根基,他讽刺功名之虚妄而依恋功名之作为,这种矛盾是自然的,因为任何先进的思想家都不能完全脱离他的时代。
就探索知识分子出路而言,《儒林外史》既揭示了18世纪科举制度下没有独立生存能力惯于妾妇之道的士的没落,也隐约触及了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漂泊的异乡人的宿命。就小说的探索和追问而言,从知识分子生活到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及危机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家吴敬梓从士人——文化——道三个层次逐层深入地探索人生的价值,而所得却如那首民歌《黑骏马》的最后两个字——寻寻觅觅的结果是“不是”!
虽然理想或者说“道”可望而不可及,小说最末一回“自礼空王”和“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消解不同,而散发出放下生命的担子的安然自得。“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入得《儒林外史》的么”?作者对这一问难“避而不答,转以一长调作结:再次道出他对自己生命中抒情境界的不衰信仰”。作为个体的生命,以短暂探索永恒必然有其道阻且长的悲剧性,但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做自己的事:爱过、啸傲过、醉过、探索过,即可超脱和释然地回归永恒的怀抱。此一境界与尼采《悲剧的诞生》异曲同工,是悲观之后的温暖和勇气。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正是这可能凋零的抒情境界给予自我意识觉醒的心灵之永不凋零的遮蔽——即使时不我与,个体生命还是可以坚守自我而活出意趣风骨来。
在一个热爱读书、重视教育的国度,民族文化发展的滞后难道只应该由制度的荒谬和时代的局限负责吗?其中有没有民族性格的症结所在? “读书功名论”其影响之深入民间,甚或波及当代教育。傅国涌先生曾谓廿八都的文昌阁是那个百姓之镇的集体安慰和梦想的寄托,反映了民族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情结”。从这一点来说,严监生形象又几成预言,严监生的那一口气似乎还是没有咽完,他临终前的两根手指仿佛幽冥的火焰,烛照到今天。而那一根灯草,以千钧重量,拷问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值得我们述往思来,思考读书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究竟何在。这就不只是儒家文化的困境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现代性改造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不仅是知识分子不能失落,也是一个文化强盛的民族所必备的公民精神。
综上所述,严监生是吝啬鬼,而且是一个中国吝啬鬼。严监生形象打通了小说中士人——文化——道三个层次,勾联着小说的结构与主旨,渗透和表现着民族文化心理,也直指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中的功利症结。正是这一点使其得以成为与世界一流吝啬鬼形象相比肩的典型。中国吝啬鬼之谜既是寓言也是预言,为《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探索小说提供了佐证。无论是评价小说的人物还是其结构艺术,都不能“削中国叙事文学之足,适西方文学类型标准之履”。这部述往思来的伟大作品,既是时代的,也是民族的,因而是世界的,向作为交响乐团的世界文化贡献了特异性的中国乐谱。严监生形象、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镇,值得反复研读。
注:
②谢波《严监生吝啬鬼形象质疑》,《明清小说研究》1987年第6期。
④陈文新、鲁小俊《且向长河看落日——〈儒林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282页。
⑤张国风《漫说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⑥罗生《严监生式悲剧与民族文化心理——论为严监生招魂》,《云梦学刊》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