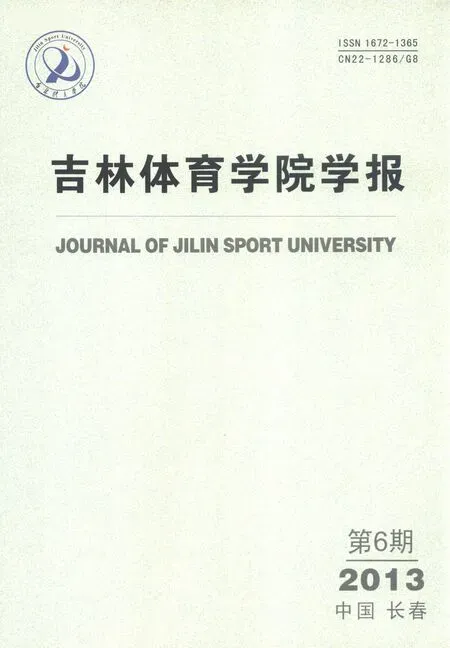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解构与重构
周传志 喻丙梅 廖建曹 黄丽姿
(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解构与重构
周传志 喻丙梅 廖建曹 黄丽姿
(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民俗体育在长期发展衍变过程中形成了以仪式动作、象征符号和信仰传说为内容的结构体系。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其生存环境和参与主体自身发生了变化,民俗体育正面临解构,体现为功能的变迁、内容和形式的更新及参与主体的变化。面对新时期的要求,需要民俗体育在重构过程中做到动作形式更加简单明快、象征符号更加明显易懂、信仰体系更加科学正确等。
城镇化;民俗体育;解构;重构
民俗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1]它的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是以身体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在民间开展的与‘俗’文化关系密切的体育”即为民俗体育,它主要存在于节庆、宗教、礼仪等活动中。[2]民俗体育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强烈冲击,陷入发展困境,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1 农业社会中形成的民俗体育结构
民俗体育多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结构,包括外在的仪式动作、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和民俗体育背后的文化信仰。
1.1仪式动作
仪式是指“人们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3]当代最负盛名的仪式研究者,表演人类学家特纳使用“社会剧”来强调仪式的表演性,认为仪式具有交流和交通的特质。[4]每个民俗体育活动都通过相对固定的身体动作构成一定的仪式过程。如江西永新盾牌舞的仪式是:表演者头裹汗巾,上身着对襟短衫,下着黑色紧口裤,在族长(地方首领)带领下祭祀祖先牌位。族长擎三炷香,率众向祖先牌位三鞠躬,然后杀雄鸡,以其血滴入酒中供奉于案首,再拜。然后表演者手执武器(钢叉、盾和刀)开始表演。[5]这种类似武士出征前祈福仪式过程含有明显的宗教祭祀意味,给人庄严肃穆之感,甚至传递出不惜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息。
而台湾宋江阵的表演仪式则以排成圆圈拜祖师爷开始,然后由集合开始、正式演练和集合解散三个阶段构成。全体演练人员集合“开彩”(呐喊三声)后,“李逵”执双斧请神驱邪。然后“宋江”执旗、“李逵”持斧先行,其他演练人员于其后成单行或双行排阵打圈,然后经过蜈蚣阵、白鹤阵、八卦阵等多个阵形演练(夹以个人武艺展示或打斗表演),表演以再次集合拜神,连吼三声结束。[6]这种表演性仪式过程宣扬的是一种“替天行道,不惧强势”的正气,也具有驱邪逐魔的宗教功能。
1.2象征符号
在上述民俗体育活动中,一些特定物体作为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仪式本身是一个符号整体,它由仪式空间、仪式对象、仪式时间、仪式声音和语言、仪式确认、仪式行动等构成。[4]民俗体育中的象征符号,可能会被涉身其中的人们所理解和确认,但也可能因时间流逝而使那些即使熟知这种仪式本身的人也不一定能准确辨认出这些象征符号。
1.3传说信仰
在多数的民俗体育背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传说(神话),这种传说是基于一定的信仰之上的。如永新盾牌舞的起源问题上,有“干戚舞”遗存说、戚继光抗倭传入说、太平天国运动传入说、荆楚文化孕育说、自身发展说、外乡人传入说等多种观点。[5]其中就含有原始宗教信仰、英雄信仰等。而宋江阵起源含有两个神话:其一是梁山好汉是36天罡和72地煞,系天上星宿转世;其二是梁山好汉为108个蛇精投生。余嘉锡教授在其《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考证说:“宋、元之际,有伪撰江题壁词者,造为‘六六雁行连八九’之语,是为一百八人之说所由起”。[8]可见,所谓“梁山一百单八将”本身也是借助神话附会而成的。在宋江阵表演中,不仅通过仪式和象征强化这种神话,而且通过表演,寓意团结协作,斩妖除魔,保一方平安,甚至“替天行道,反清复明”。
在民俗体育的以上三部分结构中,隐藏在传说背后的信仰(或者说传说本身所透露的信仰)是核心部分,它决定着民俗体育活动中外在的动作方式、仪式过程,也影响着人们对民俗体育活动中符号象征意义的认识。
2 城镇化过程中民俗体育的解构
现代社会中,我国民俗体育不仅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体育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且受到城镇化过程中来自内部的人的思想观念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变革,也必将导致民俗体育的“被解构”,即动作仪式、象征符号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体现为民俗体育功能变迁、内容和形式的更新及参与主体的改变。
2.1功能变迁
诞生于农业社会中的民俗体育有较强的功利目的,无论是“求雨舞”还是“鞭春牛”,莫不是祈求风调雨顺,丰收安康;也不管是火把节还是宋江阵,也都是希望能子孙满堂、合境平安(有些民俗体育甚至演变成训练参与械斗的氏族子弟的手段,如宋江阵和盾牌舞都曾有过这样的历史)。这是基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环境和传统宗教信仰之上的,试图通过天人感应,使上天满足人们的期望。而在城市化过程中,虽然人们生产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人们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强,认识能力的增长,试图通过民俗体育来改善自身生存、生产与生活环境的意图逐渐降低,民俗体育的宗教功能逐渐被娱乐功能所代替;而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环境到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范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被业缘关系所取代,民俗体育在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凝聚族人的功能逐渐被健身和现代交际功能所代替。
2.2内容和形式的更新
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宗教信仰因素的减少,民俗体育的宗教色彩在进一步降低,这必然导致民俗体育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如永新盾牌舞在如今的表演中,请神仪式被忽略,“五涧水老爷”的菩萨和抬老爷的轿子不在随身携带。服装变得更加鲜艳,经过改造后的音乐更加雄浑有气势,去掉了原有的妇女歌唱表演部分,使盾牌舞表演更加紧凑。而台湾宋江阵也取消了“开脸”(以油彩化妆)、服装也由专门表演服变成运动服,取消了不少原有的戒律,表演器械上虽然也贴有符箓,但已不再刻意强调;台湾高校也连续八年举办“创意宋江阵”比赛,使宋江阵更加符合当代社会需求。民俗体育的动作形式也因此会做出相应调整,如减少过去那种冗长、缓慢而重复的动作,更加讲究动作的美感和力度等。
2.3参与主体的改变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民俗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构成逐渐多元化,从以前专属某个特定群体转变为更加开放。如前面提及的宋江阵表演,过去主要是角头子弟阵头表演,现在外姓人也可以参与,职业构成中除了农民,还包括了商人、学生甚至公职人员。而盾牌舞过去仅仅是南塘村吴姓男子参与,现在参与者扩展到永新县各个阶层。过去民间舞龙舞狮活动,现在已经在高校中开展。
参与主体的改变,特别是受过较多文化教育的年轻人的参与,使民俗体育更加有活力。当然由于年轻人对这些民俗体育传统的理解与长辈不同,也带来民俗体育原始色彩的降低。民俗体育参与者构成的多元化也带来传承中的不变,更带来训练和表演中的配合问题。
3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民俗体育重构
民俗体育本身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在特定时间根据生产和生活需要而逐渐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宗教信仰、聚居形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特点。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民俗体育的生存环境在发生变化,如不能根据社会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进行民俗体育结构重建的话,其前途和命运则难以预料。
3.1动作形式应更加简单明快
城市生活节奏明显要快于乡村生活,无论是对于逐渐适应城镇生活的新市民也好,还是本已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市民也好,他们都希望从事更加简洁明快的体育活动。民俗体育原来的那种舒缓的节奏、复杂的动作、不断重复的样式已经不适合现代生活的特点。根据台中九天技艺团的真实经历改编的台湾电影《阵头》中,主人公对传统民俗体育进行改造,融入了现代音乐、舞蹈元素,使传统阵头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活力。台湾对民俗体育大仙尫仔的改造,也是将街舞动作融入进去,使其动作更加简单、节奏更加明快,以“电音三太子”的新形式出现后,原来较为沉重的宗教色彩被充满动感的体育色彩代替,受到青少年的普遍欢迎,并荣登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3.2象征符号可更加明显易懂
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逐渐脱离了农村生活的青年人而言,原来民族体育中的象征符号由于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如羌族推杆游戏中的“杆”和喜洲火把节中的“火把”都具有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于许多人已经难以理解。而有些民俗的象征意义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如重阳登高尊老的象征意义。还有些民俗体育活动,部分象征意义被人们记住,而部分被遗忘,如鞭春牛其劝春耕的象征被人们记住,而其繁育的象征意义则可能被忘记;而舞龙曾经的巫术象征意义可能被人们记住,但舞龙时不同数量、不同颜色的象征意义不一定每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下,现代民俗体育的象征符号的添加争取迎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只有这样,其教育和娱乐意义才更容易得到体现。
3.3信仰体系应凸显科学性
为了加强的合法性,民俗体育在演进过程中被附会了许多的传说。如闽南扒龙舟本是一种巫术“禳灾”活动,后来被附会上纪念屈原的传说;闽台宋江阵和永新藤牌舞和抗倭将军戚继光的传说联系起来;喜洲火把节加入了贞妇传说以适应儒家礼教的需要。这些传说是和当时的原始宗教及儒家思想相联系的,符合了社会主流的信仰体系要求,所以能被人们牢记和执行。而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具有迷信色彩的宗教信仰越来越被人们放弃,其内部动力作用难以体现。这时候就需要以科学、健康、人本等现代信仰来替代传统的宗教和儒家信仰,为民俗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4 结语
民俗体育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成为现代体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仪式动作、象征符号和信仰传说为内容的结构。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生存环境、参与和观赏主体自身素质的变化,面临“解构”的危险,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对其进行结构的重新调整。并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来培养传承人、完善民俗体育自身。
[1]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5.
[2] 王俊奇.也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及其关系[J].体育学刊,2008,15(9):101-104.
[3] 维多克·特纳.象征之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
[4]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58-159,209.
[5] 尹国昌,刘欣然.民俗体育奇葩:永新盾牌舞的文化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4):109-113.
[6] 周传志.台湾民俗体育“宋江阵”的社会人类学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4(2):99-101.
[7] 梁永佳.象征在别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85-103.
[8]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309.
DeconstructionandReconstructionoftheFolk-sports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
Zhou Chuanzhi, Yu Bingmei, Liao Jiancao, Huang Lizi
(Department of P.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Fujian)
The folk-sports has formed the structure which include ritual, symbol and belief in its long develop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folk-sports faces the danger of deconstruction because of change of it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participator. The deconstruct process has the features of the variety of functions, content and pattern, performer. The folk-sports should have a more simple action system, a more clear symbol system, and a more rational belief system.
urbanization; folk-sports;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2013-09-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TY015);闽南师范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SX12002);2013年闽南师范大学科技文化节立项课题、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310402070)。
周传志(197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闽台民俗体育。
G812.0
A
1672-1365(2013)06-0100-03